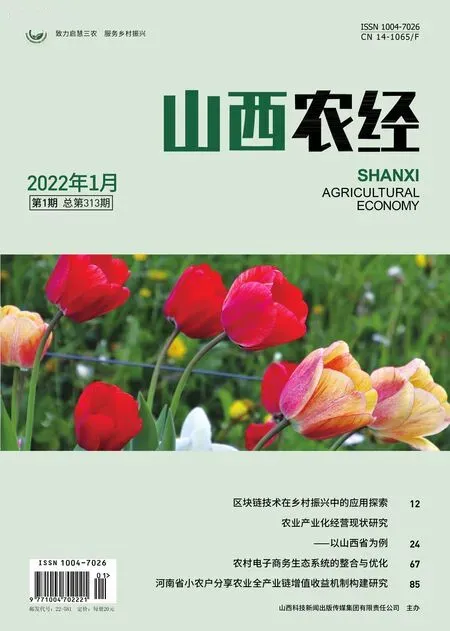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行動困境及破解
——基于后脫貧時代的視角
□李益銘,胡艷麗
(1.新疆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7;2.新疆大學國家安全研究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7)
1 問題提出與研究現狀
貧困是整個人類社會難以回避的頑疾。使貧困人口平等共享經濟發展成果,體現著社會的基本良善與正義。《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的發布,吹響了全社會脫貧攻堅戰總動員的號角。歷經數年努力,截至2020 年末,我國9 899 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 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的壯美篇章。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也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隨著絕對貧困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我國全面邁入后脫貧時代,農村相對貧困治理成了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2]。相對貧困是在比較中產生的概念。和以基本經濟狀況為核心的絕對貧困問題不同,相對貧困問題具有長期性、復雜性。這一客觀事實呼喚著包括社會組織在內的多方力量在制度化框架內共同行動。因此,理清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的行動困境并加以紓解是緊迫的現實問題。
人們對貧困的認識由來已久。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立足于無產階級立場,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出現的貧困問題及其根源進行了闡釋,為反貧困行動提供了實踐指導[3]。阿瑪蒂亞·森(2001)[4]從“可行能力”角度考察貧困問題,認為改善貧困人群創造經濟收入的技能和能力是消除貧困問題的關鍵。可持續生計是學界較為主流的理論分析框架。這一框架將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等綜合考慮,貧困對象可以在指導下進行資產調整組合以優化生計策略、改善貧困狀況[5]。引入社會組織等力量參與貧困治理已經成為了一種共識。社會組織所具備的行動優勢能夠加速扶貧資源的動員速度,推動貧困治理目標的實現[6]。社會組織參與貧困治理的行動,實際上就是前者利用自身信息、資金優勢以扶貧項目的方式改善貧困群體生活狀況的活動過程[7]。作為社會治理工具的有效補充,社會組織必然在我國農村相對貧困治理工作中承擔重要的使命[8]。
2 后脫貧時代視角下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的必要性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農村相對貧困問題將長期存在。農村作為社會治理的一部分,其相對貧困問題是不同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同其他治理難題一樣,農村相對貧困治理需要以整體視角去考察。以后脫貧時代為視角,對農村貧困問題加以審視,可以發現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的必要性。
2.1 “運動式”貧困治理模式轉變的現實背景
脫貧攻堅時期,我國貧困治理模式具有鮮明的“行政力量”主導的特征。在這一模式內,大量政策資源向農村地區傾斜,使我國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在較短時間內基本得到解決。攻堅式貧困治理模式的有效運轉需要投入大量的治理成本,在脫貧攻堅戰結束以后,社會層面已不再支持開展規模大、動員程度高的“運動式”貧困治理行動,時代呼喚治理成本更低、更具有針對性的新型貧困治理模式。
“攻堅”一詞本身就在表達一種短期內集中力量以克服難題的狀態。隨著我國邁入后脫貧時代,行政力量正有序退出,政府角色也將由“臺前”轉向“幕后”。我國“運動式”貧困治理模式正加速轉變,社會組織有必要參與到農村相對貧困治理行動中,成為新型貧困治理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2.2 相對貧困問題的特點與社會組織角色特征相契合
相對貧困問題具有復雜性與長期性兩個特點。復雜性即造成客體相對貧困的原因、界定其是否擺脫相對貧困狀態是復雜的;長期性即與絕對貧困相比,相對貧困在一定社會范圍內會長期存在。相對貧困這兩個特點使得該問題的治理手段需要從多樣性和持久性兩個方面加以考察。社會組織作為社會力量的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社會治理工具的重要補充,隨著社會發展而長久存在。作為一種“自組織”,社會組織本身具備多樣性的特征。致力于解決相對貧困但發力點不同的社會組織,恰能與復雜的、不同類型的相對貧困問題對接起來。這一現實凸顯了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的必要性。
2.3 治理資源導入需求與社會組織功能的互補
貧困治理目標難以在外部資源輸入不足的情況下實現。貧困治理客體需要各種資源的有效輸入,這些資源包括各種扶助資金、教育和技術培訓等。治理行動中,這一資源導入的需求與社會組織的功能是互補的。具備公益性和信息優勢的社會組織在作為外部力量參與治理行動時,不僅能將各類資源直接導入到貧困家庭中,還能在充分了解貧困地區需求的基礎上,充當各種社會力量的“紐帶”,將致力于回饋社會的企業、想要擺脫貧困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平臺等聯合起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有效改善貧困家庭的處境,推動解決相對貧困問題。
3 社會組織參與我國農村相對貧困治理的多重行動困境
3.1 依附性困境:依附性過強,社會影響力難以有效擴散
政治科學語境下的“依附”(Dependency)是指特定國家經濟發展會受到其所依從的另一個國家經濟活動擴大或縮小的影響。這一描述本身是中性的。引申至社會層面,社會組織恰需要一定的“依附”狀態才能有序發展,然而過度依附必然導致行動力難以滿足現實需求,文章將其概括為“依附性困境”。
社會組織是公民社會的產物。由于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我國社會組織發展起點較低。相較于更符合我國歷史文化、有著天然“權威合法性”的政府,社會組織在參與貧困治理行動時會出現公信力不足的情況,其社會影響力難以擴散,直接影響貧困治理行動成效。此時,為了獲取更多“資源”和“便利”,社會組織會傾向于主動加深依附水平,反過來加劇公信力不足的狀況,形成惡性循環[9]。在后脫貧時代,隨著政府在扶貧領域的角色由“親自下場”轉向“方向指揮”,社會組織需要扮演更加積極主動的角色,而陷入依附性困境的社會組織將難以在后脫貧時代發揮更大的作用。
3.2 制度空間困境:制度空間模糊,政策支持不足
這一困境體現于制度空間和政策支持兩個方面。
一是制度空間方面。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社會組織的管理依據主要有《民法典》《慈善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以及其他各類零散分布的政策文件,尚未有統領性成文法律,制度空間較為模糊,并伴隨經常性的“清理整治”。面對此種狀況,社會組織會長期傾向于采取保守的管理措施,回避幅度過大、影響組織穩定的改革措施,使本組織長期保持原有的管理結構,這不利于本組織長遠發展,更使得其在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行動時難堪大任。
二是政策支持方面。我國地方政府層面的社會組織發展專項政策較多,而中央層面的支持性政策相對較少,政府整體對社會組織的態度是“允許”而非“大力支持”。社會組織在培育和發展環節受到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強,影響其對相對貧困治理行動的參與。
3.3 組織能力困境:外部行動目標難以實現,內部管理水平不高
組織能力困境體現在內、外兩個方面。
一是外部困境,即社會組織的行動能力不強。審視我國既往的貧困治理實踐可以發現,社會組織在獲得貧困治理的“入場”許可后,其行動過程往往呈現出“被動”合作的特征。社會組織本身的行動能力難以符合現實要求,而扶貧項目在執行過程中往往會在地方公權力的影響下使最終成果出現“精英俘獲”、目標偏離等多種現象。
二是內部困境,即社會組織自身的組織管理水平不高。我國社會組織管理水平良莠不齊,組織制訂的管理條例、原則與愿景在多數情況下僅依靠自我約束來實現,整體管理水平不高,缺乏自我提高組織管理水平的意愿,難以將組織行動與貧困治理對象有機整合起來,必然嚴重影響貧困治理行動的效果。
4 紓解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困境的對策
4.1 機制端
機制是各要素運行方式的集合,破解社會組織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的困境首先要從機制端發力。
一是宣傳機制。要通過宣傳引導,將社會共識凝聚起來,使更多的社會力量關注到農村相對貧困問題。要認識到相對貧困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制度性的減貧長效機制才能加以解決,并為不同社會力量參與共同治理奠定良好的輿論環境。社會組織要加強自身公信力建設,重視利用互聯網平臺擴大社會影響力,加強與民眾的溝通交流。
二是盡快設立多方參與的新型治理與保障機制。在這一機制的治理環節,政府應作為引導性角色存在,減少行政干預,提高社會組織活動的自主性;社會組織則是這一治理機制內的關鍵行動者,在政府、政策的宏觀引導下,以“行動伙伴”的角色參與其中,更加直接、靈活、有效地對接貧困地區,通過責任共擔、成果共享的方式,推動貧困治理目標的實現。在保障環節,應注意后續可能出現的返貧問題,通過安排多輪階段性結果觀察,使社會組織的行動能夠真正與貧困群眾福祉掛鉤,有效阻斷返貧過程。
4.2 政策端
政策反映著權力投入的方向與目標。
一是要加快整合現有的法律、法規,完善與社會組織有關的法律安排,盡快出臺一部充分反映我國國情且具有“提綱挈領”地位的專門法,調整社會組織的活動空間,為社會組織的長遠發展提供支持,為社會組織更好地參與農村相對貧困治理提供充足的政策基礎。
二是圍繞我國農村相對貧困治理和社會組織發展的特點,出臺以培育為重心的社會組織發展支持性政策體系。這一政策體系應具備及時更新的特征,通過分類支持、重點培育與農業農村發展緊密相關的社會組織做大做強,使更契合解決農村問題、掌握農村地區群眾真實需求的社會組織成為政策的受益人和農村相對貧困治理行動的主要參與者。
4.3 能力端
貧困治理目標能否實現是由具體的實踐活動決定的,實踐是貧困治理過程的關鍵環節。破解前文所述的“能力不足困境”,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
一是采取措施激發社會組織提升行動力的意愿。在現有社會管理體系內,根據不同農村、不同類型貧困的特點,對參與相應治理的社會組織定期進行綜合評定。評定內容應以社會效益為導向,將受助群眾評價、合作伙伴方評價等維度納入其中。對于取得較好評定結果的社會組織,可適當給予包括財政獎勵在內的各種獎勵。
二是強化對各類社會組織開展管理人員培訓和交流活動的支持。鼓勵不同社會組織之間增強合作、加深共識,進一步支持社會組織之間開展各種經驗交流活動。要在總結部分組織管理水平較高的社會組織運作經驗的基礎上,以社會組織管理人員為對象,針對性設計相應的培訓課程,并使這些內容實現制度化、長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