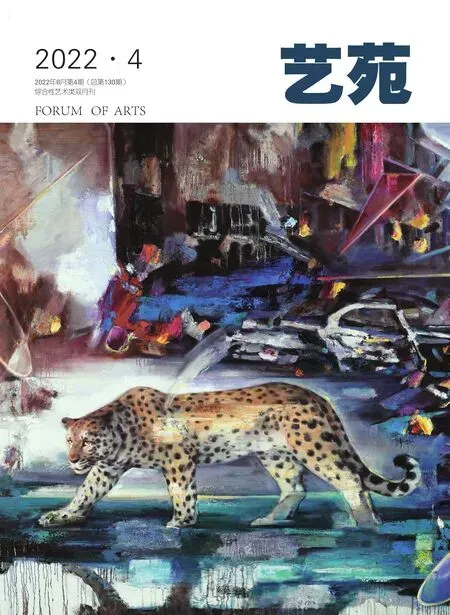文化變遷視域下韶山山歌的傳承與重建
蔣 河
傳統音樂的形成與建構是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化間“濡化”“涵化”的結果。[1]67在多元文化融合與互動中,生成了原生性的音樂文化傳統,這種傳統有可能是對既有傳統的發明、改造與借用。韶山山歌是湖南韶山人民在生產生活中集體創作、世代傳唱的歌曲,因為歷史移民活動、區域交通及物質生產方式等變遷,韶山山歌不斷適應其所處時代社會、歷史、民俗、審美語境的需求,這一延續的傳統音樂文化行為,在城鎮化進程中逐漸失去了賴以產生、生存、傳承和發展的空間。所謂文化變遷(Culture change),多數人類學家指的是任何足以影響文化內容或文化機構的變化。[2]39“無論社會平穩還是動蕩,所有文化都會在歷時進程中的某個時間點發生變異。”[3]126文化變遷改變著人們的行為和觀念,對于民歌而言,歌唱行為與歌唱觀念無疑是基于區域歷史文化背景而生成。
在以往的研究中,筆者探討了韶山山歌的音樂文本特征、旋律特征及演唱行為方式[4]16-19,郭朋榕討論了韶山山歌的文化利用價值及非遺傳承困境[5]280-281,熊曉輝談到韶山山歌與青年毛澤東獨特性格形成之關系[6]8-11。筆者經過疏理發現,目前的研究尚未專注于歷史變遷視角下韶山山歌這一歌唱“傳統”的傳播形式、生成語境及文本構成。本研究結合筆者作為韶山人親歷的“知”與田野考察的“知”及相關歷史文獻閱讀的“知”,對位于韶山沖的韶山山歌現存傳承人進行山歌采錄與口述史訪談,同時閱讀地方志及地方整理的民間歌曲集,分析這些文本以揭示在社會文化環境變遷視域下韶山山歌是如何體現出文化傳承與文化重建的特征。
一、“十里三音”:人口的歷史遷徙與山歌音聲屬性
(一)移民:文化的“涵化”
文化特征的空間分布是經時間變化的結果,族群傳統文化的涵化過程最終導致本土音樂文化的重建,并隨著長期的歷史積淀以及對主流文化的認同,進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傳統。[1]67-78歷史上人口的大規模遷徙不僅給韶山地區帶來了文化的傳播,而且通過文化融合等極大地影響了地方的風俗,實現地方文化的重建。江西移民自唐末五代開始,宋元遞增,明代為盛,長達七個多世紀,他們在湖南許多縣境內“率多聚族而居”,有的縣“十戶有九皆江外之客民也”。[7]55其中“十里三音”便是移民運動帶來的現象,因為移民,使得贛語、湘語出現了區域間復雜的融合演變。《湘鄉同治縣志》載:“湘邑民無數姓為一村,多聚族而居,不輕易出外。”[8]40由此可見,家族聚居生活圈子狹小,與外界接觸受到限制,這是“十里三音”現象的重要形成原因。
江西移民給韶山帶來了江西的語言,如,韶山方言走叫“行”(hang)、吃叫“呷”(qia)、腦袋叫“腦殼”、乞丐叫“叫化子”、烏黑叫“墨黑”等,都是江西口語。從2013年至2016年間,筆者在韶山市文化館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期間搜集了70余首韶山山歌歌詞,通過對詞集中大量情歌內容歌詞分析發現,韶山山歌中稱“情妹”為“嬌蓮”,如《日落西山想屋里》:“日落西山四山黑,嬌蓮搶傘就留哥住,我的妹,山中還有牛和馬,房中還有少年妻,日落西山想屋里。”(1)這個共有的名字還出現在湘中安化山歌中,如“玉米葉子兩頭尖,玉米好吃桿子甜。想吃玉米早來摘,想找嬌蓮早來連。”“楠竹山里好排姜,交個情姐在遠鄉。隔山打鑼鑼不響,氣死姣蓮想煞郎。”[9]54還出現在贛西山區蓮花縣山歌中,如“打鼓要打鼓邊沿,作田要作姐門前。一日落得三回水,三天見得九回面,兼到落水看嬌蓮。”“打支山歌嬌蓮聽,可惜嬌蓮離遠哩。”“二勸來到界河邊,河邊碰見嫩嬌蓮。嬌蓮問我名和姓,梁山伯來祝英臺。”[10]38-43
結合歷史記載與山歌文本分析可見,“嬌蓮”這個俗語并非韶山的“傳統”,由此可推測,韶山山歌是在移民運動中兩種文化互動交流而形成的音樂文本互文,是文化不斷的“涵化”所形成的結果。
(二)山歌:內涵與外延的建構
什么是山歌?韶山山歌在長期的自我文化建構中形成了穩定的局內觀念,這種局內觀念對于山歌內涵與外延的界定有別于傳統的民歌“三分法”所定義的山歌。按照“三分法”對山歌的屬性論斷,山歌在音樂體裁本質上特征是直暢和自由的,“是山歌產生場合條件和功用要求在音樂上的集中反映,又是山歌音樂形式構成要素特征形成的原因之一”[11]101,具體表現為感情抒發的直暢性、形式創作的自由性、形式手法的單純性。[11]101-102按照《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湖南卷》,湖南漢族民歌的分類方法根據湖南地區實際,在三分法的基礎上加入了田歌,即分為山歌、小調、號子、田歌四類。其中,對田歌的定義是:“農民在田間勞作時為解除長久單調的勞動而形成的勞累疲乏,鼓舞勞動熱情所唱的歌。它大部分是在集體耕作中演唱,有獨唱、對唱、穿唱、一領眾合等形式。”[9]212按照這個定義,田歌和山歌的屬性十分接近,只是田歌是局限在勞動中演唱,目的是為了鼓舞勞動熱情。然而,在韶山人局內觀念中,田歌即山歌,田歌音調與一般山歌音調構成并無很大區別,區別在于田歌為一唱眾和的形式,領唱為實詞,和唱為襯詞。
根據對老傳承人的采訪及山歌采錄,筆者將所采集到的山歌文本進行梳理歸類,得出他們所認為的“山歌” 的類型范圍——在生活中、勞動作中所演唱的直暢、即興、自由的歌曲都是山歌,山歌的表現方式有獨唱、對唱、一領眾和,其中就唱腔而言分為平腔和高腔,就演唱場合及內容綜合考慮來說,分為插田歌、踩田歌、情歌、生活歌等四類。
(三)旋律:湘語特色音聲音調
受到歷史移民的影響,韶山的方言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而這個特色直接影響到韶山山歌的音調、節奏等特征。韶山型方言唯獨存在韶山區域,而距韶山不到二十公里的相鄰地帶有湘鄉型方言、長沙型方言、流沙河型方言,可見韶山方言的獨特性。拿湘語古全濁聲母的演變為例,韶山型方言和周邊的就有差別:韶山型方言古全濁聲母在舒聲韻中逢塞音、塞擦音基本保留濁音,逢擦音部分保留濁音,部分清化,在入聲韻中古全濁聲母全部清化;而湘鄉型方言古全濁聲母在舒聲韻中濁音基本保留,并無清化,長沙型古全濁聲母清化,在舒聲韻中一般讀不送氣音。[12]66語言在一定程度影響到文化,一方面它是傳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保存和體現了特定文化,語言也影響到山歌的生成,韶山方言的語言音調、發音特色、慣用詞匯對于韶山山歌的風格特點產生了重要影響。
韶山山歌很大程度上體現出韶山方言音調的某些特征,韶山山歌有即興、隨意的特征,它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演唱,歌詞表現得口語化、生活化,因此也往往會使用大量口語詞句和襯詞,山歌中基本旋律的特征、特征音程與節奏、調式等特點都各自有其特色。從韶山方言的調值來看,主要集中在 5、3、1,實際的語音音高接近于羽宮角三個音構成的音程關系,韶山山歌中的字多腔少的陳述性段落音高十分接近于語音。[4]16-19韶山山歌因使用韶山方言演唱而流暢、樸實,襯詞多,襯腔多顫音,音域八度以內,組合最多的是“小-大三度”關系結構,這個音調結構形成主要受方音影響,即羽、宮、角三個音相互構成大小三度關系,構成韶山山歌旋律音調(譜例1)。受方言語調的影響,顫音和滑音的運用很多。
除了音調特征,韶山方言還影響到山歌的節奏特征,例如韶山山歌中有一種陳述唱詞的節奏,這類節奏接近語言的節奏,未形成規整的節拍旋律,通常是一字一音(譜例 2)。
還有一種是句中與句尾加插的延長音及拖腔,延長音的自由伸縮幅度較大,經過觀察發現同一山歌不同次的演唱,延長音的音高變化不大,主要變化在節奏伸縮,例如《不是情哥不開腔》(譜例3)。
二、“棄農從商”:物質生產變革與歌唱環境轉變
(一)交通:從封閉走向開放
影響文化變遷的機制有很多,如變異、創新、傳播和涵化。[13]410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常用來描述今天正在發生的社會和文化變遷的術語之一,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原本閉塞的韶山變得開放,外文化、全球化不斷沖擊這這片土地,通過文化傳播不斷影響著韶山地區的文化變遷,影響著韶山山歌的“傳統發明”及傳承傳播。
韶山社會由農村為主改變為以城市為中心,非農業人口逐年增加,人們的職業從農民為主轉向多元發展,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為主轉向為以第三產業為主。20世紀中葉之前韶山交通十分閉塞,陸路交通不便,只有鴉瓦大道和鄉寧大道縱橫境內,路寬不過兩米。陸上運輸全靠肩挑背負,土車運送,境內與外界主要的物資運輸靠鱉石橋和銀田寺設有的碼頭。[14]214在這種環境下生成的韶山山歌較少受到外來文化傳播的影響,山歌音調與唱詞受到傳統的影響較多。另據《韶山志》記載,新中國成立后,境內交通建設發展迅速,從 1950 年開始修建七里鋪至韶山沖的公路,半數以上沙石路面改為瀝青或水泥路面,1967 年韶山鐵路建成通車,與湘黔線連通,方便全國各地群眾來韶山參觀,之后省道、縣道、鄉道的修建與完善讓韶山與外界、農村與城鎮交通越來越方便,隨著外來游客的增多,韶山開始發展第三產業,逐步城鎮化發展。[14]213隨著外來文化的不斷傳播與信息全球化的到來,韶山已經不再封閉,韶山山歌已經失去了原生的土壤,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由農耕主體轉向旅游服務為主體。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價值取向呈現出多層次、異質性和多元并存同構于同一生活空間的態勢”。[15]35-39筆者在韶山度過了少年時期,感受到在城鎮化的進程中人們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娛樂相互分離,人們娛樂方式越來越多樣化,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與生產力的發展,人們有了閑暇的時間上網、打牌、看電視、聽廣播,很少有人再演唱山歌來傳情解乏。
(二)生產:從農耕轉向旅游服務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生存于其中的物質環境對其所實行的社會文化制度和習俗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因為一定環境下的居民會用一定的技術開發自然資源,因而也就會結成了一定的勞動組織模式,而勞動組織模式又會影響到社會結盟方式”。[16]67“我們只有掌握了音樂在其文化和社會環境中發生、發展的相應證據,才會對人類在音樂方面的創造行為有所領悟。”[17]59韶山山歌的演唱場合大多依附于勞動,物質生產方式的變遷直接影響到韶山山歌演唱場域,甚至韶山山歌的主體——山歌手的存續。
韶山山歌在農耕時代具有凝聚族群、團結勞動者的重要作用,植根于韶山歷史文化深處的“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把韶山人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長期積累成為一股無形的社會力量,推動著韶山村民積極參加生產勞作。在人與人近距離接觸中山歌是重要的情感交流橋梁,它生動地展現出韶山地方音調的韻味,是一個族群的聲音,包含著全民性的活的記憶,是構建文化認同的重要標志。韶山田秧山歌中的一唱眾和就是團結與凝聚族群的生動例證,在集體插秧等勞動中,領唱者的唱詞十分富有號召性與意志力,和唱者和的都是非語義性的襯句,同一而與領唱呼應。在過去韶山多自然災害,生活條件艱苦的環境下,韶山田秧山歌凝聚了集體勞動者,有利于形成團結合作的協作精神,提高勞動效率。“那個時候,不管是插田、砍柴還是做其他農活,大家都喜歡唱幾句山歌。”毛繼余說,“只要哪個一開腔,大家就跟著和起來了。”例如韶山田秧山歌《我們沖里開秧田》領唱與和唱一唱一和,領唱歌詞表達了勞動人民渴望大豐收的愿望,采用了夸張的手法,如“梗禾長得賽茅棚”“糯禾長得像苧麻林”“新禾壓斷舊田壟”等。而集體插秧活動中,勞動者們的和唱體現出對領唱的認同與呼應,生動展現了開秧田們(插秧)這一生產習俗中,勞動者們的勞動熱情。
韶山山歌在農耕時代還具有調節情緒、緩解疲勞的功能,是人們勞動與生活中重要的精神生活組成部分。韶山農民通過歌唱的方式將人們的精力轉移到山歌上來,在勞動時忘記疲乏,在生活的閑暇中歌詠時事、生活,通過山歌傳情達意,溝通交流。2014年6月18日,筆者和山歌手毛愛霞在其韶山沖家中進行了訪談,試圖解讀韶山山歌的局內觀念。毛愛霞說:“勞動累了休息的時候唱,覺得輕快,有涼風吹。”正如她所說,歌手們普遍認為,唱山歌有緩解疲勞的作用,所以山歌主要在勞作時演唱,以插秧為例,勞動者彎腰插一會秧,然后伸直腰唱幾句山歌,不僅能和其他勞動者取得交流,而且放松了自己。她還說:“做事的時候,男的逗女的,女的逗男的。”不論婚否,山歌中的情歌通過男女對唱的形式能讓勞動的氣氛變得活躍,這是農民們自娛自樂的一種方式。
現代農作機具的推廣普及,逐漸替代了傳統農具的手工勞動,原本依靠手工勞動的集體插秧、收割活動逐漸被機械農具所替代。1982年春,中共中央《關于湖南問題座談紀要》的精神在韶山貫徹后,全區 61個大隊、1063個生產隊、19581戶農戶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又取消糧食、棉花、油料、生豬統派購制度和調整農業的內部結構。[14]22020世紀80年代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更是讓農民轉變了生計方式,農民的經營自主權得以擴大,農業逐步向工、商、運輸、建筑、服務綜合經營的商品經濟轉化。隨著承包責任制的完善,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外出打工者逐漸增多。[14]67生產、生計方式的轉變直接導致山歌的演唱主體——農民的銳減,大量農村人口外出打工維持生計,不再面朝黃土背朝天,也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曾經的農民集體出工景象不復存在。原來集體勞動中,一唱眾和的田秧山歌難以尋覓,生產方式的變革直接影響到山歌的演唱環境,根本上導致了田間歌手的缺失。“人有一種沖動,要在直接呈現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實現他自己,而且就在這實踐過程中認識他自己。”[19]39當艱苦的集體手工勞作語境不復存在,作為進行交流、活躍勞動氣氛的山歌原生語境已經瓦解。
三、“歌唱的歷史”:社會文化變遷與山歌創作傳播
(一)革命山歌的生成
“民歌,特別是抒情的民歌,這種形式最容易為不脫離生產的人們所掌握,并且常常是他們不吐不快的時候的產物,就自然很多都是真摯動人地抒寫勞動者的胸臆的作品了。”[20]24歌以言志,唱韶山山歌的勞動人民在歷史不同時期通過山歌來反映意志,韶山山歌留下了不同社會歷史時期的印記。新中國成立前,韶山境內仍然是封建土地制度,地主占有土地對農民進行剝削,農民不得不以高租、高息、高押金佃耕地主的田地或受雇為地主耕種。由于無法擺脫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農民世代受窮。
韶山山歌《有女莫嫁韶山沖》體現出韶山沖過去封閉、貧困的狀況:“韶山沖,韶山沖,我丈夫砍柴做零工,家住深山嘴無人問,茅屋小路無人行,有女莫嫁韶山沖。”[9]322再如《韶山和歌》:“韶峰山上幾千年,窮人過去無保障,田里豐收有寅年,討米逃荒在外邊。”[20]10
過去韶山農民苦難的日子也從側面在韶山山歌中體現,如山歌 《十二月探嬌蓮》表達出十二個月都要農忙,只有過年時節才有空探望姣蓮。山歌中也有反映階級斗爭的內容,如《打起山歌斬閻羅》歌詞中就有階級斗爭的內容在里面,“磨快梭鏢閃閃亮”“自衛軍成立人耳多”“打起山歌斬閻羅”,表現出農民群眾的意志與認同。還有的山歌,是對韶山貧苦的傾訴,能激起群體認同。如《車柴難買兩尺布》:“韶山沖來沖連沖,丈夫砍柴做零工,要想扯布做衣裳,舍死送柴到鎮上,車柴難買兩尺長。”[20]14
農民以山歌歌唱出對農民協會的認同,通過韶山山歌表達農民階級的意志。農民協會是從1925 年開始在韶山成立的社會團體,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反映農民階級的意志。農協負責人是農民夜校教員,夜校的學員多為農協發展對象,韶山周圍 20 多所農民夜校后都成為秘密的農協組織。韶山農協開展平糶、減租減息和廢除田捐、特捐的斗爭,農協成立農民自衛軍,采取清算、罰款、小質問、大游團等方法,給土豪劣紳有力打擊。農民協會還開展禁止牌賭、鴉片、宰殺耕牛等活動,開班農民夜校,沒收祠堂、寺廟作為農民協會會址。1927 年,農協會員由 2 萬人發展到 4 萬余人。[14]56筆者2014年采錄到的反映這一歷史的山歌有山歌手毛繼余演唱的《農民協會好威嚴》:“郎屋門前一樹槐,槐樹高頭掛招牌,招牌上面四個字,農民協會好威嚴,我情哥哥在里邊。”
韶山山歌《打起山歌斬閻羅》[9]112則充分體現出韶山山歌在農民群體中的價值認同,歌詞中“山歌不打不快活,大路不走草成窩”充分體現出農民的革命干勁,“磨塊梭鏢閃閃亮,自衛軍成立人耳多,打起你山歌斬閻羅”反映出農民協會成立自衛軍的真實歷史,體現出農民自衛軍打擊土豪劣紳的斗志。
韶山是毛澤東的故鄉,韶山留下了毛澤東開展革命活動的足跡,韶山人民對毛澤東有著深厚的情誼,因而,有一些韶山山歌表達了韶山人民對毛澤東這一“同鄉”的擁戴與崇拜。如筆者2014年采錄到的毛繼余演唱的《太陽一出四山紅》:“太陽一出四山紅,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韶山解放后,逐步走向開放與富裕,韶山山歌體現出韶山農民對黨的感激之情。如《春風不吹花不開》:“春風不吹花不開,樹木不花果不來,沒有黨的好領導,幸福日子不會來。”[20]11再如2015年筆者在韶山沖湯瑞仁家采錄的湯瑞仁唱的《天上星星朗朗稀》:“天上星星朗朗稀,莫笑貧家人穿破衣,山中樹木有長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感謝黨和毛主席,紅色江山萬萬年。”還有《春來早起莫貪眠》:“春來早起莫貪眠,夏日炎天苦向前,秋天懶惰無收獲,冬天寒冷莫怨天,感謝黨的好領導,幸福的日子萬萬年。”
在革命時期,韶山山歌的歌詞文本充滿著斗志,不論是《農民協會好威嚴》還是《打起山歌斬閻羅》,都蘊含著強烈的斗爭精神;新中國成立后,韶山山歌歌詞文本則集中表現了韶山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激之情,對于毛澤東的敬仰,這種感激與敬仰是直抒胸臆的。韶山山歌來源于民眾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的集體創作與傳唱,積淀著韶山地方百姓的情感,體現出區域與族群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和心理特征,因而,韶山山歌承載著歷史記憶與文化基因,它是基于族群集體記憶之上的族群中的個體對族群共同體的歸屬認知和情感依附。
(二)作為“非遺”的山歌
我國一直使用的“民族民間文化”的內涵與教科文組織1989年提出的“傳統和民間文化”相類似。但“民族民間文化”不能完全等同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亦難于涵蓋“高雅、精品文化”以及宮廷藝術、宗教文化等門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1989年提出的“傳統和民間文化”、1993年提出的“人類活瑰寶”到后來的“人類口頭遺產”“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以及最后確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概念不僅是名稱的變化,更是國際社會在幾十年的保護工作中走過的幾個比較重要的階段,是對非物質遺產價值不斷認識并逐漸加深的階段。“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提出首先是擴大、擴展了對該遺產的保護范圍和寬度,其次是加大了保護深度和保護力度,再就是對該遺產價值的認識的不斷提升。“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作為一個概念,在漢語語境中,其名稱就包含了廟堂/民間這樣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隱伏著一定的價值判斷;同時,“民間”還體現出與“主流”相對立的話語姿態,這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判斷是有所區別的。[21]
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公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來,我國政府積極響應,加入了該《公約》,國務院辦公廳2005年出臺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制定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等[22]179,2011年通過公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在2006年6月又公布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還相繼成立了國家、省、市、縣各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逐步形成科學的保護體系,人們的保護意識逐漸加強。在“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保護方針指導下,2007年,韶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成立,由韶山市文化館主管,為韶山市文化館內設機構,其人員也由韶山市文化館工作人員兼任。2007年至2010年韶山市文化館普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共16類31項,建立了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中韶山山歌等項目于2007年申報為湘潭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項目。政府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工作的主導者,在政策法規、投入資金、組織工作等方面起到了支持的作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策實施條件下,韶山山歌得以被逐級申報與保護,2012年5月,韶山山歌成功申報為湖南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筆者在2013年至2020年在韶山文化館工作的幾年間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發現當地在山歌搜集傳承中帶有機械性思維,每年象征性地開展幾次山歌進校園與山歌節慶舞臺展演活動,剝離了山歌傳承本質的文化邏輯。例如山歌手在韶山銀田鄉村旅游節被邀請去油菜花地給游客唱山歌,營造旅游節一時的民俗熱鬧氛圍;在宣傳部門組織的群眾文藝匯演活動中,把它“拿來”加上MIDI伴奏進行翻唱,成為被包裝的韶山文化,使之“為他人生產自我”。失去原生土壤的韶山山歌,作為“非遺”的保護措施除了記錄與展示外,沒有找到有效的傳承路徑。
非遺的系列保護措施起到了記錄與宣傳韶山山歌的作用,但多年的“非遺”保護工作并沒有對韶山山歌的有效傳承起到作用。根據筆者2020年的走訪調查及與各個鄉鎮文化站咨詢掌握到的消息來看,韶山山歌目前在民間存活狀態不容樂觀,山歌手普遍老齡化,隨著一些老山歌手相繼離世,山歌傳承幾乎到了“人亡藝絕”的境地。從目前普查所掌握到的老一輩傳承人分布來看,大坪地區2人,原韶山鄉5人,永義地區2人,如意地區1人,楊林鄉2人,歌手年齡普遍在70歲以上,而稍微年輕的傳承人不但數量稀少,而且由于其生活脫離了山歌原生的農耕社會土壤,所學到的山歌沒有老一輩那么“地道”,無法成為“局內人”。從田間景觀來看,韶山山歌已經基本從田間景觀中消失,一方面,傳統手工勞作被機器所替代,曾經的“集體出工”的場面不再,韶山山歌賴以生存的農耕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變遷,人們的審美娛樂方式多元化,唱山歌的習俗已不再,沒人唱,沒人接應更沒人和,山歌只留存于老一輩傳承人的記憶中。
(三)山歌的舞臺化改編與呈現
美國民俗學與民族音樂學家約翰·霍姆斯·麥克道爾認為:“‘使民俗化’(to folklorize)意味著將傳統的表達性文化從生產的源點抽離出來,并且將其重新置于一種與之疏遠的消費 環境。”[23]16-32韶山山歌經過多位藝術家改編成舞臺音樂作品,這種重建的韶山山歌表演形式是作曲家認為的有效彰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種藝術形式。20世紀 50 年代,韶山山歌從田野剝離作為獨立的藝術作品呈現。當時歌唱家何紀光深入湖南民間,向民間高腔山歌歌手請教,其中,他來到了韶山學習韶山的插田歌——“過山壟”——這種山歌一唱,隔山隔壟都聽得見。[24]153何紀光把學來的韶山山歌《插田歌》讓歐陽振砥重新填詞、白誠仁改編,編成了領唱加合唱的多聲部歌曲《日出韶山東方紅》。20世紀70年代,這首歌通過出版物進行廣泛的傳播,目前筆者共搜集到20世紀70年代載有《日出韶山東方紅》的出版物11本,它們集中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這是韶山山歌音調最早的改編藝術作品,也是當時最為廣泛傳播的、具有深刻影響的作品。在20世紀70年代《日出韶山東方紅》輝煌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韶山山歌沒有再被藝術家挖掘,隨著改革開放與社會轉型,山歌漸漸走出了韶山人的生活。直到2008年,湖南作曲家劉振球先生來韶山找尋山歌手,他將原生的韶山山歌加入他的交響詩《長島人歌》的素材,也是從那開始,許久未唱山歌的毛愛霞和毛繼余將山歌“重新撿了起來”。因為交響詩《長島人歌》,兩位韶山沖里的老人隨湖南交響樂團將山歌唱到了臺北音樂廳和國家大劇院。這些“被邀請”走向舞臺藝術的山歌表演,就是一種音樂文化身份的重建過程,同時這種結局來自于韶山山歌本身民間傳唱語境的逐漸消失,以及外部的現代化、流行化、城鎮化進程對地方民間音樂強烈沖擊影響下的文化產物。
四、余論
在新文化地理學的概念中,地方是聚集了人們的經歷、記憶、愿望、認同等多種情感的場所;而空間更多帶有抽象的表征意義,具有隱喻性[25]1-5。但我們仍可以看到,在社會的急劇變革下,韶山山歌的音樂主體文化身份被模糊,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不復存在。就拿老一輩山歌手來說,他們成了“代表性傳承人”之后,雖然留住了他們的歌唱能力,卻依然面臨后繼乏人的尷尬境地,因為韶山山歌原始質樸的歌唱方式及音調潤腔與現代人歌唱習慣有所出入,這也是為什么當我們試圖引導年輕音樂愛好者去學習山歌時,他們普遍認為“難”或者“找不準調”,從而出現很難找到一個能很好傳承韶山山歌的年輕歌手的原因。當韶山山歌“申遺”后,其價值被得到“認定”,成為韶山地方文化的一個符號,然后,政府與藝術創作者所利用各自主體理解的山歌來進行“地方文化”的宣傳與推介,這種“地方文化”是在他者視角的價值界定,包含權力與文化多重價值判讀,是一種“人工文化”。
筆者認為,更好的傳承韶山山歌,除了維護山歌的原生性環境,還要讓山歌本身有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新變遷,在適應中保留山歌的基本音樂文化屬性。韶山山歌要保持活態,應該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是要有活態的傳習環境,歌俗、歌唱習慣不能斷,光靠帶幾個徒弟、進幾次校園是無法保持山歌生命力的;其二是要有活態的民間山歌創作與傳播,山歌內容也需要“與世推移”,也需要“換血”,正如本文從歷時性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時期韶山山歌內容的嬗變,這種“傳統的發明”才能延續下去。
韶山山歌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而出現不同的主體內容。在全球化、現代化和城鎮化的的大背景下,人們信息傳播方式、娛樂生活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是不可逆且應主動適應的過程。反觀文化變遷過程,韶山山歌由作為生活的民俗走向了作為文化與權力展演的新民俗,從民俗原本的自我封閉式傳承走向應用性的創作與發明的范式轉變。本文以梳理韶山山歌在這一變遷中經歷的動態的、持續性的文化重建過程,挖掘它在文化變遷過程中建構中的意義及其驅動因素,這無疑對我們認知韶山山歌這一民間音樂文化的傳承保護,探索歷史隱喻與文化變遷的傳統音樂文化傳承傳播途徑有著參考意義。
注釋:
(1)歌詞于2017年7月采錄于韶山市韶山沖毛繼余家,記錄人為蔣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