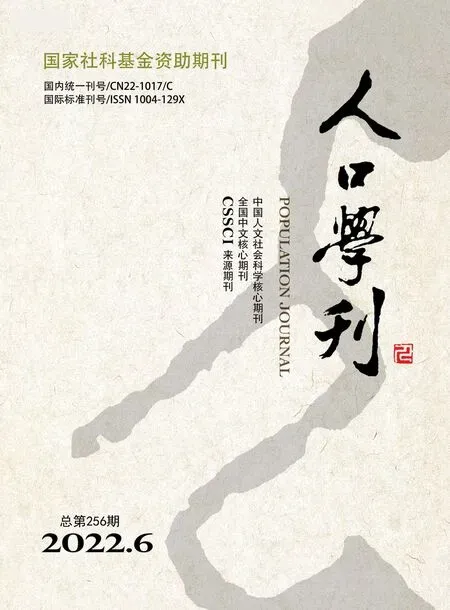日本“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實踐及啟示
周 軍,隋吉原
(江蘇理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江蘇 常州 213001)
一、引言
2010 年日本的總人口數達到高峰12 806 萬人,之后人口數量逐年下降,2065 年將跌至8 808 萬人。但日本的老齡化率卻一路攀升,2015 年達到26.6%,占總人口的1/4 以上,預計2065 年將進一步增加到38.4%,屆時日本的老年撫養比將達到1.3∶1。[1-2]同時,日本的社會保障支出費用逐年增加,1973 年是62 587 億日元,2013 年則達到1 106 566 億日元,[1]歐美型高福利、普惠型的社會保障難以為繼,因此,日本汲取了發達國家經驗,結合本國國情,制定了名為“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新型福利保障體系。
日本學界對該模式進行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對該模式存在的必要性的研究。主要從應對社會風險的角度出發,認為這是社會的健康、介護理念的發展[3]及福祉保障社會化的必然產物。[4]第二類是對該模式供給機制的研究。這些研究主張為了強化地域社會的功能,提供更靈活的服務,需要在工作機制、財政保障、利權分配等方面進一步完善。[5]第三類是跨部門合作的研究,涉及地區實踐、信息共享、管理方式、人才培養等,[6]涵蓋了社會學、經濟學、護理學、公共衛生學等不同領域。相比之下,國內對該模式的認知度并不高,已有的少量研究表明該模式作為社會福利保障政策的一環,是日本政府解決弱勢群體社會難題的重要舉措。[7-8]本文將從宏觀、微觀的角度,理清脈絡,還原日本地域綜合照護模式從基層試點到推廣全國的過程,并通過對其實踐情況的調查分析,探討其運用的實際情況,以期對我國自2016 年開始試點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福利保障的社會化進程及地方的管理有所借鑒。
二、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確立和擴容
地域綜合照護模式源自基層的實踐,被政府推進、制度化后推廣到各地區。因此,該模式的形成經歷了雛形期、確立期和擴容期三個階段。
1.雛形期
20世紀70年代,因家庭護理能力不足,護理方法不當,護理條件差等原因,不少老年患者出院后病情再度惡化的情況比較普遍,于是廣島縣御調町公立醫院在1974年開展了上門看護、上門康復訓練等服務。結果發現困擾患者及其家屬的不只是醫護問題,還有各類亟待解決的日常生活問題。針對這種情況,山口提出了醫院、政府部門合作的機構改革方案以期打破制度的壁壘。具體的方案是將政府的老年福利部門與醫院的健康管理部門整合成一個“健康管理中心”,設在醫院內以便集中、高效處理老年患者的各類事務。“地域綜合照護模式”一詞即出自山口于1984 年刊登在《厚生福祉》雜志上的文章中。[9]該模式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形成了以醫療為主、以醫療機關為先導,公私一體、獨樹一幟的服務形態。這個模式使該地區臥床老年人數量急劇減少,僅相當于同類城鎮的1/3。[10]1994 年4 月厚生省設置了對策本部,成立了老年介護、自立支援模式研究會,成員共同撰寫了報告《關于構建新型老年護理模式》,[11]這標志著該模式正式進入了官方視野。
2.確立期
1989 年日本政府推出的《黃金計劃》,提出將老年福祉與醫療相結合的照護制度的構想,要求各地區以增進老年福利為宗旨,以市、町、村為單位,以中學學區為單位設立負責咨詢和協調的居家護理支援中心,對老年介護、居家醫療實行統籌管理。1997 年2 月國會通過的《介護保險法》標志著傳統的家庭護理功能的社會化,實現了按需護理及護理的社會化。同一時期發布的《黃金計劃21》也提出要建設地區居民相互扶助的區域社會以及構建值得信賴的為老照護服務體系。《介護保險法》和《黃金計劃21》構成了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制度框架。
2008 年作為政府老年人保健增進事業的一環成立的“地域綜合照護研究會”開啟了針對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專項研究,2009 年5 月發布的《地域綜合照護研究會報告書——作為今后研討的論點的梳理》首次就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給出了定義,[12]即以住宅供給為前提,以保障安全、安心、健康的生活為目標,采取“自助”“互助”“共助”和“公助”四種方式,在老年人日常生活圈的范圍內提供包括醫療、護理、生活等在內的一體化支援服務,并強調具體實施由各地區結合自身情況而定。2011年6月國會通過的《為夯實護理服務根基部分修訂護理保險法等法案》的第1 條中出現了地域綜合照護模式一詞,這是該詞首次在法律條文中出現,[13]標志著該模式上升到了法律層面,完成了制度化。
3.擴容期
2000 年《社會福利法》成立標志著福利保障成為地域政策的核心。這部法律提倡社會福利的地域化,主張基于政府和居民平等關系的、全民參與的地域福利制度。2014 年修訂的《介護保險法》也規定生活支援不再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家政服務、安否確認、外出幫助、社會參與援助,還包括資產管理、合同簽署以及提供因家庭結構變化而喪失的家的功能等。這也意味著地域綜合照護模式擴大到了地區居民日常生活的全部。2017年厚生勞動省頒布的《為強化地域照護模式對介護保險法所做的部分修改案》以及據此修改的《社會福祉法》正式將實現地域共生社會作為地域綜合照護模式深化的目標。該模式現已提升到以構建“共生型社會”為目標的高度。[14]經過擴容,地域綜合照護模式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地域性的福利保障、地區振興的舉措,其重要性與日俱增。
三、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內涵及實踐
1.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內涵
地域綜合照護模式是以地區居民享有自立、尊嚴的生活為目標,涉及居住、醫療、保健、護理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各要素。這些要素相互聯結形成了地域性、綜合性、照護性、系統化“三性一化”的立體結構。
在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實施過程中,培育居民的區域共識、地區認同感,形成相互理解、互相扶持的紐帶,這些體現了其地域性。其綜合性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服務主體的一體化,包括官方機構、保險機構、金融機構、社會組織(NPO、社會福祉協議會、老人俱樂部、町內會)以及個人,提倡各主體之間的合作。二是服務對象的全面化,囊括了老年人、殘疾人、育兒期婦女、生活貧困者等各類社會弱勢群體。三是服務內容的精準化,即根據個體實際情況量身定制醫療、護理、預防、康復、住宅、生活支援等一攬子服務。四是服務管理的一體化,即策劃、組織、管理、監督、實施的統籌安排。五是服務形態的立體化,即提供多層次、連貫性、無縫化、可持續性的服務。進入21 世紀,與疾病共存、提高生活品質(QQL)成為主流需求,照護進一步從以醫療為中心向以生活為中心,即從“醫療完結型”向“地域完結型”轉變。地域綜合照護模式借鑒了生態學、仿生學的原理,既有自我調節功能,還可與其他系統相融合,具有發展的特性。
2.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實踐
日本綜合研究所于2014 年3 月對50 個城鎮的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建設情況進行了大規模調查,[15]各地區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地區實踐情況

續表1
因各地區老齡化程度、經濟發展狀況不同,民生需求各異,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實際情況也不同,呈現出兩大特征:
一是多樣性。有的地區發展較快,有的地區還停留在探討階段。這是由于各地區具有充分的自主權,因地制宜的結果。這些模式可分為三個類型:全面型主要以大城市、經濟發達地區為主。大城市本身社會基礎好,經濟發達,服務體系完備,能夠根據自身特長構建具有區位優勢的機制;部分型多限于中小城市、經濟較發達地區。由于少子老齡化,加之受經濟條件和人文環境所限,重點放在醫護方面;監護型多見于人口分散且老齡化程度高、社會資源不足且經濟欠發達的偏遠地區。為把有限的資源效益最大化,這些地區還有信息化的傾向。
二是多元化。加強以非營利組織為代表的社會組織的參與。事實證明這種做法可以改善居家福利保障質量,提高為民服務的精準度,也有利于服務的多樣化。在加強民間力量的同時,政府的作用并未削弱,而是將重點放在協調管理方面,發揮監督保障作用。但實踐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城市的“自助”要比“互助”容易,而鄉村則“互助”易于“自助”等。“自助”的前提是能夠購買到服務,這就需要以發達的市場為基礎,但對于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存在一定困難。而“互助”的前提是要擁有一定緊密度的鄰里關系,這對于人口流動頻繁或者鄰里關系疏遠的地方是不利的。
四、地域綜合照護模式的啟示
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具有基數大、增速快、壽齡高等特點,養老保障面臨巨大壓力。雖然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但養老服務仍是一個薄弱環節,是有待開發的“夕陽產業”“銀發產業”。為了達成國務院的《“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所提出的“為老服務多業態創新融合發展”“強化居家社區養老服務”以及“完善老年健康支撐體系”的建設目標,日本的地域綜合照護模式有以下兩方面的啟示。
1.養老服務系統化的路徑
一個模式的形成是經過了系統化的過程。而系統化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即具有多個構成要素、共同目標、相互關聯性,歷經關聯、合作、統合三個階段。因此,要構建系統化的養老服務需要三個步驟:首先,做到各服務主體內部的功能梳理和整合,如醫院不同病理科的共同會診、社區各部門的聯合等,并強化合作,形成一個獨立的服務部門。其次,醫院、社區、養老院、非營利組織、高校、企業等開展跨區域合作,并明確各合作主體的功能與職責。最后,在實踐過程中,培養各參與主體的共識,形成共通的目標意識,構建新體制內文化,整合、重構形成制度。我國可從局部試點做起,以醫院為中心,以醫療、護理為主,逐步擴大系統化的規模,最終形成覆蓋患者生活的網絡系統。
2.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
日本受福利多元主義影響,其社會福利的服務主體已多元化,分政府部門、民間營利部門、民間非營利部門、個體部門四類。而地域綜合照護模式能夠成功推廣,關鍵在于充分發揮了后三類部門的主體性。社區對我國居家養老的意義重大。我國應盡快提高居民的參與意識,鼓勵社會力量的參與,構建多元化的服務主體,形成居民參與型的管理體系,才能穩定居家養老功能。為此,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一是要提高地區居民的參與意識。現代社會文明發展進步的同時也衍生了各種社會問題。如老年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受歧視,與社會脫節等問題。對此,愛知縣豐橋市開展了鄰里互助活動。這種活動采取的是自主、自愿和力所能及的方式,提倡從身邊的小事做起,通過幫扶行為,讓所有人認識到、感受到“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相互幫扶的重要性,并由此培養了將地區的問題視作自身的事情的責任感,提升了對人生價值、生活意義的認識。
二是要發揮非營利組織(NPO)的作用。面對現代社會各類人群的多元化需求,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不能面面俱到。而NPO 能夠分擔政府的一部分職責,具有成本、效率的優勢,貼合人本主義原則,能夠滿足各類人群的多元化需求。而且NPO能夠以更靈活的方式提供志愿利他式服務,滿足個體或多或少的“需求溢出”情況。[16]
日本的實踐證明民間組織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比較敏感,提高其活動能力,以它們為主體制定對策,既有助于下情上達,又能夠有助于政府彌補管理的漏洞及迅速應對,還能夠使服務更精準化。在我國NPO、志愿者團體的公益作用也更加明顯。為此,除了要從稅制、政策、經濟上給予其支持外,還應該鼓勵其在營利約束機制內有適度的營利行為。[17]這種營利行為不是與市場爭利,而是作為補充純公益部分的一種手段,有助于其發展和公益價值的提升。應積極鼓勵社會組織的參與,形成社會組織嵌入社區治理結構,以解決多層次、多樣化的公共服務供給問題。[18]此外,隨著大數據、云技術、AI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地域綜合照護模式有向ICT化、智能化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