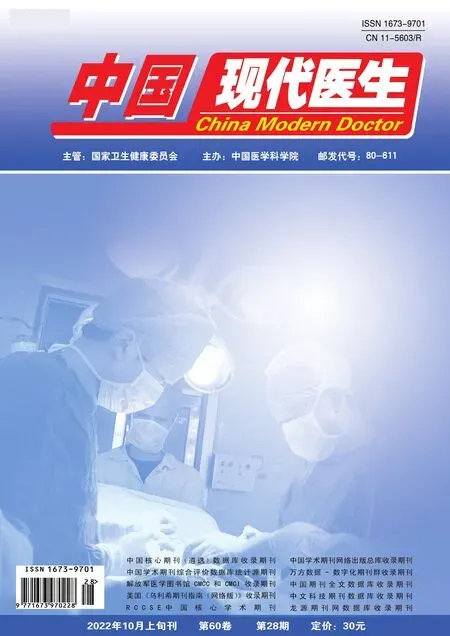糞菌移植在腸易激綜合征中的作用研究進展
李 妮 楊 卓 李淑霞
1.甘肅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學院,甘肅蘭州 730000;2.甘肅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肛腸科,甘肅蘭州 730000
腸易激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種慢性功能性腸病,在排除器質性病變的基礎上,根據羅馬Ⅲ診斷標準,反復發作的腹痛或腹部不適,且伴有排便習慣及糞便性狀的異常。根據糞便性狀的不同,羅馬Ⅳ標準將IBS 分為4 種亞型,腹瀉型IBS(IBS–D)、便秘型IBS(IBS–C)、混合型IBS(IBS–M)和未分類型IBS(IBS–U)。IBS 在全球范圍內流行,總患病率高達11.2%,且有逐年增高的趨勢。大量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女性IBS 患病率普遍高于男性,男女之比約1∶2,引起性別差異的因素目前尚無定論。目前IBS 發病原因及病理機制尚未明確,包括胃腸運動異常、內臟高敏感、腦腸軸功能異常、腸道菌群失調、腸道炎癥、細菌感染等在內的多種因素參與其中。糞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作為一種重塑腸道菌群的新型治療方式,已成功用于艱難梭菌感染的治療,在IBS 的臨床研究中引起廣泛關注。
1 腸道菌群與腸易激綜合征
1.1 正常人體腸道菌群的變化
腸道菌群龐大且復雜,一個成年人體內腸道細菌數量大致為1×1014個,約為人體自身細胞的10 倍,種類達2000 余種,包括擬桿菌門、厚壁菌門、放線菌門、變形菌門等不同細菌門,其中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占據主導地位。腸道微生物參與調控人體健康,與宿主相互依存保持平衡關系,這些寄存的微生物構成腸道菌群的微生態系統,被稱為“第二個基因組”,也有學者提出假說,由腸道菌群構建的“菌腦”可能是人體物質記憶的“第二大腦”。根據對機體的作用,細菌可分為3 類:生理性厭氧菌、條件致病菌和病原菌,而以雙歧桿菌、乳酸桿菌為代表的生理性菌群,可維護腸道生物黏膜屏障,限制病原菌入侵定植。當腸道免疫系統功能失調時,條件致病菌和病原菌過度增殖,誘導巨噬細胞向M1 型分化,促進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IL–6等炎癥因子釋放[1]。腸道中的微生物在催化酶酵解下釋放有益的短鏈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CFA),特別是乙酸、丙酸和丁酸,參與糖代謝過程為腸黏膜細胞代謝、生長提供主要能量。SCFA 作為腸道菌群和免疫系統間的溝通介質,可直接激活G蛋白耦聯受體(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GPCR)抑制組蛋白脫乙酰酶的活性,調節免疫反應[2]。現有研究表明,多糖作為腸道菌群的主要能源,通過提高碳水化合物活性酶的活性,增加SCFA 的生成,降低炎癥因子的表達,增加緊密連接蛋白(zonula occludens,ZO)的表達,調節菌群結構維持生理活性[3]。
, ,
1.2 IBS 患者腸道菌群的變化
已有研究證實IBS 患者存在腸道微生物代謝紊亂,主要表現在菌群豐度降低、多樣性減少、結構比例失調,這種改變引發腸道炎癥,導致宿主發生病理變化。有學者收集來自IBS–D 患者和健康人群的糞便樣本進行分析,發現IBS–D 患者雙歧桿菌屬、乳酸桿菌屬、擬桿菌屬豐度降低,普雷沃菌屬豐度顯著增高,推測普雷沃菌屬可能與IBS–D 高風險呈正相關[4]。Chung 等[5]在IBS 患者糞便樣本中檢測出較高比例的韋榮球菌科細菌,空腸黏膜中分枝桿菌科和奈瑟菌科細菌含量卻顯著低于健康人群。國內學者對60 例IBS 患者糞便標本進行細菌分析,發現IBS 組雙歧桿菌數、乳桿菌數、雙歧桿菌(Bifidobacterium)與大腸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數值之比(B/E 值)均低于健康組,由此推斷,IBS 患者腸道菌群定植抗性減弱,造成腸道病原體易感性[6]。不同亞型IBS 患者腸道菌群變化亦有所不同。趙娟等[7]研究發現,腸道雙歧桿菌、乳桿菌數量IBS–D 組高于IBS–C 組和IBS–M 組,但腸桿菌和腸球菌數量相反,IBS–M 組高于IBS–C 組和IBS–M 組。研究指出在IBS–D 和IBS–M 患者中,產生丁酸鹽的細菌家族水平較低,丁酸鹽積累的減少增加腸腔中的滲透負荷,最終導致腹瀉[8]。當前關于IBS 患者糞便微生物譜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可能與地理環境、統計方法的異質性有關,但包括幾個共同的趨勢,如厚壁菌門水平增加、擬桿菌門水平降低、厚壁菌門/擬桿菌門比值(F/B)增加[9]。
1.3 菌群–腦–腸軸與IBS
腸神經系統與自主神經系統、循環系統、免疫系統及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 軸)共同構成一個龐大的網絡系統,彼此間的聯系通過腦–腸軸(brain–gut axis,GBA)的反饋來實現。與宿主相關的微生物群可直接或間接通過免疫、代謝或內分泌途徑,為神經系統提供關于環境的實時信息。腸道菌群在GBA雙向調節中起重要作用,一些腸道微生物可作為“神經核調節素”影響宿主腦細胞神經元的轉錄,進而影響宿主的行為。神經營養素和它們的受體,特別是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在促進神經元和神經干細胞的存活和分化中作用突出,尤其在大腦皮層和海馬區是突觸可塑性的有效調節劑。腸道生態環境的失調使與可塑性有關的神經營養因子濃度降低,表現為焦慮、抑郁樣行為及記憶障礙的增加,然而這種過度應激反應可通過移植嬰幼兒雙歧桿菌來逆轉。研究發現,相比于新生正常小鼠,新生無菌小鼠海馬區和杏仁核BDNF 表達水平下降,血–腦脊液屏障功能受損,同時伴有腦部神經發育減慢,一定程度上腸道微生物參與機體中樞神經系統的發育[10]。過敏反應是持續腸道炎癥的結果,在GBA 中扮演著重要角色。IBS–D 和IBS–C 患者結腸黏膜組織Toll 樣受體4(toll–like receptor 4,TLR4)水平升高,免疫反應失調可能導致IBS 患者持續性低水平炎癥狀態,免疫細胞與腸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其他炎性介質也可存在于傳入神經末梢。離子通道負責神經元動作電位的啟動和傳播,電壓門控鈉通道亞型9 與內臟慢性疼痛密切相關,通過介導慢性失活鈉電流在靜息膜電位電壓下被激活,極大調節神經末梢的興奮性;在Gq/11/PKC 和Gi/o/PKA 細胞內信號通路中,持續性鈉電流使受作用于GPCR 的炎性介質明顯增加,參與炎癥誘導的機械超敏反應[11]。由此推斷胃腸道傳入神經的痛敏反應,是IBS 患者腹痛的主要機制。
2 糞菌移植治療腸易激綜合征的療效
El–Salhy 等[12]對77 例IBS 患者(FMT 治療后)的糞便進行16SrRNA 基因測序分析發現,細菌水平在FMT 后1 年發生變化,擬桿菌屬和普雷沃菌屬顯著增加,表明FMT 能夠恢復腸道菌群的多樣性,改善菌群結構。首第文等[13]研究納入28 例行FMT 治療的IBS 患者,對比IBS 患者FMT 前后菌屬差異,發現移植后糞便中疣微菌門、艾克曼菌的豐度均高于移植前;FMT 后12 周IBS 患者生活質量量表評分低于FMT 后4 周,且FMT 后4 周和12 周的IBS癥狀嚴重程度量表(IBS symptom severity scale,IBS–SSS)、胃腸道癥狀分級評分較移植前顯著下降,腹痛和排便不盡感有所改善,排便次數和糞便性狀亦接近標準。花月等[14]采用FMT 治療12 例IBS–D患者,隨訪至12 周,患者腹痛緩解率達83.33%,其他不適癥狀較前均有顯著改善,且隨訪期間未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葉小研等[15]納入19 例難治性IBS 患者接受 FMT 治療,以 Bristol 糞便性狀分型和IBS–SSS 評分為療效評定指標,治療1 個月和6 個月后糞便性狀改善有效率為 89.5%和 94.8%,IBS–SSS 評分呈遞減趨勢。Johnsen 等[16]研究顯示,治療組患者在FMT 治療3 個月后,IBS–SSS 評分下降超過75 分,但在12 個月后不再顯著。在一項隨機雙盲安慰劑試驗中,52 例IBS 患者被隨機分配到FMT 膠囊組和安慰劑組,盡管接受FMT 膠囊的IBS患者的腸道菌群多樣性增加,但3 個月后安慰劑組的癥狀改善程度更明顯[17]。以上研究初步證實FMT療效顯著,IBS 患者在行FMT 治療后臨床癥狀得到緩解且不良反應的發生較少,但仍需更多高質量的研究設計去檢驗FMT 的長期療效。
3 糞菌移植治療腸易激綜合征的作用機制
3.1 FMT 恢復腸道菌群數量和多樣性
FMT 幾乎涵蓋了健康供者腸道內的全部共生菌,通過16SrRNA 基因測序分析發現FMT 治療后患者腸道菌群多樣性增加,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菌株相對豐度增加,且FMT 治療后患者微生物群落的組成與健康供者相似。研究指出,在抗生素擾亂人體腸道菌群后,自體糞便移植可重建腸道黏膜微生物群,實現腸道結構穩態逆轉,從而恢復宿主微生態平衡[18]。El–Salhy 等[12]采用生態失調試驗分析糞便細菌,發現FMT 后菌群失調指數降低,腸道細菌譜發生改變,細菌豐度量化值從-3 到+3。FMT 治療后有益菌群產生大量有機酸,降低腸道pH 值,誘導杯狀細胞分泌黏蛋白Muc,增加腸道黏液黏度,進而提高腸道定植力。
3.2 FMT 恢復腸道黏膜屏障功能
FMT 混合著大量天然有益菌,通過與病原菌搶奪黏附位點、競爭腸道內營養、維持無氧內環境、阻斷細胞凋亡信號通路等途徑保護腸道上皮細胞的完整性,提高腸道黏膜屏障功能,對抗IBS 發生[19]。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是革蘭陰性菌細胞壁的特有成分,釋放的小分子激動劑與TLR4 相互作用,觸發促炎細胞因子,而益生菌治療能夠有效抑制LPS 誘導的腸道上皮細胞自噬,對腸道黏膜屏障起保護作用。秦謙等[20]研究發現,FMT 能夠促進硫酸葡聚糖引起的小鼠腸道黏膜屏障損傷的修復,接受FMT 治療1 周后,小鼠腸隱窩上皮細胞增加,黏膜呈愈合趨勢,腸道炎癥明顯緩解。研究還發現,FMT 治療后小鼠腸道菌群結構發生改變,乳桿菌屬顯著增多而擬桿菌屬和顫螺菌屬比例減少。分析認為,FMT 可能通過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長,維持菌群結構平衡、減輕小鼠結腸炎癥,促進腸上皮細胞緊密連接、恢復腸黏膜生物屏障功能。
3.3 FMT 提高腸道黏膜免疫水平
通過FMT 提高腸道有益菌的豐度,增加SCFA水平,維持腸道內促炎因子與抗炎因子的平衡。SCFA可直接調節TLR4 信號通路,抑制促炎細胞因子如TNF–α、IL–1、IL–8 的產生及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活化,介導固有免疫的炎癥效應。SCFA 促進參與Treg 細胞分化與增殖的轉錄因子表達叉頭蛋白3 的表達,Treg 通過釋放轉化生長因子–β、IL–10 等抗炎細胞因子發揮免疫抑制作用[21]。此外,一些腸道細菌促進抗炎Treg 細胞的增殖,分泌抑炎因子調節先天免疫。復合微生物群的重新引入可充分逆轉抗生素化合物導致的促炎和抗炎細胞因子抑制,FMT 治療后菌群多樣性恢復可激活腸道中巨噬細胞、T 淋巴細胞及B 淋巴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
3.4 FMT 調節內臟超敏反應
腸道組織存在炎癥或受到化學和機械刺激時,內臟傳入神經纖維變得敏感,中樞神經興奮過度,使內臟痛覺感受器處于高敏狀態。IBS 參與內源性疼痛處理和調節相關區域(如基底神經節)的程度更高。IBS 患者腸黏膜肥大細胞與內臟慢性疼痛傳導的神經細胞毗鄰,約70%的肥大細胞與腸神經纖維直接接觸,分泌多種神經肽,傳遞慢性疼痛。肥大細胞在應激后釋放多種活性介質,如類胰蛋白酶、組胺、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等物質,導致內臟敏感性異常。5–HT 作為中樞–腸神經系統間的神經遞質,與不同受體結合發揮生物學作用,其中5–HT3 受體可參與結腸擴張腹痛信號在延髓神經元的傳遞。研究表明,腸道菌群的免疫識別反應影響神經元信號的傳導,從而改變內臟高敏感性[22]。韓棉梅等[23]研究發現,IBS 模型大鼠接受FMT治療后,大鼠結腸組織TLR2、組胺和5–HT 表達水平顯著降低。由此推斷FMT 可通過拮抗肥大細胞表面TLR2 異常激活,抑制組胺與5–HT 釋放,避免趨化因子的產生,改變機體內臟超敏反應。
3.5 FMT 調節腸神經內分泌功能
在無菌小鼠中定植正常小鼠的腸道微生物群,通過釋放5–HT 的分泌和激活5–HT4 受體促進宿主腸神經系統神經元成熟,FMT 后使腸道神經元祖細胞的增殖能力增強。在人源化抑郁模型中,Zheng 等[24]將抑郁癥患者和健康人體的糞便菌群移植到無菌小鼠中,隨后進行行為測試,FMT 2 周后,與健康對照受體小鼠相比,抑郁癥微生物群受體小鼠抑郁、焦慮樣行為增加。研究還發現,抑郁癥患者的腸道微生物多樣性明顯失衡,菌群結構變化可能與抑郁癥存在高度相關性。由此推斷腸道刺激使中樞神經系統表現出高反應性,這種應激反應也可引起胃腸功能失調,GBA 失衡參與疾病發生。與正常小鼠相比,無菌小鼠大腦皮層和海馬中的BDNF 表達水平降低,HPA 軸反應更敏感,在神經內分泌學上,腸道微生物群可調節控制應激反應的HPA 軸[25]。Barroso 等[26]研究發現,從色氨酸中提取的代謝物與中樞神經系統產生的干擾素共同作用,激活星形膠質細胞中的芳香烴受體,從而抑制腦部炎性反應,暗示腸道微生物通過改變芳香族氨基酸水平調控宿主中樞神經功能。
4 結語
FMT 通過使用來自健康供體的糞便制劑增加腸道有益菌群的定植抗性,激發機體免疫應答,發揮治療疾病的作用,具體作用機制包括恢復腸道菌群數量和多樣性、提高腸黏膜免疫水平、恢復腸道屏障功能、調節內臟超敏和腸神經內分泌功能等方面。當前大量臨床試驗已證實FMT 在治療IBS 方面療效突出,但還需進一步的研究明確其長期療效。總之,人體腸道菌群數量龐大且復雜,人們對微生物治療機制的研究還很有限,隨著高通量測序和宏基因技術的開展,利用不同來源的數據和技術,探究相關糞便菌群微生物產物明確某些特定菌群功效,挖掘新的靶向化合物,將為IBS 及相關的胃腸道疾病提供一個有希望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