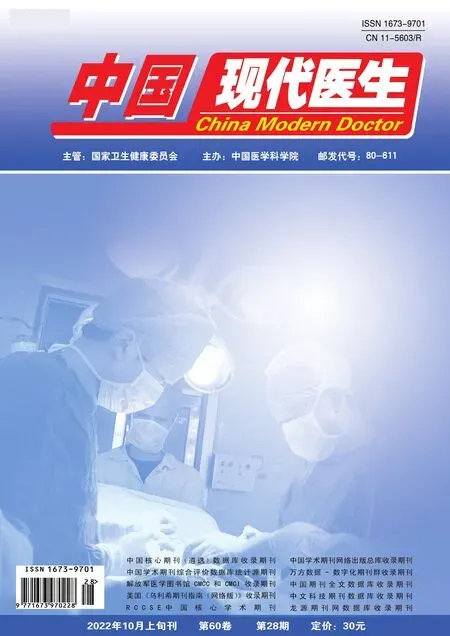肝移植治療肝癌及預后因素相關研究進展
陳澤維 俞世安
1.紹興文理學院醫學院,浙江紹興 312000;2.金華市中心醫院肝膽胰外科,浙江金華 321000
原發性肝癌是常見惡性腫瘤之一,發病率位居全球癌癥第6 位,病死率位居全球癌癥第3 位[1]。根據病理類型,原發性肝癌可分為肝細胞癌、肝內膽管細胞癌和混合型細胞癌。對于早期肝癌,有效的治療方法包括肝移植術、肝切除術和射頻消融術。中國大多數肝癌患者就診時已處于疾病中晚期,肝切除術或射頻消融術的術后復發率均高于早期肝癌患者。肝移植術能夠治愈肝臟腫瘤,消除潛在的肝硬化,同時避免因肝切除導致殘肝發生肝功能障礙,是治療中晚期肝癌的有效方法之一[2]。本文將闡述肝移植治療肝癌及預后因素的研究現狀及進展。
1 肝癌肝移植的移植標準
目前國內外應用最廣泛的移植標準仍是由Mazzaferro 等于1996 年提出的米蘭標準:①單個腫瘤≤5cm;②腫瘤數量≤3 個且最大腫瘤直徑≤3cm;③未侵犯大血管及肝外轉移[3]。符合米蘭標準的患者術后5 年生存率可達80%[4]。但米蘭標準對腫瘤的大小和數量具有嚴格的限制,未重視肝癌的生物學特性及肝臟儲備功能,導致許多肝癌患者失去肝移植機會。為使更多肝癌患者能從肝移植中獲益,全世界各地移植中心分別提出新的肝移植標準,如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UCSF)標準:①單個腫瘤≤6.5cm;②腫瘤數量≤3 個,最大腫瘤直徑≤4.5cm 且腫瘤總直徑≤8cm;③無大血管侵犯及肝外轉移[5]。該標準與米蘭標準相似,注重腫瘤的數量和大小,但擴大了適應范圍,能夠取得相似的術后生存率,給更多肝癌患者提供肝移植機會。此外還有以下多個單中心移植標準[3]。如突破腫瘤學特征的多倫多標準:①對腫瘤的大小及數量沒有限制;②無肝外轉移;③無血管侵犯;④無全身癥狀;⑤排除低分化腫瘤。納入腫瘤生物標志物的京都標準:①腫瘤直徑≤5cm;②腫瘤數量≤10 個;③異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 Ⅱ,PIVKAⅡ)≤400mAU/ml。結合我國肝癌情況的杭州標準:①腫瘤總直徑≤8cm 且腫瘤無大血管侵犯和肝外轉移;②腫瘤總直徑>8cm,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400ng/ml 且活檢提示高、中分化。其中杭州標準由我國鄭樹森院士團隊提出,創新性結合腫瘤生物學特性,并根據AFP 和腫瘤直徑這兩個獨立預后因素將杭州標準細分為A 型和B 型[3]。A 型腫瘤總直徑≤8cm,或腫瘤總直徑>8cm 但AFP≤100ng/ml;B 型腫瘤總直徑>8cm,但AFP 在100~400ng/ml;結果顯示A 型肝癌患者5 年無瘤生存率顯著高于B 型肝癌。杭州標準同樣擴大了適用范圍,其有效性已得到國內多個移植中心的驗證,但其缺點是術前需進行腫瘤穿刺活檢確定腫瘤分化程度,因此可能造成針道擴散,需慎重考慮。各類移植標準均以米蘭標準為基礎進行漸進式擴展,術后患者的腫瘤復發風險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但可為更多的肝癌患者縮短移植等待時間。我國為進一步完善肝移植受體選擇及術前評估,將米蘭標準、UCSF 標準和杭州標準列為主要標準[6]。各移植中心可結合實際臨床情況選擇最適宜的肝移植標準。
2 肝移植供體來源與處理
受公民傳統的死亡觀念、文化氛圍及宗教影響,死亡供體數量短缺是所有移植中心面臨的普遍問題。活體捐獻仍是肝移植供體的主要來源,尤其在亞洲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埃及等[7]。目前對活體供體標準沒有統一的定義,為確保供體生命安全,通常以符合下述標準作為首選:①供體年齡為20~50 歲;②與受體血型相符;③體質量指數<30kg/m2;④肝臟無脂肪變性及其他基礎疾病;⑤預計殘肝體積超過原肝體積的35%[8]。隨著肝移植技術創新及手術經驗積累,無肝中靜脈的右肝移植物已成為成人肝移植中最常用的移植類型,但小肝綜合征仍十分常見[9]。門靜脈高壓是造成小體積移植物損傷的主要因素[10]。當門靜脈壓力超過 20mmHg(1mmHg=0.133kPa)可通過半門腔靜脈分流術、脾動脈結扎術、脾切除術、脾腎分流術、腸腔分流術等術式調節門靜脈血流[11]。Hibi 等[12]首次提出通過雙葉移植技術降低受體發生小肝綜合征的風險,即從兩個供體中取出左肝移植給同一受體,經過研究發現雙葉和單葉肝移植的長期術后結果無明顯差異,但雙葉肝移植術中輸血需求增大,手術時間延長,術后并發癥增多。此外,為克服供受體血型不符問題,提高活體移植物利用率,現常采用利妥昔單抗聯合全血漿置換的脫敏方案[5,12]。但移植排斥反應尚未根除,最佳的移植免疫方案尚未確定,仍需進一步研究和探索。
相較于亞洲其他國家,我國過去10 年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事業方面得到快速發展[13]。腦死亡供體(donors after brain death,DBD)和心死亡供體(donors after cardiac death,DCD)逐步成為我國肝移植的主要來源之一。與DBD 移植物相比,DCD移植物熱缺血時間較長,缺血再灌注損傷更嚴重,移植術后發生缺血性膽道并發癥的可能性更大。有學者提出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劑可消除膽管周圍微小血管中的血栓,常溫離體保存方法可恢復膽道缺血區域,改善缺血性膽道并發癥[14]。有研究表明接受DCD 移植物的患者與接受DBD 移植物的患者相比,兩者術后生存率無明顯差異[15],但亦有研究得出相反結果[14]。現關于不同類型死亡供體移植物對患者造成的術后生存差異尚未得到證實,具體影響仍待研究。
3 肝移植術前橋接及降期治療
由于肝臟供體來源不足,肝移植隊列等待時間長,部分患者可能因肝臟腫瘤進展無法始終保持在等待名單中。橋接治療能減少活性腫瘤的大小和數目,避免患者因腫瘤進展超出移植標準而被移出等待名單,并能降低腫瘤復發風險,提高移植術后生存率[4]。治療方式包括肝動脈化療栓塞術、肝動脈放療栓塞術、經皮乙醇注射、射頻消融、局部手術切除及靶向治療等。一般肝移植術前等待時間超過6個月的患者需進行橋接治療[14]。但是目前沒有關于各種橋接治療方法有效性的大型數據研究,橋接治療方法的選擇主要由各移植中心的臨床經驗及患者腫瘤情況決定,對橋接治療成功的標準仍無統一定義,對移植術后的影響仍待研究。
降期治療適用于不符合肝移植標準的肝癌患者,通過與橋接治療相似的治療方法減少腫瘤的大小和數量以達到肝移植標準,進而加入移植等待名單。Mazzaferro 等[16]研究結果提示,對超出米蘭標準的肝癌患者經降期治療后再行肝移植的術后生存率與最初即符合米蘭標準的肝癌肝移植患者相似。目前關于降期治療的成功標準沒有統一共識,通常以符合米蘭標準作為成功標志。由于部分侵襲性腫瘤接受降期治療后仍有進展可能,降期治療成功的患者均需進行至少3 個月的觀察,定期復查腹部CT 或磁共振成像以便及時發現腫瘤進展并采取進一步治療措施[17]。對AFP>1000ng/ml 的肝癌患者,其降期治療成功的另一標志是AFP 降至500ng/ml 以下[17]。
4 肝癌肝移植術后復發的預測因素
肝癌肝移植術后復發的預測因素可分為兩大類:腫瘤相關因素和血清標志物。腫瘤相關因素包括腫瘤的直徑和數量、腫瘤血管侵犯、衛星結節和腫瘤分化程度。腫瘤的直徑和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移植時的疾病負擔。Li 等[2]研究表明腫瘤直徑>5cm 和腫瘤數量≥3 個與腫瘤復發相關。但這兩項指標無法準確反映腫瘤的生物學特性。腫瘤血管侵犯嚴重、存在衛星結節、腫瘤分化程度低均預示腫瘤復發概率大[14]。可在移植術前通過穿刺活檢進行評估,但術前穿刺活檢的準確性較低,并存在針道轉移及因腫瘤高度異質性而造成假陰性的風險。
血清標志物作為動態變化指標,可提供更精準的腫瘤生物學特性和反映移植術后復發風險,主要包括AFP、脫γ–羧基凝血酶原(des–γ–carboxy prothrombin,DCP)和中性粒細胞和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術前AFP 是一種預測肝癌肝移植術復發的有效指標。有研究報道術前經局部區域治療AFP 從>1000ng/ml降至<100ng/ml 和100~499ng/ml 的患者,其術后5年生存率分別可達88%和67%[18,19]。DCP 即異常凝血酶原,是一種因肝癌細胞對凝血酶原前體的合成發生異常,凝血酶原前體羧化不足而產生的蛋白質。研究表明與AFP 相比,DCP 對肝癌的診斷具有更高的靈敏度,但特異性稍低,術后常規檢測DCP 能有效發現肝癌的早期復發,尤其是乙型肝炎相關性肝癌[20]。研究報道DCP>400mAU/ml 是肝癌肝移植術后復發的危險因素[14]。Xu 等[21]研究發現NLR 升高與腫瘤相關巨噬細胞的聚集、浸潤及腫瘤中炎癥因子的產生有關,能促進全身中性粒細胞產生,同時提出 NLR≥4 與肝癌肝移植患者術后的總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時間和無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DFS)時間密切相關。
5 肝癌肝移植術后復發的預防
肝癌肝移植術后最常見的死亡因素是肝癌復發,大多數發生在術后2 年內,最常見復發轉移部位依次為肺(44.0%)、骨(29.8%)、肝(26.2%)和腹膜(26.2%)[22]。早期采取預防復發的措施對延長患者術后的OS 和DFS 時間具有重大意義。
索拉非尼是一種多激酶抑制劑,能直接抑制肝癌細胞增殖,并通過抑制腫瘤新生血管形成間接抑制肝癌細胞生長,現已作為晚期肝癌的一線治療藥物。研究報道索拉非尼能降低移植術后肝癌復發風險,延長患者術后的OS 和DFS 時間[19]。但Satapathy等[23]研究發現,對具有高風險因素(腫瘤直徑>5cm;腫瘤數量<3 個且至少有1 個腫瘤直徑>3cm;腫瘤數量>3 個;腫瘤血管侵犯;存在肝外轉移;存在衛星結節)的肝癌患者,索拉非尼不能提高其移植術后的OS 率和DFS 率。目前關于肝癌肝移植術后預防性使用索拉非尼的研究較少,其有效性需進一步多中心隨機對照研究驗證。
移植術后使用免疫抑制劑,如鈣調磷酸酶抑制劑能減少排斥反應發生,避免移植物損傷,但同時可導致機體免疫力下降,監測和抑制腫瘤的功能減弱。研究表示以環孢霉素為核心的免疫抑制方案會增加肝癌肝移植術后復發風險,可能是通過抑制機體免疫系統,降低機體檢測并消除血液循環中殘留肝癌細胞的功能[24]。目前他克莫司已逐步替代環孢霉素,鈣調磷酸酶抑制劑如何在排斥反應和免疫抑制間取得平衡是下一步研究重點。基于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的抑制劑西羅莫司和依維莫司為術后免疫抑制策略提供新的方向。體內外研究均表明此類藥物可通過干擾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肝癌增殖活性,同時多項研究表示西羅莫司能抑制肝癌的復發和轉移,延長患者生存時間[14]。目前mTOR 抑制劑的療效研究大多為回顧性研究,其在肝癌肝移植術后的真實療效需大量前瞻性研究證實。
6 小結
肝移植作為治療肝癌的最佳方法,應嚴格掌握和選擇適合各移植中心的肝移植指征。適當的移植物處理和受體的橋接或降期治療能夠提高患者受益。掌握術后復發的預測因素并開展適宜的預防措施能減少患者的術后復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