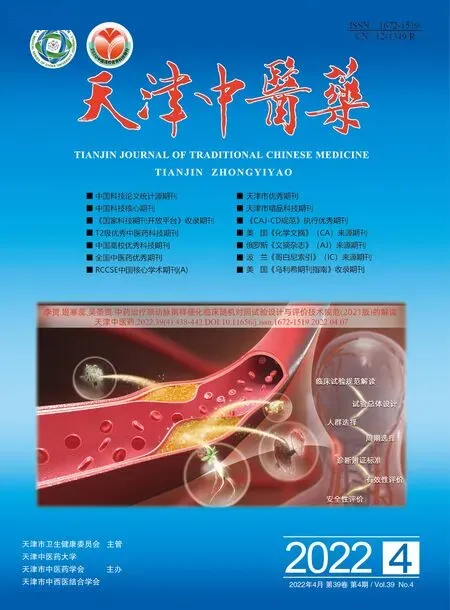從中醫整體觀談甲狀腺癌的防治*
林鴻國,黃學陽,劉大晟,蔡炳勤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血管甲狀腺外科,廣州 510120)
中醫學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涵括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調神理念和疾病防治實踐經驗,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中醫整體觀。中醫整體觀認為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既強調人自身內部的統一性,又注重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它貫穿于中醫對疾病的認識、辨證、診法和治療等各個方面[1]。甲狀腺癌屬中醫“癭瘤”“石癭”范疇,是目前發病率增長最快的實體惡性腫瘤,2015年中國癌癥中心統計的數據表明,甲狀腺癌已上升至女性惡性腫瘤的第4位,居所有惡性腫瘤的第7位,占所有惡性腫瘤的5.12%,其治療的手段主要是以手術為主的綜合治療[2-3]。西醫認為甲狀腺癌的病因暫不明確,與接觸放射線、高碘或低碘飲食、遺傳、情緒、內分泌等相關,與中醫整體觀理論相契合。因此,筆者認為以中醫整體觀理論為指導,結合現代醫學成果,可在甲狀腺癌的防治中發揮重要作用。
1 中醫整體觀理論在甲狀腺癌預防中的應用
1.1 形神合一觀—心理與生理的有機融合 中醫整體觀強調形體與精神是生命的兩大要素,兩者相互依存,互相制約,是一個有機整體。《素問·上古天真論》重視“形與神俱”“形神合一”,認為人的正常生命活動是心理和生理功能的有機融合,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中醫注重心理因素對疾病的影響,“形神合一”就是生理與心理統一性的概括。《濟生方》指出:“夫癭瘤者,多由喜怒不節,憂思過度,而成斯疾焉。大抵人之氣血,循環一身,常欲無滯留之患,調攝失宜,氣滯血凝,為癭為瘤。”認為甲狀腺癌的發生多因情志不遂,肝郁氣滯,血凝為瘤。《圣濟總錄》謂癭瘤“婦人多有之,緣憂郁有甚于男子也”,而西醫統計也表明女性甲狀腺癌發病率約為男性的3倍,皆因女性偏于情感,不耐情傷,在臟腑氣血變化的過程中,更易受情志的影響,進而引發甲狀腺癌[4]。因此,對于甲狀腺癌的預防不可忽視心理因素的影響。各種原因所致的精神過度興奮或憂郁均使人體處于高度應激,腎上腺皮質激素分泌升高,導致甲狀腺激素的過度分泌及T淋巴細胞的功能異常而發病[5]。故重養性、調精神、暢情志、平心態、持樂觀,對于甲狀腺癌的預防至關重要。
1.2 天人相應觀—人體與自然環境的統一 甲狀腺癌的發生,早有文獻指出與環境關系密切,如《呂氏春秋·盡數篇》曰:“輕水所,多禿與癭人。”同時,《儒門事親》有“頸如險而癭,水土之使然也”之說,深居大山內陸,難得海洋之物,碘元素缺乏,故生癭病者眾,指出甲狀腺癌的發生與碘的攝取量有關,但過高的碘攝入同樣易誘發甲狀腺癌[6-8]。ILIAS等[9]學者的調查研究發現,出生于碘充足地區人群甲狀腺乳頭狀癌的發生率明顯高于缺碘地區出生人群。中醫認為“天人相應”,天即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不同居住環境的人群所患疾病也各異。甲狀腺癌患者,多為內陸山區缺碘及沿海高碘人群。因此,根據中醫的整體觀思想及現代醫學對甲狀腺癌的認識,對于甲狀腺癌的預防應注重:第一,順應自然,作息規律,并鍛煉體魄。長期的熬夜、勞累可削弱人體的抵抗屏障,易感外邪,故需“起居有常”;第二,調攝飲食,做到“食飲有節”。長期的高碘或低碘飲食均影響甲狀腺癌的發生,因此需因人、因地、因時制宜,如以高碘飲食為日常的沿海地區,則適當減少碘的攝入,在低碘地區則相反;第三,避其邪氣,《黃帝內經》曰:“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甲狀腺乳頭狀癌的發生與接觸放射線密切有關,尤其在兒童時期,正氣尚未足,邪氣易侵內,更應減少接觸放射線這些“外邪”。
1.3 病理整體觀—病變互相影響和傳變 病理上的整體觀,主要表現為病變的互相影響和傳變,需注重既病防變和已病防復。既病防變暨早期診治、防止傳變。早期診治,首先要重視體檢,因甲狀腺癌的早期表現大多數是無癥狀的,在體表亦不能觸及包塊,彩超檢查有助于早期發現甲狀腺癌。而甲狀腺癌的發生可能與遺傳有關,尤其是家族性的髓樣癌,如家族中出現類似的患癌親屬,其他成員更應加強體檢,以期早期診斷。防止傳變應注意加強甲狀腺癌的基因檢測,甲狀腺癌相關的基因突變包括BRAF、RAS、RET等,甲狀腺乳頭狀癌與BRAF基因突變關系密切,有研究表明BRAF基因突變可影響腫瘤的侵襲、轉移和預后[10]。
已病防復強調的是病邪盡除,定期排查,注重調攝,謹防疾病的反復發作。如早期診斷出甲狀腺癌,筆者認為應積極的手術祛邪。對于微小癌,雖日本有部分研究學者主張分化型甲狀腺癌大部分為“惰性癌”,進展較慢,可保守觀察,但分化型甲狀腺癌也有進展快速的亞型,在不能判斷其屬于哪種亞型之前,手術祛邪,術后復查,注重調攝是最有效的方法。手術祛邪不僅效果確切,而且隨著外科技術及理念的快速發展,手術也相對安全。
2 中醫整體觀在甲狀腺癌治療中的指導
2.1 甲狀腺癌治療體系的建立—中醫辨證,西醫治法,融會貫通 甲狀腺癌尤其是分化型甲狀腺癌的治療,目前西醫主要包括手術、內分泌治療、放射碘治療。中醫整體觀思想強調以扶正祛邪、調整陰陽為主要治則,把中醫辨證論治貫穿治療始終,并將行之有效的西醫治療方法納入其中,以中西醫治療措施作為辨證施治的具體方法。如治療早期,正未虛的情況下,當以祛邪為主,首選手術;術后邪去正虛,則以中藥扶正為主,并加內分泌的治療。這里的“辨證論治”不再拘泥于望聞問切的四診資料,而是包括腫瘤分期、病理結果等現代的病情評估體系。
嶺南瘍科流派代表性傳承人名老中醫蔡炳勤教授具有50余年的甲狀腺外科中醫臨床辨治經驗,尤其對甲狀腺癌圍手術期咳嗽、聲嘶、發熱、汗出等癥均有獨特見解。筆者通過跟師學習,堅持以中醫整體觀為理論指導,以發展的目光看待中醫辨證方法和西醫治療手段,將中、西醫治法囊括其中,根據不同的發病階段和患者病情選擇合適治法。中醫整體觀理念對外科圍手術期患者的處理注重細節,講究內外結合,外治手術使痰濁之邪已去,外科術后通過中醫內治調理扶助正氣,使得患者康復更快[11]。如本科的甲狀腺癌術后患者給予吳茱萸加粗鹽炒熱外敷可有效緩解疼痛,防止肩頸綜合征;中藥沐足、耳穴壓豆等處理均可有效改善甲狀腺術后患者的睡眠,促進快速康復。
2.2 手術祛邪是治療的有效手段—手術祛邪,中西并用,相輔相成 目前手術是治療甲狀腺癌尤其是分化型甲狀腺癌的主要手段。手術祛邪,消除病變對全身的影響,切斷病變在臟腑間的相互傳變所造成的連鎖反應,通過整體治療達到消除病邪,治愈疾病的目的,也是中醫整體治療觀的具體體現。
首先,中醫學從未拒絕過手術治療,一直將手術治療作為祛邪手段和治病辦法,早在漢代就有著名醫家華佗用麻沸散將患者麻醉后進行死骨剔除術和剖腹術的記載,這是世界醫學史上最早的手術記載。19世紀后,西方在解剖、微生物、病理生理等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促進了手術治療學蓬勃發展。1909年瑞士外科醫生Kocher因在甲狀腺外科手術方面的重大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獎。而中國因歷史原因,外科手術學發展相對滯后,進而與西方醫學在解剖、手術治療等方面拉開了較大的距離。東、西方醫學發展歷史的不同導致后期有人認為手術僅是西醫治療方法的錯誤判斷。
其次,中醫整體觀表明中醫學有自身的哲學基礎與理論體系,是幾千年醫學實踐的總結,但同時它也是包容的、開放的,是以療效為最終的評估指標,所以雖基本理論體系一致,但不同年代都會誕生不同流派的大家,如金元的“寒涼派”“攻下派”“補土派”“養陰派”,中醫外科的“全生派”“正宗派”“心得派”等,百家興起,流派紛呈是中醫學百花齊放發展的迅速時期。正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對于不同的思想理念和文化成果,只要是好的知識體系和治療技術,均可把它納入其中并加以應用。現代手術治療學擁有相對完善的體系,可作為中醫學治療手段的有效補充,筆者認為對于像甲狀腺癌這一類的實體腫瘤,中醫外科當以手術切除為主要手段,祛邪務快,祛邪務盡,如何有效的祛邪并且減少復發,需要吸收西醫手術治療方法學的精髓,參考手術治療的規范、循證醫學、共識及制定的指南,中西并用,相輔相成。
2.3 中醫辨證論治思想是治療的靈魂—辨證施治,強調個體,注重平衡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認識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是中醫學整體治療觀理論體系的基本特點之一。在甲狀腺癌的治療過程中,辨證論治不單在中藥的選用方面發揮作用,它同樣可用于手術方案的選擇、內分泌藥物的調整、放射碘治療的選擇等。而個體化的治療其實就是辨證論治的精髓所在。例如手術方式的選擇,要根據腫瘤的大小、有無侵犯、有無淋巴結轉移和遠處轉移、基因有無突變等綜合考慮選擇手術的范圍,而且術中的不同情況也隨時影響著手術方式的調整;再如甲狀腺癌患者術后的內分泌治療,口服優甲樂可降低促甲狀腺激素,從而抑制甲狀腺增生,但患者的病情不同,控制的目標也不一樣,同時患者的年齡和基礎疾病也影響著其對藥物的耐受性,因此內分泌藥物治療也要根據患者病情和自身情況相應調整,這也是個體化治療的體現。縱觀甲狀腺癌領域的西醫治療方案,也是強調個體化治療,這與傳統中醫的辨證論治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在甲狀腺癌的治療中,要將辨證論治思想貫穿始終。
2.4 中醫扶正理念是術后恢復的關鍵—司外揣內,以表知里,祛邪扶正 手術是祛邪的有效手段,手術后由于刀刃所傷、邪去正虛,則需匡扶正氣,“祛邪為匡正,邪去更扶正”是中醫手術觀的核心理念[12]。中醫學思想在術后恢復中的應用可分為以下3個方面:1)術后早期:由于手術及麻醉影響,患者易出現咽痛、發熱、咳嗽、咯痰的表現,結合舌脈,如辨證為風熱上擾,治療上可疏風疏熱,常用牛蒡解肌湯或銀翹散加減;如辨證為痰濕內蘊,主要表現為咳嗽咯痰,痰稀,舌淡,苔白,則以燥濕化痰為治法,常用二陳湯加減。2)術后中遠期:一般是手術1個月后,患者有不同程度氣陰不足、陰虛或陽虛的表現,出現疲倦、汗出、心悸、怕冷或怕熱、口干、納差等,此期除了根據患者的個體化不同調整優甲樂用量外,還可予辨證使用中藥補益,如常用的補中益氣湯、歸脾湯、腎氣丸、生脈散、六味地黃丸等,促進患者癥狀的明顯改善,獲得較好的生活質量。3)甲狀腺術后未能及時就診出現甲狀腺功能減退者,中醫辨治需注重健脾補腎、溫陽固本,可選用右歸丸合附子理中湯加減。4)對優甲樂抑制治療不敏感:在臨床中,筆者發現有一小部分患者采用規范的優甲樂治療,促甲狀腺素(TSH)仍不能降低至治療目標,而辨證施治的中藥治療可有效幫助TSH降低,常用的中藥有夏枯草、牡蠣、土茯苓、山慈菇、鵝管石、白芥子、黃藥子等,中醫藥在甲狀腺癌術后患者的防復發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2.5 調補陰陽是無法手術者的有效治法—注重整體,調補陰陽,暢達氣血 甲狀腺癌無法手術者分為兩類:一為全身情況不佳、難以耐受手術;二為喪失手術機會,如腫瘤晚期,或未分化癌手術效果差。中醫學在這方面的應用主要是調整陰陽、扶助正氣、調暢情志、改善生活質量,以達到帶瘤生存、與瘤和平共處的目的,而不宜以消散大寒之品試圖有效祛邪,這樣有可能導致邪未去而正更虛,加速機體的衰亡。處于這期的患者一般體弱或因腫瘤耗傷正氣,筆者認為應以調補陰陽為主要治則,可采用六味地黃湯加人參、黃芪、靈芝、冬蟲夏草、豬苓等。無法手術的甲狀腺癌部分患者會選擇放療或靶向藥物治療等不確定的祛邪手段,均有進一步傷正可能,中醫藥治療注重整體觀,采用益氣養陰等補益之法暢達氣血、調和陰陽平衡,可選用參貝飲或增液湯隨證加減,有助于減輕化療、放療毒副反應,增強療效。
3 小結
綜上所述,中醫整體觀不僅體現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統一性,也提示著疾病在病理上相互影響、相互傳變,更是指導在疾病的防治應注重中、西醫融匯互通,司外揣內,以表知里,辨證論治,調補氣血陰陽平衡。因此,從中醫整體觀出發,在甲狀腺癌的預防中,重視飲食環境和情志心理因素,不忘疾病的傳變和影響,未病先防,既病防變,已病防復;在甲狀腺癌的治療上注重整體,中、西醫融合互通,將西醫的任何行之有效的檢查檢驗手段作為傳統中醫“四診”資料的補充,把手術、內分泌、放射碘等有效的現代治療手段作為中醫辨證施治的治療措施,以中、西醫診治方法為具體導向,融匯貫通,辨證施治,使人體氣血調暢,陰陽平衡,疾病乃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