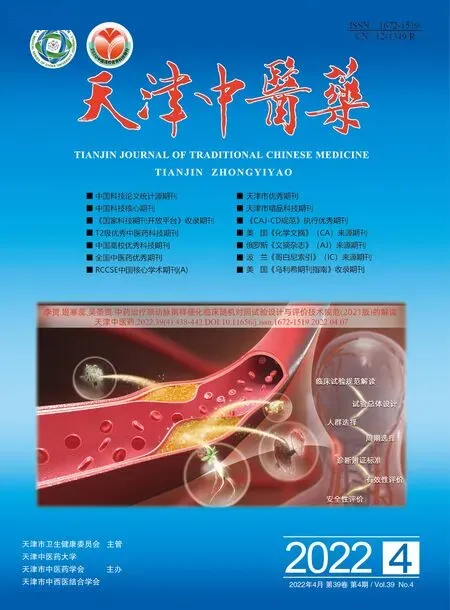益氣化濁法治療癌因性疲乏驗案舉隅
李盾,叢漉彥,付于,2
(1.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針灸科,天津 300381;2.國家中醫針灸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癌因性疲乏指與癌癥或與癌癥治療相關的疲乏感,為癌癥患者當中最為常見且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的臨床癥狀[1]。當前,相對于癌癥本身的臨床治療上,癌因性疲乏為癌癥患者所最為關注且不能忍受的癥狀。因此,癌因性疲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癌癥患者在癌癥治療過程中的依從性,且嚴重加劇患者自身的心理負擔,使得其在患病及治療期間的焦慮、抑郁狀態加重[2],進一步地加重患者的疲乏感。癌因性疲乏雖表現為以疲乏感為主癥的軀體感受,但其與心理應激呈現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趨勢,因此本病應當基于當今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進行綜合認知與臨床治療。美國國家癌癥綜合網絡(NCCN)發布的癌因性疲乏臨床實踐指南,癌因性疲乏被明確定義為“一種令人痛苦的、持續性的、主觀上的勞累感或疲乏感,與近期日常活動量不符合,但與癌癥或癌癥治療呈現相關性,且干擾正常活動功能”[3]。目前,癌因性疲乏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但迄今為止的研究證明本病與多種因素呈現明確的相關性,這些相關因素主要包括炎癥和應激介質、下丘腦-垂體軸相關的激素變化、免疫激活、神經心理障礙、節律紊亂及肌肉代謝失調等[4-7]。在癌因性疲乏的現代醫學臨床治療方面,目前臨床采用神經興奮劑以及激素類藥物,中樞神經興奮劑采用如利他林等,激素類藥物采用皮質醇激素、孕激素等針對癌癥患者以疲乏為主的癥狀進行改善,旨在提升患者的生存質量[8-9]。
1 正虛邪實為癌因性疲乏的病因病機
癌因性疲乏屬于中醫學“虛勞”范疇,是指以臟腑虧損以及氣血陰陽俱虛導致久虛成勞的多種慢性虛弱性證候[10],《素問·通評虛實論》中記載“精氣奪則虛”,闡明虛勞成因的基礎為精氣虛衰。癌癥作為一種慢性消耗性疾病,在成因上符合中醫學認知下的正氣虛弱的病理狀態,《醫宗金鑒·積聚》中強調記載“積之成也,正氣不足,而后邪氣踞之”,闡釋了人體正氣強弱為積聚產生的根本原因,本虛標實為癌癥的發病病機。
癌因性疲乏即虛勞作為癌癥的主要伴發癥狀,其病因在中醫學中定義為久病重病內耗正氣所致。基于癌癥本身所造成的虛勞,其病機為重病之人體內邪氣偏盛,耗傷臟腑之氣,導致機體五臟氣血陰陽虧損;或久病之人,其病情遷延不愈,耗傷精氣進而導致正氣難復。以上病機往往在內耗機體正氣的同時,致使痰濕瘀血之類的邪實內生,進而加重機體負擔,漸進壓制機體正氣,從而最終使得五臟氣血陰陽平衡嚴重失調,并影響患者的心理應激狀態,產生如焦慮、抑郁等消極心理狀態,嚴重降低患者的生存質量。
而立足于癌癥的現代治療手段所造成的癌因性疲乏的病因病機,有學者提出[11-12],手術治療所導致的氣陰兩傷而脾胃失調、放療所導致的熱毒內侵而化燥傷陰、化療所導致的肝腎虧虛伴脾胃不和,以上3點分別是造成臨床癌癥患者在常規診療后出現癌因性疲乏的主要病因病機。綜上,不論是腫瘤本身亦或是癌癥治療所導致的癌因性疲乏,總以正虛邪實、氣陰兩傷為主要病因病機。
2 益氣化濁法的治則精要
益氣化濁法在癌因性疲乏的治療上,以補虛瀉實,標本兼治為主要治療原則。
2.1 補虛以健脾益氣養陰為指導原則 補虛方面,重視健脾培本配合益氣養陰從本論治,以提升機體正氣為要。元代醫家李東垣在《脾胃論》中強調“人以胃氣為本”,指出虛勞論治的基本原則即“勞者溫之,損者溫之”,認為虛勞應以益氣甘溫補中之法從脾胃論治,此為對《黃帝內經》中“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的治療理論的發揮;《景岳全書》對此也提出了相似的治療原則,認為治療積聚,“只宜專培脾胃以固其本”,提出積聚的產生源于“脾胃不足及虛弱失調”,進而耗傷人體正氣引發虛勞諸證;并論述道“善補陽者,必于陰中求陽”,闡釋了其培補脾胃陽氣的同時應當配合養陰清熱之法的學術觀點。通過從陰引陽,一方面能夠輔助脾胃陽氣的化生,另一方面能夠輔助機體由于癌癥狀態下體內病理產物的蓄積所致的久郁化火,以及癌癥放化療損傷機體正氣所共致的氣陰耗傷[13]。
2.2 瀉實以化濁利濕逐瘀為指導原則 瀉實方面,重視化濁利濕從標論治,以祛除體內邪氣為要。東漢醫家張仲景首次提出“虛勞”之名,強調“補虛不忘治實”,認為虛勞的治療法則應當在補虛的基礎上注重治療體內邪實。脾主運化,為機體氣血生化之源;而在病理狀態下,脾胃虛弱則水谷精微運化輸布失司,進而出現津液代謝障礙,化生痰濕,導致痰濁結聚,機體臟腑不得濡養,從而在腫瘤的基礎上產生虛勞之證[14]。根據元代醫家朱丹溪的理論闡述,傳統醫學對癌癥中邪實方面的認知,與痰瘀病理產物具有一定的相關性,朱丹溪將癌癥的病機高度概括為“痰挾瘀血,遂成窠囊”;清代醫家王清任針對瘀血同樣闡述道“氣無形不能結塊,結塊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則凝結成塊,血受熱,則煎熬成塊”,強調瘀血在癌癥的發病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提出化濁逐瘀之法治療體內積聚之證。綜上,益氣化濁法通過健脾益氣養陰配合化濁利濕逐瘀,使得機體達到氣血陰陽調和的穩定狀態。
3 益氣化濁法的方劑配伍規律
益氣化濁法的主方在方劑配伍上,嚴格遵循君臣佐使的組方規律,詳述如下。
黃芪、白術、茯苓、山藥為君藥。黃芪甘溫,歸于肺、脾經,功在益氣升陽,白術苦而甘溫,歸于脾、胃經,功在健脾燥濕,兩者相伍激發脾胃陽氣,益陽而燥濕;茯苓甘淡,能入肺、脾經,利水滲濕而健運脾胃,山藥甘平,能入肺、脾經,補脾益胃而生津益氣,兩者相配能夠滲利水濕痰飲而不傷及脾胃陽氣。上四品總為益氣之品,旨在健脾益氣,升陽利濕,主要針對癌因性疲乏患者的疲勞主證。關于本方4味君藥的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黃芪多糖主要通過恢復細胞因子的不平衡狀態以及降低FOXp3的表達從而抑制免疫抑制作用,在腫瘤微環境中發揮抗腫瘤作用[15];白術中的蒼術內酯-Ⅱ則能夠通過激活Nrf2-ARE信號通路,減少氧化應激反應以介導抗腫瘤效應[16];茯苓多糖具有清除人體過度產生的自由基(O2-、OH、DPPH)的能力,能夠降低癌癥患者在病理狀態下,過多的自由基對于正常細胞或組織所產生的攻擊性,從而介導抗腫瘤機制[17]。山藥中的薯蕷皂苷則能夠明顯上調以Akt1為靶點的miR-149-3P,導致Akt1信號通路的抑制,從而發揮在腫瘤抑制方面的潛在優勢[18]。
廣藿香、陳皮、半枝蓮、重樓為臣藥。廣藿香辛溫,歸于脾胃之經,功在和中避穢祛濕化濁,陳皮苦而辛溫,歸于肺、脾經,功在理氣健脾燥濕化痰,兩者相伍意在化痰祛濕而健運脾胃;半枝蓮涼而微甘,歸于脾經,能夠化濕瀉濁,解毒消瘀,重樓苦而微寒,歸于肝經,能夠解毒化濁,清熱散瘀,兩者相配意在化濁解毒,利濕消瘀。上四品總為化濁之品,旨在利濕化痰,解毒消瘀,主要針對癌因性疲乏患者腫瘤方面的調節,發揮抗腫瘤效應。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廣藿香中的山奈酚能夠通過激活IRE1-JNK-CHOP信號通路誘導自噬細胞死亡發揮抗腫瘤效應[19];陳皮中的川陳皮素能夠通過激活AKT信號通路,參與自噬功能下調與細胞凋亡,降低腫瘤細胞自噬所產生的多藥耐藥性的抵抗作用[20];半枝蓮乙醇提取物則通過抑制IL-6誘導的STAT3通路的兩個關鍵靶基因cyclin D1和Bcl-2的上調,從而抑制腫瘤細胞增殖[21];而重樓皂苷通過抑制NF-κB激活,進而抑制腫瘤的生長增殖以及其血管生成[22]。
生地黃、白芍、知母、麥冬為佐使之藥。生地黃甘寒,歸于心、肝、腎經,功在清熱涼血,養陰生津,白芍苦酸而微寒,歸于肝脾之經,功在養血斂陰,養陰合營,兩者相伍意在清熱而益陰,調和陰分而從陰引陽;知母苦而甘寒,能入肺胃之經,能夠清熱生津,養營潤燥,麥冬甘苦微寒,亦入肺胃之經,能夠養陰潤燥,生津益陰,兩者相配意在清熱涼血養陰,益氣生津合營;上述4味藥總為養陰之品,旨在益陰清熱,生津潤燥,主要針對癌因性疲乏患者放化療后氣陰虧虛之證候。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地黃多糖能夠誘導NK細胞增殖進而提升NK細胞活性,間接地對腫瘤的增殖產生抑制作用[23]。白芍中的芍藥苷則能夠通過上調miR/124抑制P13K/Akt及STAT3的表達,從而誘導腫瘤細胞凋亡[24]。而知母皂苷能夠下調P13K/AKT/mTOR與Ras/Raf/MEK/ERK通路的蛋白表達,發揮對腫瘤細胞的細胞毒性作用[25]。麥冬皂苷B通過增加caspase-3和Bcl-2相關X蛋白的蛋白表達水平,增加腫瘤細胞的凋亡率及細胞形態改變,從而發揮腫瘤抑制的潛在作用[26]。
4 典型病案
患者男性,55歲,2018年10月15日初診。主訴:右側小腦中腳星形細胞瘤切除術后4個月,末次化療后2個月,疲乏無力。患者2018年5月因“突發頭暈伴口”在當地某醫院神經內科就診。查顱腦核磁共振(MRI),診斷為右側小腦中腳星形細胞瘤。2018年6月行神經導航切除術,術后持續化療1個療程后,自覺化療后疲乏感明顯,且伴隨嚴重失眠及納差,故拒絕進一步化療。刻下癥見:疲乏感甚,伴頭暈無力,四肢沉重,情緒低落,納差口渴,入睡困難及失眠多夢,早醒,小便頻數,大便干,舌淡,苔薄白,脈沉細。西醫診斷:右側小腦中腳星形細胞瘤。中醫診斷:虛勞;中醫辨證:脾虛濕蘊、氣血虧虛。治以健脾益氣,養陰化濁。予益氣化濁方,黃芪 20 g,白術 15 g,茯苓 15 g,山藥 10 g,廣藿香 10 g,陳皮 10 g,半枝蓮 10 g,重樓 10 g,生地黃 10 g,白芍15 g,知母 10 g,麥冬 10 g,因心腎不交失眠,故配合交通心腎之法,佐以酸棗仁15 g,丹參10 g,阿膠10 g。共14劑,每日1劑,水煎分兩次溫服。
2018年10月29日2診,患者述服上方后,疲乏癥狀改善明顯,入睡較易,仍多夢及納差口苦,心煩及頭暈時作,情緒低落,舌淡,苔薄白,脈沉弦。守方加減,配合和解少陽之法,予黃芪20 g,白術15 g,茯苓 15 g,山藥 10 g,廣藿香 10 g,陳皮 10 g,半枝蓮10 g,重樓 10 g,生地黃 10 g,白芍 15 g,知母 10 g,麥冬 10 g,酸棗仁 30 g,柴胡 15 g,黃芩 10 g,木瓜10 g,麥芽10 g。共14劑,每日1劑,水煎分兩次溫服。
2018年11月12日3診,患者疲乏感大幅度減輕,睡眠質量得到明顯改善,無多夢及早醒,納食口苦及頭暈好轉,情緒改善,自訴近1周自覺時有午后潮熱,仍煩熱時作,舌微紅,苔薄黃,脈細數。2診方劑予以加減化裁,配合滋陰清熱之法,予黃芪30g,白術 15 g,茯苓 15 g,山藥 10 g,廣藿香 15 g,陳皮 10 g,半枝蓮 10 g,重樓 10 g,生地黃 15 g,白芍15 g,知母 15 g,麥冬 15 g,酸棗仁 30 g,柴胡 10 g,黃芩 10 g,木瓜 10 g,石斛 15 g,女貞子 10 g,菟絲子5 g。共14劑,每日1劑,水煎分兩次溫服。
2018年11月26日4診,患者自述未見疲勞感且日活動量大幅度提升,情緒穩定,午后潮熱及煩熱改善,整體狀態趨于穩定,舌紅,苔白,脈細。效不更方,3診方劑予以降低部分藥物劑量,減少藥味,延長服藥周期以輔助后期化療,予黃芪15 g,白術15 g,茯苓 15 g,山藥 10 g,廣藿香 10 g,陳皮 5 g,半枝蓮 15 g,重樓 15 g,生地黃 10 g,白芍 10 g,知母10 g,麥冬 10 g,木瓜 10 g,石斛 10 g,菟絲子 5 g。共28劑,每日1劑,水煎分兩次溫服,并建議患者考慮進一步化療。
隨訪至2019年2月,患者疲乏感未見復發,整體狀態趨于良好,規律服用4診中藥湯劑,隨癥加減并規律化療。
按語:本案患者在術后及化療后,根據其癥狀及舌脈,考慮脾虛濕蘊、氣血虧虛。腫瘤內耗氣血,手術傷及正氣,化療攻伐脾胃,機體不得氣血濡養,氣血大虧,脾胃受伐,水谷精氣不得運化,反在內釀濕成痰,濁陰不得清化,故見疲乏。當治以健脾益氣,養陰化濁,又兼心腎不交所致之失眠見癥,故方以益氣化濁方配合交通心腎法。主方君藥之黃芪、白術、茯苓、山藥共奏健脾升陽、益氣化濕之功;臣藥之廣藿香、陳皮輔助君藥芳香化濕,而半枝蓮、重樓用以祛邪化濁,以蠲除瘀毒;佐使之生地黃、白芍、知母、麥冬,一者配合君藥以陰中求陽,補充陰液以幫扶機體化生陽氣;二者益陰而清熱,以防內熱化瘀更甚;而患者又以失眠見證,故方中配伍酸棗仁、丹參、阿膠以滋養心血,交通心腎。
2診數劑中藥服后,患者的疲乏癥狀已明顯改善,因內虛得補,故可兼顧患者兼證。因患者久病,情志不遂,故情緒抑郁、頭暈煩躁伴口苦脈弦,故采取小柴胡湯之君藥柴胡、黃芩以和解少陽,疏肝解郁;久郁肝胃不和、脾虛不運,則癥見食欲不振,故佐以木瓜、麥芽健脾利濕。
3診患者前證趨于穩定,因腫瘤內耗氣血,損陰及陽,故患者癥見陰虛內熱證時作,法當調補陰陽又忌用藥滋膩礙于脾胃,則方中配伍石斛、女貞子滋陰清熱,菟絲子補腎益氣以陽中求陰,上藥即能調補陰陽,又補而不滯,則患者陰虛內熱之象得到顯著改善。
4診患者整體癥狀以趨于良好,陰陽趨于平衡,考慮患者仍需進一步化療,故部分降低藥物劑量及藥味使用,令藥力平緩持久;微微加大半枝蓮、重樓劑量,一則考慮患者正氣來復,瘀毒留戀,二則上述兩味藥具有在現代藥理學研究中所明確證實的抗腫瘤效應。經治,患者諸證明顯改善,陰陽持恒,精神來復,生活質量得到明顯提升,能夠進一步采取抗腫瘤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