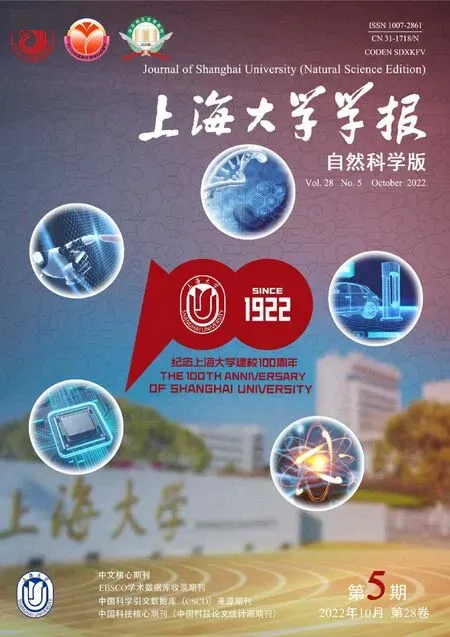創面瘢痕形成機制研究進展
竇涵鈺,崔白蘋,丁小雷
(上海大學醫學院,上海 200444)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總面積約1.5~2.0 m2,占體重的5%~15%,可保護組織器官免受理化傷害、病原體的入侵,以及防止水分過度丟失[1].人的皮膚主要由表皮、真皮、皮下組織三部分組成.毛發和腺體等附屬物來源于表皮,根植于真皮層.成纖維細胞、巨噬細胞和肥大細胞是真皮組織的主要組成細胞.真皮以下是高度血管化和神經支配的皮下脂肪組織.
皮膚作為人體的第一道防線,常因物理性、機械性、生物性和化學性等因素而發生各種損傷(統稱為創面).創面愈合需要多種細胞、細胞因子和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ECM)時空協同完成.當皮膚受損時,傷口附近的成纖維細胞被激活并合成分泌大量的膠原纖維,同時包括巨噬細胞在內的炎癥細胞分泌炎癥因子和生長因子協同啟動修復反應.當損傷較小時,細胞外基質在修復中短暫沉積,創面可以快速有效愈合;然而,如果損傷比較嚴重或者反復受損,細胞外基質沉積,纖維結締組織大量增生,就會形成堅硬的、形狀不規則的疤痕.病理性瘢痕可以分為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前者在原始傷口邊界內發展,易隨時間消退,而后者則會無限制生長形成瘢痕疙瘩[2].在發達國家,每年大約有一億人患有與疤痕有關的疾病,僅在美國抗疤痕藥物的市場就高達120億美元,已成為世界公共衛生和經濟的重大威脅[3].
1 創面愈合與瘢痕形成
創面愈合是創傷后維持皮膚完整性的重要生理過程,正常的創面愈合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主要分為3個連續且重疊的階段:止血/炎癥期、肉芽組織增殖期和重塑期[4],在創面修復的任何階段出現異常都可能會導致瘢痕的產生.止血階段的血小板功能紊亂會增加纖維粘連蛋白和肉芽組織產生,引起傷口組織的過度增生,導致瘢痕形成.傷口局部的炎癥增強,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TGF-β)濃度增加會導致病理性瘢痕的產生.成纖維細胞和巨噬細胞對膠原沉積和ECM的重塑也會導致瘢痕形成[5].近期研究表明,成纖維細胞和巨噬細胞之間可以通過TGF-β相互作用,因此纖維化程度可能是由成纖維細胞和巨噬細胞的旁分泌相互作用介導的纖維化與溶解活性的平衡決定的[6].
2 皮膚成纖維細胞主導創面瘢痕形成
創面愈合的結果分為完全組織再生和纖維化修復(形成瘢痕).在早期哺乳動物胚胎中,背部皮膚可以實現完全再生,但在人類妊娠晚期之前的某個階段喪失了這一再生功能[7].與正常皮膚相比,瘢痕沒有毛囊、腺體等真皮附屬物,且伴有過量的膠原沉積,強度小于正常皮膚[8].瘢痕的細胞外基質的重組有別于正常皮膚的多孔晶格組織——類似于“籃子”的編織結構,而成纖維細胞則是合成和重組細胞外基質導致瘢痕增生的關鍵性細胞.
2.1 成纖維細胞的不同亞型及其在瘢痕形成中的作用
不同成纖維細胞譜系在皮膚發育、體內平衡和對急慢性炎癥的反應方面均不同.不同的成纖維細胞譜系決定了皮膚發育和修復中的真皮結構.為了全面理解成纖維細胞在創面愈合和瘢痕形成中的作用,需要了解不同的成纖維細胞類型及功能.
2.1.1 根據功能分類
在小鼠背部皮膚中存在En1譜系陽性成纖維細胞(Engrailed-1 positive fibroblasts,EPFs)和En1譜系陰性成纖維細胞(Engrailed-1 negative fibroblasts,ENFs)[9].EPFs是造成皮膚疤痕和黑色素瘤生成的主導者,而ENFs不會導致纖維化瘢痕.在胚胎發育階段,ENFs占真皮成纖維細胞的95.5%,EPFs占比不到1%.在皮膚發育過程中,從ENFs主導逐漸轉變為EPFs主導,皮膚也從組織再生轉變為瘢痕形成.除去EPFs可以減少傷口中結締組織沉積,減少疤痕形成,并減少黑色素瘤生長.近期研究發現,選擇性抑制成纖維細胞Yes相關蛋白(Yes-associated protein,YAP)信號可以阻止En1的激活,促進ENFs介導的傷口修復,減少纖維化和疤痕生成[10-12].與背部皮膚類似,在小鼠口腔真皮中存在Wnt1譜系陽性成纖維細胞(Wnt1 positive fibroblasts,WPFs)和Wnt1譜系陰性成纖維細胞(Wnt1 negative fibroblasts,WNFs),其中WPFs引起ECM沉積.
通過時空單細胞測序分析人的不同功能真皮成纖維細胞亞群,發現真皮成纖維細胞至少可以分為4類:位于上層真皮的lin?CD90+CD39+CD26?成纖維細胞,并表達COL6A5;位于下層真皮的lin?CD90+CD36+成纖維細胞,與脂肪前體細胞共表達CD90和CD36標記物;位于整個網狀真皮的lin?CD90+CD39?RGS5+和lin?CD90+CD39+CD26+成纖維細胞[13].通過單細胞分析特性皮炎患者的皮膚發現,COL6A5+COL18A1+成纖維細胞亞群與T細胞和炎性分枝狀細胞相互作用參與皮膚炎癥的進程[14].
2.1.2 根據空間位置分類
真皮成纖維細胞亞群根據不同的空間位置分為上層乳頭真皮(papillary dermis,PD)成纖維細胞和下層網狀真皮(reticulate dermis,RD)成纖維細胞,它們有不同的形態特征及特性[15].乳頭狀成纖維細胞通常是細長的紡錘形狀,網狀成纖維細胞則是方正拉伸的形態[16].已有研究發現,乳頭狀成纖維細胞是形成毛囊所必需的,網狀成纖維細胞會在傷口處表達α-平滑肌肌動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產生ECM,最終導致纖維化發生[17].PD和RD受不同信號調控,Wnt/β-連環蛋白和Sonic hedgehog(Shh)可以刺激PD增殖和ECM的重塑,而RD對表皮轉化生長因子(TGF-β)信號產生反應[16].
2.1.3 根據表面標記分類
為了確定不同成纖維細胞亞群的功能和基因表達上的差異,需要不同的分子標記.在人和小鼠的真皮中,CD39在乳頭狀真皮中上調,CD36在下層網狀真皮組織中上調.CD90+CD39+成纖維細胞亞群富集在真皮上層,參與上皮化;CD90+CD36+成纖維細胞亞群則富集在真皮下層,更多參與疤痕形成.已有研究者通過單細胞RNA測序技術來研究皮膚成纖維細胞的異質性,根據表達標記物將人真皮成纖維細胞分為分泌乳頭狀、分泌網狀、間充質和促炎癥4個亞群.在瘢痕疙瘩中,間充質成纖維細胞亞群的百分比顯著增加.相關功能研究表明,間充質成纖維細胞是瘢痕疙瘩膠原過度表達的關鍵.在纖維性皮膚病硬皮病中也發現間充質成纖維細胞亞群增加,這表明間充質成纖維細胞參與皮膚纖維化[10].
2.2 成纖維細胞粘附在瘢痕形成中的作用
2.2.1 肌成纖維細胞與ECM粘附
轉化生長因子(TGF-β)是激活成纖維細胞最常見的細胞因子,在創面愈合的炎癥階段,炎癥細胞分泌TGF-β,誘導成纖維細胞向肌成纖維細胞轉化,并合成大量ECM成分,如Ⅰ型和Ⅲ型膠原、纖連蛋白、層粘連蛋白和其他基底膜蛋白.目前普遍認為,瘢痕形成主要是由肌成纖維細胞分化介導的,肌成纖維細胞持續激活會導致組織攣縮變形產生大的疤痕[18].肌成纖維細胞的收縮力主要是依賴于肌成纖維細胞與血管和過度沉積的ECM粘附形成的肉芽組織[19],成纖維細胞對肉芽組織的牽拉導致組織攣縮[20-21].
成纖維細胞在微環境的影響下,可以將機械信號轉為生物信號來調節纖維化反應[22].已有研究表明,成纖維細胞可以通過細胞表面的整合素受體與基質蛋白結合,來調節細胞外基質的重塑.整合素介導的成纖維細胞與基質的粘附通過整合素-FAK-Rho GTP酶途徑完成[23].整合素聚集并激活粘著斑激酶(focal adhesion kinase,FAK),FAK可以介導成纖維細胞遷移,導致瘢痕增加[24](見圖1).

圖1 成纖維細胞介導瘢痕形成過程Fig.1 Process of fibroblast mediated scar formation
2.2.2 成纖維細胞間粘附
除了細胞與基質之間粘附,成纖維細胞之間的粘附對于傷口收縮和瘢痕形成也十分重要.皮下筋膜由疏松的網狀結締組織構成,在皮膚和體內組織器官之間形成一層較薄的無摩擦界面.已有研究發現,皮膚損傷會引起筋膜成纖維細胞集體遷移,使皮膚逐漸收縮最終形成疤痕[25],遷移的成纖維細胞是在胚胎早期表達Engrailed-1的EPFs.EPFs聚集需要一種粘附分子,細胞粘附又是一個依賴鈣的過程.鈣粘蛋白是跨膜蛋白,可以通過粘附連接將細胞結合起來[26].當皮膚受損時,筋膜EPFs會上調N-鈣粘蛋白,促使筋膜EPFs向傷口中心集體遷移并聚集.大量成纖維細胞產生緊密的膠原纖維,重塑結締組織,最終形成疤痕,使組織柔韌性降低.減少N-鈣粘蛋白表達,可減小疤痕面積.
在筋膜EPFs中顯著高表達連接蛋白Cx43,Cx43協調EPFs集體遷移和筋膜基質移位進入傷口,從而介導疤痕形成[27].Cx43可能是N-鈣粘蛋白上游的轉錄因子,敲除Cx43會降低N-鈣粘蛋白水平[28].已有實驗結果證明,TGF-β通過Smad途徑誘導Cx43的表達,通過Erk/MMP-1/膠原Ⅲ途徑促進瘢痕形成[29].
3 巨噬細胞通過免疫反應調控創面瘢痕形成
巨噬細胞由骨髓產生,在外周血中循環或遷移至幾乎每一個組織,是人類先天免疫和后天免疫的重要效應細胞[30].巨噬細胞在傷口修復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如清除死亡細胞、碎片和病原體,通過細胞外基質沉積再血管化和傷口再上皮化.巨噬細胞在創面愈合中為傷口提供關鍵的信號分子,巨噬細胞功能障礙會使Ⅰ型和Ⅲ型膠原沉積增加,肌成纖維細胞活化增殖,進而影響正常的再生過程,甚至會促進纖維化的發展[31].
3.1 巨噬細胞譜系和表型可塑性
巨噬細胞分為組織常駐巨噬細胞和單核細胞衍生的巨噬細胞[32].巨噬細胞將抗原遞呈到免疫活性T細胞,啟動適應性免疫反應[33].巨噬細胞是組織修復各個階段中最豐富的炎癥細胞之一[34],巨噬細胞被招募到損傷部位后開始清除細胞碎片和壞死組織,還可以分泌蛋白酶和促炎介質防止病原體的入侵.
根據細胞的表面標記,巨噬細胞大致可以分為M1型和M2型.M1巨噬細胞可以被干擾素-γ(interferon-γ,IFN-γ)和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激活,產生大量的促炎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如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TNF-α和其他傷口愈合初始階段的介質,因此M1巨噬細胞被稱為促炎巨噬細胞.M1巨噬細胞具有很強的吞噬能力,可以吞噬凋亡的中性粒細胞,清除傷口中的病原體.而選擇性激活的M2型巨噬細胞被IL-4、IL-13激活,分泌抗炎效應物,如IL-10、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等,因此M2巨噬細胞被稱為抗炎巨噬細胞.M2巨噬細胞可以調節炎癥反應,參與后期傷口修復過程[35-36].
巨噬細胞持續被促炎因子激活和M2型巨噬細胞功能受損出現在各種慢性炎癥環境中,包括慢性傷口[37]、肺部炎癥[38]、動脈粥樣硬化[39]和胰島素抵抗[40-41].M2型巨噬細胞持續激活則會導致組織纖維化和瘢痕形成[42].另有多項研究表明,傷口局部環境可以誘導巨噬細胞從M1表型轉變為M2表型,這可以讓巨噬細胞成為抗瘢痕的一個治療靶點[43].
3.2 巨噬細胞對創面愈合與瘢痕形成的調控作用
除了成纖維細胞,巨噬細胞也在創面修復和疤痕形成中起重要作用.在創口早期主要分布的是M1型巨噬細胞,在創傷后7~14 d達峰,而M2型巨噬細胞主要分布在晚期傷口和瘢痕的增生期,在創傷后14~28 d達峰[44].巨噬細胞介導成纖維細胞增殖、肌成纖維細胞分化和膠原沉積.巨噬細胞的數量和表型變化會影響創面愈合過程并且決定疤痕的形成.當巨噬細胞總數減少,表型由M1轉為M2,說明傷口從以再上皮化和肉芽組織發育為主的修復階段進入穩定階段[45],若創傷持續存在,M1型巨噬細胞在較長時間內不向M2型巨噬細胞轉變,就會導致創面愈合時間延長(見圖2).

圖2 巨噬細胞介導瘢痕形成過程Fig.2 Process of macrophage mediated scar formation
巨噬細胞通過肌成纖維細胞分化影響膠原合成,或通過分泌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直接調控ECM成分[36].MMPs可以降解基質中各種類型的膠原蛋白,維持正常真皮結締組織量的相對穩定,在傷口修復過程中還有清除壞死組織、促進細胞遷移和組織重塑的作用.巨噬細胞可以通過向肌成纖維細胞分化參與瘢痕的形成[40].巨噬細胞可以分泌MMP-10來應對皮膚損傷[39],在MMP-10-/-小鼠受損皮膚中,巨噬細胞數量和移動情況正常,但瘢痕較重,說明巨噬細胞分泌的MMPs在皮膚損傷修復過程中調節了組織重塑并減輕了瘢痕的形成[40].
在創傷早期階段,巨噬細胞在IFN-γ和TNF-α的作用下分化為M1型,在瘢痕愈合晚期和增生性瘢痕形成中會分離出較多的與M2型巨噬細胞相關的TNF-β,使M2型巨噬細胞在創面愈合過程中增加,在重塑階段達到峰值,在增生性瘢痕形成過程中減少.若創傷持續存在,M2型巨噬細胞參與促進纖維化形成并分泌TNF-β,間接促進ECM生成和成纖維細胞向肌成纖維細胞分化[46].巨噬細胞和成纖維細胞本身來源的TGF-β可以作為纖維化中巨噬細胞與成纖維細胞相互作用的信號,促進成纖維細胞活化.M1型巨噬細胞可以產生IL-6活化成纖維細胞,活化的M2型巨噬細胞可以產生驅動成纖維細胞增殖的因子,如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巨噬細胞還可以分泌IL-10抑制肌成纖維細胞分泌α-SMA和Ⅰ型膠原蛋白(見圖3).成纖維細胞和巨噬細胞可以通過參與ECM的調控實現相互作用,成纖維細胞可以沉積和組織ECM,而巨噬細胞則可以降解和修飾ECM[6].

圖3 瘢痕形成過程中成纖維細胞與巨噬細胞的相互作用Fig.3 Interaction between fibroblasts and macrophages during scar formation
3.3 以巨噬細胞為靶點治療增生性瘢痕
在增生性瘢痕性動物模型中,巨噬細胞的全身性耗竭有效地抑制了創面愈合亞急性期的增生性瘢痕形成,并下調M1相關細胞因子(TNF-α,IL-1β和IL-6)和M2相關細胞因子(TGF-β1,IL-10和IL-1α)[47].在巨噬細胞選擇性耗竭的轉基因小鼠模型中,發現巨噬細胞的消耗可顯著減少炎癥期血管化肉芽組織的形成和上皮化,最終減少肉芽組織和瘢痕形成[48].相反,也有研究表明,在修復過程之前和整個修復過程中,使用白喉毒素驅動溶菌酶消耗巨噬細胞的策略會導致創面愈合受損[22].如果沒有巨噬細胞,傷口就無法清除中性粒細胞,同時就沒有高水平的促炎細胞因子使得轉化生長因子β1表達降低[49],從而減少肌成纖維細胞分化導致的傷口收縮減弱,以及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表達滯后導致的血管生成減少[49].近期研究表明,肥胖會上調S100A9激活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進而抑制巨噬細胞向M2型分化,導致皮膚損傷不能快速修復,形成肥胖相關的皮膚炎癥.若抑制S100A9則可治療肥胖相關皮膚炎癥,促進創面愈合[50].
綜上,M1巨噬細胞的存在時間延長和/或表達增加,M2巨噬細胞數量減少和/或M2活化增加,都可以改變傷口炎癥的微妙平衡,從而顯著影響修復過程.從M1表型到M2表型轉換的任何失敗都會導致炎癥增加和大量TNF-α的分泌,從而抑制慢性傷口的愈合.
4 展望
瘢痕形成和完美再生是創面組織修復過程中兩個完全相反的結果.在哺乳動物胎兒早期存在無瘢痕愈合和再生,隨后在胎兒晚期和新生兒早期之間消失.這可能是由于胎兒的免疫反應較弱和En1譜系陰性成纖維細胞介導皮膚修復,從而產生較低水平的免疫細胞而達到完全組織再生性修復.然而,一些低等生物如蠑螈卻一直具有完美再生的能力,為什么哺乳動物在進化過程中失去了這種能力?可能是為了減少病原體感染而進化的超越正常皮膚生長速度的快速修復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卻留下了不可避免的問題——瘢痕.因為瘢痕的形成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受不同類型的細胞、細胞因子、信號通路、基因調控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目前臨床上尚缺乏治療瘢痕的特效藥.
成纖維細胞和巨噬細胞一直被認為是瘢痕形成的主要參與細胞,通過研究成纖維細胞的不同亞群和不同修復階段巨噬細胞類型,以及成纖維細胞和巨噬細胞在創面修復過程中的相互作用,可以使研究者更深入了解創面瘢痕形成的機制.如果可以抑制成纖維細胞激活和促進M1型巨噬細胞向M2型巨噬細胞轉化,就可以減少瘢痕形成,促進慢性炎性創面愈合.斯坦福大學的相關研究發現,阻斷Engrailed-1激活和抑制En1陽性成纖維細胞的YAP信號,使得En1陰性成纖維細胞可促進皮膚再生,并完全恢復正常的毛囊、腺體、基質超微結構和機械強度[11-12],在不久的將來有望通過藥物實現無瘢痕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