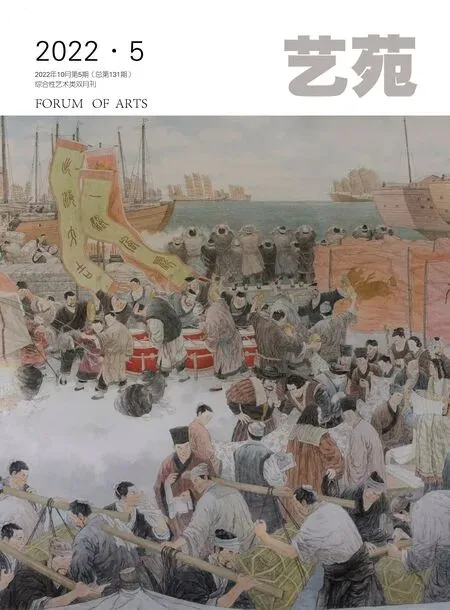基于電子界面的想象
——論數碼屏幕影像的觀看機制
廖曉宇 潘可武
按照法國電影學者安德烈·戈德羅(André Gaudreault)與菲利普·馬里恩(Philippe Marion)的說法,數字媒介的出現帶來了電影的第八次死亡。[1]16在數字轉折的背景下,電影的死亡預言更多的是指電影失去了它的銀幕地位、媒介特性或是文化優勢,而不是媒介和產品本身的消亡。由于失去了其本身的獨特性,如它的固定裝置(膠片、放映機、銀幕、黑暗影院等),又獲得了其他圖像媒介的標準,電影逐漸走向自身邊界的不確定性。一方面,面對籠統而混雜的“后電影狀態”,電影重新回到自己的傳統領域之中。經典電影定義的空間-技術-敘事邊界被重新把握,強調電影場域的純潔性以及“電影狀態”在非日常狀態下的主體效果。[2]85-92另一方面,比起反復重申的特性,電影轉向基于對變化和差異的接受,不再將自身設定為一個封閉的存在。在這場沖破其工業、媒介、敘事和體驗邊界的運動中,電影沒有走向削弱,而是超越和重生。放在一種同時代的特殊經驗中來看,我們所遭遇的并非是滯后話語給行為設定的基本范圍,即“這樣做了才能稱之為看電影”。更多的是,“看電影,無論在哪”的這種現象已經來到我們身邊并且實實在在影響了我們。
數字時代的影像呈現出一種移動和分散的狀態,不斷擴展到其傳統的裝置和環境之外,因此變得隨處可見。影像在電影院內、電視機上、平板電腦里,還有隨身攜帶的手機中。這些設備不僅能收看各種豐富精彩的影像類型,并且都支持播放同一個影像。弗朗西斯科·卡塞蒂用“移置”(relocation)一次來概括電影向其他設備和其他環境移動的過程。他認為,電影在“移置”中保證了電影經驗的延續,“由于一種新的支持或新的設備——一種經驗在其他地方重生,而以前的媒介的生命,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完整性繼續存在”[3]28,從而把電影從它的死亡魔咒中解救出來。在觀眾一邊選擇觀看哪部電影,一邊選擇在何處、以何種設備觀看的過程中,電影體驗的“是什么”和“如何”之間的深刻裂痕被標記出來。正如卡塞蒂所言,電影不再是完整、固定和預設的一種東西,“電影變成了電影對象和觀看電影的方式兩種東西”[3]54。
在此前提下,電影影像的一組“不變與變”浮現出來:不變的是不觸碰任何媒介的影像作品本身以及純粹的“觀看”行為,而變動的是所謂的觀看界面以及環境空間。如今,占主導地位的主要有四種媒體/界面:電視、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和LED媒體幕墻。屏幕化的影像集中在可移動性強的便攜式設備上:各種電腦與智能手機。因此,此種影像結構性地具備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內在特性,它與眼睛的交叉點就是不可或缺的“界面”——一塊自發光的屏幕。屏幕影像的觀看并不是直接的、自然的“看”,而是基于電子界面的觀看。人類在日常生活中首先面對的是以電子屏幕為中介的“界面”,然后再是藝術作品或者世界。影像通過界面呈現,或者說只有透過界面,我們才能觀看影像。這樣一種脫離直觀感受的“界面-開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觀看模式?本文以數字時代的“電子界面”切入點,從界面生成、界面縫合、觀看主體三個角度探討移動影像的觀看機制。
一、界面之域:從自然生成到技術生成
我們通過所見的東西來理解世界:無阻隔地直觀或者透過某些東西去看。對于自然而言,人類的習慣是一種直接觀看。無論是可觸碰的樹木還是難以觸碰的云朵,人與物之間并沒有另一個人造物的阻隔(眼鏡頗為例外,可以看做是維持視線的透明性工具),人眼看到的就是事物呈現出的樣子。在藝術領域,人類從來就無法做到直接觀看,無論是繪畫、雕塑,還是電影、電視、手持設備,如果沒有另外一個人造物作為中介,藝術品則無法呈現給我們。因此,這個“人造物”就是界面。界面大多數時候呈現為屏幕,而屏幕“是一扇‘虛擬之窗’,改變了既有空間的物質性,加入新的視孔,大大改變了我們有關空間乃至時間的觀念”[4]192。最早的界面或許是“窗”,它框定了一個空間,使其在人腦中轉化為一個二維平面的想象,由此改變了人對于窗外世界的感知。如同波德萊爾所言:“在日光下所能看到的東西,總是不如一面玻璃之后發生的事情,令人產生興趣。”然后,是繪畫的界面。文藝復興典范畫家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435年有關繪畫和透視的論文《論繪畫》當中提出了這個著名理論,即把繪畫的方形邊框“看成”一扇窗,畫框就是通往世界的窗口。電影的銀幕是一個經典界面,一方面繼承了西方繪畫中畫框的特點,另一方面帶來了可移動性,銀幕中的圖像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窗、畫框、銀幕,這些作為屏幕的界面通常被看作是通往更大空間的窗口,“屏幕空間通常被習慣性地理解為更廣闊的圖景空間(scenographic space)的一部分”[5]157。雖然屏幕空間是唯一可見的部分,但更廣闊的圖景實際存在于屏幕之外,外面的區域與我們身處的世界息息相關。屏幕界面中圖景的生成方式或是自然、或是主觀自然,或是客觀現實的機械復制,它們都不可避免地保留著客觀“現實”或者自然的痕跡。
與自然生成的界面不同的是,電子屏幕的界面生成建立在深刻的技術條件上。窗、畫框、銀幕的界面依賴的是改造自然材料的技術,一旦這些界面生成,它們就足夠生硬與確定,規定著最終的藝術呈現。當畫家在畫布上描下最后一筆,那么他就可以宣稱這是作品的“最終定稿”。但電子界面,或曰“人機交互界面”包含著技術的先驗邏輯。計算機技術使“所有媒體都被轉化為可供計算機使用的數值數據”[5]88。馬列維奇指出,界面的數值化呈現帶來的重要結果是其中呈現的一切都變得可以被編程(programmable)了。于是,“草稿”和“定稿”之間的區別被懸置了:不再有一個“確定的文本”,因為其每一步都可以被無限地再加工。這一點很好地體現在影像的草根實踐中。2009年,一位名叫凱西·普格(Casey Pugh)的美國導演要求數千名網民按照自己的創意拍攝《星球大戰IV:曙光乍現》中的場景。網友們在提供的15秒短片中翻拍、模仿、惡搞原作。這一場對電影的“褻瀆”實踐在短短幾個月內贏得了巨大的關注度,并在2010年獲得了艾美獎的互動媒體杰出創意成就獎。最后,這些小片段經過剪輯,組合成了一部長達124分鐘的電影,命名為《星球大戰未刪減版》(Star Wars Uncut: Director's Cut)。這是一部不需要正式拍攝,沒有正式劇本也沒有導演的電影。在賽博空間中呈現的文藝作品,不論是經典原文本,還是互聯網上形形色色的衍生作品,都獲得了技術生成的屬性。依賴計算機技術和算法的修改與二次創作,影像的創作通常會呈現出兩種版本:官方版本和衍生出的民間版本,后者包括電影解說、同人剪輯、幕后花絮等多種類型。技術賦予了每個人將現有的原材料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力,通過剪輯、配音、摳像、調色等手段,大量的民間“超文本”不僅有趣,而且還有著洞察力,揭示了官方版本潛在的“被壓抑”的內容,有時候甚至比官方版本更受歡迎,更加深入人心。
不存在“確定的文本”暗示了在數碼屏幕影像的觀看中,觀看者深受算法的控制。自然或者客觀現實退居其次,代數算法的力量篡改著電子界面的屬性。界面不再像經典屏幕(窗、畫框、銀幕)所反射的那樣,不可逆轉也不可侵蝕。界面變得具有任意性,被賽博空間的技術“代理人”(程序、預設等)與主體(創作者、傳播者、觀看者)共同統治。從日常經驗的釋義視線出發,我們遭遇了電子交互界面所帶來的第一條邊界的破壞,即“‘真實生活’及其機械模擬之間:技術破壞著‘自然的’生命-現實和‘人造的’現實之間的區別”[6]163。
二、界面縫合:從客觀現實到主觀幻象
何謂縫合?“縫合”一詞最早由拉康提出,用來說明主體生成語言意義的過程。隨后,法國理論家讓-皮埃爾·歐達爾(Jean Pierre Oudart)將“縫合”的概念引入電影研究當中,縫合理論逐漸在電影領域內重獲生機。縫合代表著缺失感被滿足的過程,一般想象的模式是將外部刻寫入內部,從而抹去自身生產的蹤跡,使整個領域“縫合”,生產出無需外部的自我封閉效果:生產過程的蹤跡、它所包含的裂縫、它的運行機理都被抹除了,產品表現為一個自然化的有機整體。[7]74齊澤克認為,在上述觀點中,縫合的功能等同于“封閉性”:“縫合表示結構的裂縫、開口被消除了,使結構能夠(誤)認自身為自我封閉的再現性總體。”[7]41標準縫合理論包括兩個假象:一是有機整體的假象,縫合將具有差異性的外部元素刻寫入內部,抹除了差異性;二是自然化的假象,縫合通過正反打鏡頭、連續性剪輯、180度原則、燈光等一系列標準工藝,抹去了缺席者(攝影機)的痕跡。
在影像中,當主觀與客觀鏡頭的交替無法令主體感受成一個“自然的有機整體”而指向更怪異的效果,此時一般的縫合不再起作用。這開啟的是“界面”(interface)的功能。在這一層面上,界面指向呈現影像的方式,即正鏡頭與反打鏡頭在同一個鏡頭中凝聚。界面開啟了觀眾在普通場面中察覺到純然幻想的維度。界面的元縫合功能包含了幻想的反身邏輯,呈現為“A-BC(AB)”結構的鏡頭。首先是一個正鏡頭(A),觀眾在此刻誤認為鏡頭內的人物是動作發出的主體。然后是一個反打鏡頭(B),標記動作作用對象,可以是人或物。最后正反打鏡頭被結合進同一個鏡頭,這個鏡頭既是正鏡頭也是反打鏡頭(AB),卻不是他們的雙重在場,而是“幻想之幻想”(C)的展現。界面縫合的理論一樣可以引入數碼屏幕的研究中。它同時包含著元界面與界面縫合的維度,它們共同構成一個“正反打”鏡頭,屏幕所呈現的內容越來越深刻地標記為一種能夠感知的主觀幻象,而不是虛構他者的幻象。
以界面的元縫合功能出發,我們如何推導出電子界面的“鏡頭結構”?無論在電子屏幕上觀看何種數字化的影像,標準的正反打鏡頭比比皆是。比如在短視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創作者先用自拍對準自己,講述一番經歷,這是一個正鏡頭(A)。然后他會將鏡頭翻轉,朝向自己的視線對象,用來解釋說明他到底看到了什么,這是反打鏡頭(B)。但接下來不會出現一個由創作者發出正反打鏡頭(C),能看到這一鏡頭的只能是觀眾。“有鑒于傳統的觀看情境,系假定在黑暗的戲院中,所有眼睛都注視著銀幕。新媒體卻是經常意味著光線充足情況下的小銀幕。”[5]203觀看環境的變化帶來了更為徹底的界面:在移動終端的屏幕上,會映射出“我”的臉。特別是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觀看者的臉會清晰地倒映在屏幕上,屏幕原本的內容變得更像是一種不穩定的投射,躲在人臉背后的陰影中。只有在觀看者主體的眼中,C(AB)鏡頭才得以成立。在這一鏡頭內,不確定的正反打鏡頭和觀看者的鏡像倒映重疊在一起,與威特·哈爾蘭的《犧牲》(Opfergang,1944)中那個標準的界面縫合鏡頭有著構圖上的相似性(圖1)。觀看者的鏡像縮減為電子屏幕上暗邊的昏暗中幻覺般的孤島,占據了觀者自身的視野,有時我們會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表情,看到我們自己對于屏幕內容的反應。這種方式將縫合撕開一個裂縫,外部的不一致性刻入內部,被識別、標記出來,不再能夠維持一個連續性的觀看狀態。由于正面鏡頭與反打鏡頭的重合(它們由“我”發出,也在表現“我”),鏡頭視點沒有分配給任何一個影片人物,反而分裂了在場空間與屏幕內空間。因此,觀看的空間無法由想象進入到象征和符號,數碼屏幕影像的觀看由此開啟了界面的效應。

圖1 《犧牲》中的界面縫合鏡頭
三、觀看之主體:從去中心化的身體到主體化
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將技術提升到關乎“人類生成”的本體論的高度,提出“后種系生成”的奇特概念:在生物種系進化完成之后,促進“人類生成”的最重要因素,不再來自生物性的遺傳,而是來自非遺傳性的積淀,亦即,對過去的文化記憶。[8]31這些非個體性的文化記憶如今由數字媒介和信息技術共同制造與保存,塑造著人類社會的此在與未來。本質上,向電子機械驅動的賽博空間“窗口”是對現實的削弱與改造。當屏幕內的影像需要再現現實的表現形式時,往往將現實置于一個物質性界面之后。而那些可以依靠算法生成的表現形式,則更加凸顯出界面的本質性力量,如同眼簾,打開就是整個世界,關上世界就會消失。觀看者主體在多用戶領域中逐漸去中心化,在肉身與賽博空間的多重身份中,主體身份變得越來越曖昧、含糊、不確定。
技術生成與界面縫合讓觀看者主體面臨的是區分外部與內部的界面的缺失。這個缺失危害到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身體”的最本質的領悟,即認為它與環境息息相關。外部與內部的界面不再被區分,而被電子屏幕整合。因此,環境不再發揮其本來的作用,而是作為界面的奴隸,被成像、被拍攝,而不是直接感受。環境因界面而存在,否則它無法被把握。更進一步來看,界面的缺失削弱了我們對于另一個人的標準現象學態度。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認為:“他人是這樣一個身體:是一個為各種各樣的意向所積獲得身體,是一個作為許多行動和話語之主體的身體,這些話語和行動回蕩在我的記憶里,正是這些話語和行動向我勾勒出他的精神風貌。”[9]59我們只能從一個外部觀察者的視角去看一個他人,他人本身的存在與他的表情、姿勢、言語及身體是不可分割的。如今,隨著外部的內部化,我們越來越少地依賴自身身體去把握人與物,在一種無環境、無觸碰、無身體的真空環境中抽象地認知當下世界。于是,在這種態度中,我們懸置了對于皮膚下真正存在何物的知識(腺體、肌肉……),認為表面(比如臉)直接反映了 “靈魂”。人類逐漸失去其在具體生命-世界中的基礎,而轉向在賽博空間內的注冊性生存。
電子界面的觀看迫使主體“分裂”出單一身體之外的許多角色。一個多用戶主體潛在地會在不同的觀看領域下意識地做出不同的反饋。在互動性觀影網站,主體傾向于及時抒發觀影感受;在直播影像中,主體傾向于釋放自己的消費沖動;在游戲影像中,主體致力于培養一個強大的賽博空間分身;在短視頻平臺,主體放任自身的欲望驅力,延長內時間,消磨外時間。觀看用戶的主體性是一種戴上面具的“自我-形象”,不斷地在真實肉身與想象身份之間滑動。一般性的看法是賽博空間的多重面具背后有一個真實的主體,這些虛擬的角色是主體的偽裝。但齊澤克指出,賽博空間想象身份的符號面具可以它之后真實的臉更真實,“外在于屏幕上‘多重自我’是‘我想要成為的人’,是我的理想自我的表現”[6]174。想象身份補充了只能有虛構或虛假形象來描繪真實生活的隱私時刻的禁令。主體為自己創造的觀看者形象可以比主體的“真實-生命”形象(“官方”的自我-形象)更像自我。就此而言,對于某部文藝作品的反饋會依據場合而發生改變。在現實生活中 (比如線下觀影會),受到社會身份與大他者的限制,我們的評價判斷總會偏離我們的真正想法。面對面時,我們帶上“面具”,做出一些符合社會常識和主體身份的評價。而在賽博空間中,真正的自我展示隱匿,符號用戶登場。在無身體的空間內,我們可以暢所欲言,展示真實的自我,說出真實的想法。主體在這些身份之間的滑動“預示了一種空洞的聯合,它使得一個身份向另一個的跳躍成為可能,這個空洞的聯合就是主體本身”[6]175。因此,“去中心化的主體”并不意味著一個真正的自我與更多的虛擬自我的多元集合,而意味著是對分裂主體的內容的去中心化。
為了更進一步說明“去中心化的身體”,我們應當參考賽博空間的“代理人”。“代理人是一個作為我的替代物完成一系列特殊功能的程序。”[6]175一方面,它作為主體的延伸,幫助主體完成賽博空間中的身份注冊。比如在視頻平臺中注冊賬戶,我們只需要填充信息,“代理人”就可以自動生成一個個性化的觀影庫,記錄主體的觀影歷史,并做出個性化推薦。另一方面,代理人也對主體行動、控制著主體。比如聽力保護措施或個性化定制服務。當觀看者戴上耳機將音量調高時,界面會自動彈出一個對話框,提醒觀看者如果繼續調高音量,可能會損傷聽力。代理人也會自動為觀看者篩選一些信息,送到電子界面上。由于賽博空間的代理人是一個技術性的外部程序,決定著觀看者的觀看行為或者內容,代理人“使主體成為中介”。我們可能會想象:“另一個我所不知道的計算機程序控制著、指導者我的代理人——假如這個情況發生的話,我事實上就是從內部被統治:我自己的自我不再是我的。”[6]176中心化的主體擁有的一個確定自我在形式上分裂成多種觀看角色,從而去中心化。屏幕角色(想象身份)與主體之間并不對立分裂,而主體與空洞之間存在分裂。“空洞”指向的就是不可見的代理人背后的最高統治者,主體無法填補與其之間的溝壑,無處可逃。最終,今天主體性的一般狀況就是一種斯蒂芬·霍金式的身體:一個保留著人類屬性的頭腦加上被中介的身體。主體通過點擊去尋找,通過界面去觀看,通過變聲器說話,通過虛假的數字角色去評價乃至再創造。
四、結語
本文探討了數碼屏幕影像的觀看機制,認為它是一種基于電子界面的想象。從界面生成的角度來看,電子界面不同于窗、畫框、銀幕等經典屏幕,它可以脫離自然屬性而完全由技術支撐。觀看的對象有一個確定的文本變為難以加以定義與闡釋的超文本;從界面縫合的角度來看,光線充足的觀看空間使得觀看者的身份被標記出來,無法維系一個連續性的觀看活動,阻礙了由想象進入到象征和符號的過程,開啟了界面效應;從觀看者主體的角度來看,肉身身體與數字身份的分裂是淺層的,更為深層的是主體身份與空洞之間的分裂,空洞指向一種賽博空間代理人背后的不確定性。與實體化的傳統影像相比,數碼屏幕影像的觀看發生了巨變。其觀看機制不僅深刻地影響到數字影像的話語體系與創作方向,更深刻地貫穿于當今人類的認知與記憶中,塑造著人類的未來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