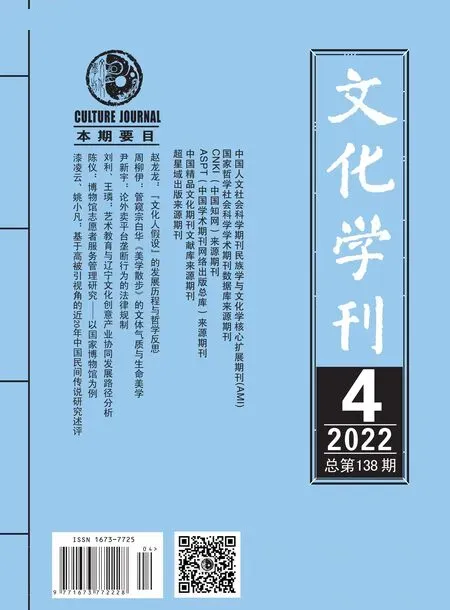空間敘事、隱喻藝術與傳奇性書寫
——解讀王安憶新作《一把刀,千個字》
劉奕含
王安憶是當代著名作家之一,新作《一把刀,千個字》再次證明了她的寫作實力。故事從淮揚菜廚師陳誠在海外的生活開始,通過紐約華人的大宴小酌,牽引出陳誠一家的命運。故事里展現了東北哈爾濱、上海弄堂和揚州城的市井人生,和王安憶此前的創作不同,這次她不再描寫熟悉的上海,而是拓寬空間,從紐約到哈爾濱、從上海到天津、揚州等地,多次的地理空間轉變與人物命運息息相關。小說《一把刀,千個字》正是作家運用她最擅長的現實主義手法帶來的全新故事。
一、空間敘事:空間轉換與人物命運
文學創作與地理空間是相互交融的,“小說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場所與邊界、視野與地平線組成。小說里的角色、敘述者、以及朗讀時聽眾占據著的不同地點和空間”[1]。故事中出現的空間是解讀作品、理解人物生活背景的關鍵信息。文學作品里較為著名的地理空間如師陀的“果園城”、賈平凹的“商洛”、莫言的“高密鄉”,陳忠實的“白鹿原”等,這些地理空間不僅是主角活動的場所,更蘊含著作家特定的心理狀態和思想意識,作為一種情感的載體被賦予美學意義。小時候王安憶因為母親茹志鵑轉業的原因來到上海生活,成長于上海,上海的一切都深刻印在王安憶心里。成名后,以上海都市為中心創作的小說《長恨歌》《匿名》等,多將上海作為人物展示人生的舞臺,也是主角們最后的歸宿。但在新作《一把刀,千個字》中,王安憶跳脫了上海弄堂,試圖通過多重空間,來折射人物命運,展示時代變遷。
小說分上、下兩部,上部講述主角陳誠在美國的移民生活。陳誠出生在江蘇,是一名廚師,故事開始他在紐約法拉盛的一家餐館做工。為謀生計,陳誠放棄了更擅長的本土菜系,做起了北美化的中國菜,偶有華人家宴就是他展示家鄉廚藝的好機會。20世紀90年代的法拉盛華裔聚集,具有濃厚的中國風味,但時間久了,陳誠仍免不了感時傷懷,畢竟這里是美國,他總覺得即便是深處華裔聚集的地方,自己仍舊是屈才的。直到師師的到來改變了他的想法。在回憶中跟隨陳誠的視角,回到了他曾經生活的地方——上海虹口弄堂,七歲的陳誠和孃孃(上海話:指姑姑)一起生活,日子瑣碎、吵鬧但也有很多樂趣,來到這里之后,采買和煮飯的活兒就全是他的了,因為要控制花銷,材料緊湊,做的每頓飯都要精打細算,不過這樣的日子也不全是苦的,因為給了陳誠日后可靠的朋友和意外的戀人。20世紀80年代初,陳誠和父親、姐姐相繼來到紐約,重新找尋人生。王安憶筆下的紐約帶有一種虛擬性,特別是80年代,美國的移民眾多,作為一心想做中國菜的陳誠在餐館做工久了,內心里有很多想法,這里王安憶也寫出了主角一家作為移民對當地的看法,很多想法反映的是他們自身的處境,這樣的命運,也為陳誠一家各自的寂寞與鄉愁提供了生發的土壤。而全家人來到美國生活的原因,與家中一直缺席的母親相關,母親的過早離世,深刻而無形地影響著家中其他人的命運,給父親、姐姐和陳誠的生活增添了許多幸與不幸。母親離開后,時間并沒有停滯,這種時光稍縱即逝的蒼涼感在陳誠心里愈發沉重。
小說下部交代陳誠母親的一生,僅在幾章的敘述里,王安憶便塑造了一位立體鮮活的母親形象。陳誠的母親出生在哈爾濱的一戶基督教家庭,從小活潑開朗,上學時母親參加集會、演出話劇,是學校的名人。那時的哈爾濱住著許多俄國人,母親也因此結識了不少俄國朋友。20世紀50年代母親和父親相識,之后結婚、生子。“但在她內心里,其實有著大志向,絕非男女愛情、一時虛榮可同日而語”[2]122。在兒子的記憶里,母親短暫出現又匆匆離場,他只有和父親、姐姐相依為命。至于這位母親的名字,王安憶沒有交代,僅以主角母親的身份登場,她與孩子們的生命交集非常短暫,母親過早地從一家人的生活中消失。父親在母親出事后,為保護年幼的“我”,將“我”送到上海的姑姑家撫養,于是“我”被迫離開了東北小城來到了陌生的上海。小說里無論是陳誠的親生母親,還是照顧過他的姑姑,她們都免于名姓,都相繼離開了人間,從此在陳誠的心中,關于母親和孃孃的記憶越來越模糊,北方和南方的回憶俱滅,只剩下小說開頭紐約的寒霜。在王安憶筆下,陳誠童年生活的這片北國小城抗戰時曾被日寇的鐵蹄踐踏,20世紀60年代主角失去了最重要的親人。隨后輾轉南下,從上海到美國,一家人尋求的是情感的棲息地。小說里人物生活空間的多次轉換,既是時代的推動,也是主角無奈的選擇。作者通過主角一家生活空間的多次轉換,完成了人物的性格塑造,交代了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命運結局,表現出陳誠和父親、姐姐幾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軌跡。
二、多重隱喻:人物命運的深度追問
隨著多年的創作積累及精神層面的自我成長,王安憶試圖在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建立起精神的血脈聯系。從早期的“雯雯系列”到“三戀”,再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叔叔的故事》《長恨歌》,她都在嘗試不同的創作技巧,時刻關注時代與個人命運,思索不同時代影響下個人的出路。新作《一把刀,千個字》將敘述的關注點調轉開來,不再只關注一個人或某一段歷史,而是由一個人引出一個家庭,圍繞歷史、美食、中西文化等諸多元素,對故事中的人物命運進行深度追問。小說中出現了多重隱喻,是幫助讀者閱讀的關鍵。隱喻不僅是認知語言學中的一種語言修辭現象,更是人類概念化認知世界的外在表達方式,這一認識視角對于文本主題的解讀具有啟發意義。
首先是題目隱喻。“一把刀”是指“揚州三把刀的頭一把,菜刀”,這里指主角陳誠的職業——廚師。“千個字”取自袁枚的“月映竹成千個字”,是陳誠和兒時玩伴踏過的竹影,也指他回憶中美好的童年時光。菜刀,作為第一刀,每刀下去便有了飯桌上的食材內容,也揭開了所有人故事的序幕。俗話說,民以食為天,中國人特別喜歡圍坐在飯桌,有時候吃飯不只是圖個溫飽,飯桌旁是形形色色的人群,在吃飯過程中彼此傳遞著訊息與情感。小說里出現了很多次飯桌,在談生活的各種“變化”,江南的青菜到了美國雖形狀完整,色澤鮮艷,但基因卻突變。在法拉盛,一道淮揚菜,就能勾起濃濃的鄉愁。小說里飯桌呈多層變化,有階層趣味的變化、政治環境的變化、種族文化的變化等,但凡有人吃喝,那一定是新表演的布景,大事件的前兆。借這些飯食,陳誠回憶起了生活過的東北小城、上海弄堂和江蘇淮安。
其次是結構隱喻。小說采用的是全知視角,上半部圍繞陳誠的故事展開,并拋出一個“謎題”: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為何來到這里?下半部主角陡然轉變,陳誠的“母親”出場,圍繞母親上學、畢業、結婚、生子到參加革命等事件展開,敘述人一方面操持著豐富多元的敘述技巧,另一方面又扮演著美食家角色,將大量有關飲食的內容傾瀉而出。王安憶在采訪中說:“在我看來,小說的上部下部,是結構的方式,說的還是一件事,淮揚廚師的前世今生,沒有按照自然時間的排序,而是按照另一種,也許更接近身心成長的先后,或者寫作當時當地的心緒”。至此“謎底”已經揭曉,作者其實是用美食、中西文化包裹外殼,敘寫了一個后革命時代的離散故事。作家不愿輕易告別革命,而是要叩問革命者的前世與今生。小說特意抹去陳誠母親的姓名,表明她只是那個特殊年代眾多普通革命者中的一員,她為革命奔走,不曾放棄自己的大志向。同時也借這位母親向世間表明,革命年代的仁人志士,他們愿意舍棄一切,家、親人、名字,只為了信仰和心中的理想。敘述者有意在多章留白,為讀者開啟了想象空間。這讓陳誠的出現,甚至小說所有人物的出現都充滿了另一層含義,就是側面烘托“母親”這位英雄。
最后是空間隱喻。小說將敘事建立在一系列空間轉換的基礎之上,地理跨度大,故事流轉多地,每次主人公的離開或遷入,既是自由意志的選擇,也是時代的推波助瀾。陳誠生在冰雪之地哈爾濱,記憶卻從上海的孃孃家開始。放棄了在中國的廚師工作,后在紐約法拉盛成為一名中餐館的大廚。圍繞不同地域舌尖上的美味,無形中開闊出另一番美妙世界。小說的地理空間顯然是一個關于特定人物成長與人生際遇的一個個地點,整部小說就像是電影中的長鏡頭,緩緩掠過紐約、弄堂、哈爾濱、揚州等,將一系列事情、人物串聯起來,構筑起小說的主體框架,也為小說主題的討論提供了演武場。這樣的寫法,王安憶也在《長恨歌》中展現過,廣場的信鴿飛入弄堂,飛進王琦瑤生活的小巷,到結尾又是鴿子視角,結束了王琦瑤的一生。轉型后的王安憶有意識地凝視時代與人物,借美食講述革命,小說內容看似瑣碎,實則蘊藏著作者對時代與生活本質奧秘的探尋,散發著濃郁的地域特色與王安憶深切的人文關懷。
三、傳奇性的書寫:還原生活本真
在小說中,傳奇性體現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正如弗萊所言,傳奇經常散發出一種強烈的主觀意識。在《長恨歌》中,王琦瑤算得上傳奇人物,她順應時代的變動而走,最終又回到了她愛恨交雜的弄堂。《一把刀,千個字》中陳誠的母親也是一個傳奇人物。她是妻子、是母親,還是一個革命者,她為革命奔走,她的革命思考和革命經歷均發生在家庭之外,她為理想遠赴南方,終有一日歸來,寫下十二張大字報,張貼在外。脫離了權力可以容納的軌道,母親的言行終究給她招致了災禍,從此母親缺席了這個小家庭的生活。其實母親在學生時代就已展現前衛思想,她個性果敢、為人堅韌,和父親結婚后也從不忘自己當初的遠大志向。當得知自己要被捕,她拒絕回家,父親苦苦哀求著,她還是堅持留下。而后被抓走,再未出現。但是孩子心里怎么能不惦記母親呢?之后的陳誠到了孃孃這里生活,后來父親攜帶姐姐看陳誠的時候,出現這樣一段對話:“停一時,父親開口了:以后,你管嬢嬢叫‘媽媽’。嬢嬢接著說:這樣,你就可以在上海讀書。他有些懵,心里恍惚著,問出一句話:我媽媽呢?兩個大人被問倒了,面面相覷,然后,他看見嬢嬢的眼鏡鏡片奇怪地閃爍一下,戴眼鏡的人哭了”[2]231。王安憶非常隱晦地刻畫出特殊年代里,知識女性在苦難中的堅韌與從容。從古至今,女性一直處于弱勢地位,五四啟蒙后,女性和關于女性命運的討論慢慢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到了當代文學作品中,張潔、楊絳、嚴歌苓等作家曾多次在作品里描寫過“文革”中堅韌的女性形象,《愛,是不能忘記的》《干校六記》《芳華》《陸犯焉識》等,這些作品不僅寄托了作家們對該時代女性的贊揚,更表現了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王安憶曾認為“女性是城市的代表,女性是城市永恒的精神。當社會災難襲來輕易改變現有秩序甚至顛倒秩序時,男性會受到重創,女性卻憑其生命承重力的韌性浮出海面,要在一種極端個人的,孤立無援的自我體驗中,女人比男人更趨于成熟”[3]。因此,女性在她的筆下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王安憶小說中的女性有著與命運抗爭的韌性,無論是《長恨歌》中的王琦瑤,還是《一把刀,千個字》中主角的母親,都不甘于命運的安排。
小說里有關陳誠母親的描寫僅集中在幾十頁里,文字雖簡短,但母親的形象卻立體鮮活。作家用抒情的筆觸描寫了陳誠母親的一生:她的崇高理想,她的溫柔多情,她的體貼入微,她的無私偉大。小說里陳誠一家的命運與時代緊密相連,期間發生了多少動人心魄的事情。但王安憶就此打住,沒有繼續書寫,她偏要去消解這種人物命運的傳奇性,她將主角陳誠沉到生活的最底層, 把他變成最普通、最平凡的百姓。陳誠作為傳奇人物的兒子,但他偏不要這個傳奇的籠罩,他沒有選擇和母親走一樣的道路,對革命、對信仰沒有那么執著。陳誠的志向很簡單,成為一名廚師,在煙火中過自己的小日子。他對母親,以及母親為之犧牲的革命,其實一知半解。長大后他選擇廚師之路,與原生家庭漸行漸遠。隨后來到美國,更象征著他改頭換面的決心。王安憶沒有寫出主角要像英雄母親一樣“一定要革命”這樣宏闊的志向,也沒有母親是革命英雄,后代的子孫一定也要是這樣的道理,小說雖是革命敘事,但卻由革命寫到美食,寫到中西文化,于無形中展示人物的傳奇性。在談到小說創作時,王安憶也曾表明,自己隨著年齡的增長,奇峻的東西看得愈發平常了。在浮泛的聲色之下,從冗長的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提煉出精華,越普通的家常其實更容易捕捉到生活細節,成為審美對象。王安憶的小說創作就常常努力以普通人為對象,她對現實人生有著一份入世近俗的關懷與思考。
初入文壇時的王安憶,創作縈繞著青春氣息和人情冷暖。中期她越發關心中國文學的發展變化,嘗試書寫多方面的主題。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個人生活經驗、情感經驗的增加,王安憶有意識地追求超越,將視線投向更深邃處,《長恨歌》《天香》《匿名》《考工記》近些年的作品里多追溯歷史,用更理性的方式思索世態人情,實現了青春小說向現實主義小說的轉變。新作《一把刀,千個字》將美食、文化、革命納入到重要的敘事與審美范疇,利用空間的多次轉換、人物心境的變遷,以隱喻書寫展現普通人生活的本質。在王安憶創作的十五部長篇小說中,《一把刀,千個字》的意義和價值,或許不在《長恨歌》之下,時間會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