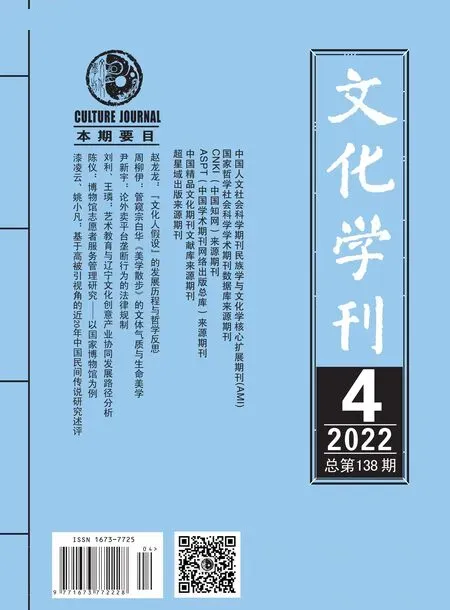論自傳記憶書寫和身份認同之關系
——以西班牙“27年一代”女作家自傳為例
歸 溢
記憶與身份認同密切相關。身份認同理論在很長時間里經歷了大轉變,“從本質主義向建構主義……從一元論過渡到多元論……[1]26”,但是無論如何變化,它始終離不開記憶的輔助。英國啟蒙哲學家約翰·洛克指出,人的身份認同的實現建立在人具有自我反思的思維意識之上,這種反思的思維意識毫無疑問與記憶息息相關:“如果一個人的思考行為能夠回溯到過去的任何一種行為或思想,那么這個人的身份認同就能得以確立[2]45”,即,身份認同可以通過記憶實現。同時,“個體的身份認同產生于個體在時間的流變中對自我作為同一的自我的認識。”[2]45。時間等因素的流變會促成身份認同的流動性,根據建構主義理論:“身份認同更像是‘短暫的卻又極具變化性的一種狀態’。身份認同的發展是需要用人的一生去完成的建構過程,也是一個永遠無法達到完結狀態的過程[2]43”。
記憶主體因其個體差異會對同一現象形成不同的記憶,但是,若個體之間存在諸多相似性,且處于相同的歷史環境中,他們的記憶會呈現共同特質,與之密切關聯的身份認同亦然。西班牙“27年一代”女作家的自傳記憶書寫和身份認同存在很多共性特征。
在西班牙“27年一代”女作家的名錄里有羅薩·查塞爾、孔查·門德斯、瑪利亞·特雷莎·萊昂、瑪利亞·桑布拉諾、艾爾內斯蒂娜·德·常布爾辛、卡門·孔德等,她們是西班牙20世紀文學“白銀時代”的杰出代表,她們通過詩歌、小說、戲劇等體裁的創作在西班牙20世紀文壇留下獨特的痕跡,為20世紀西班牙女性文學創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所有上述提到的女作家都著有自傳:萊昂的《憂傷的記憶》(1970)、查塞爾的《從天明開始》(1972)和日記三部曲 (1982,1998)、孔德的《開始生活:在梅里亞的童年記憶(1914-1920)》(1991)、常布爾辛的《艾爾內斯蒂娜·德·常布爾辛的日記和自傳片段》(2008)和桑布拉諾的《胡言亂語與命運:一個西班牙女人的二十年》 (1989),這些自傳一方面記錄了她們作為女性的個體經歷,另一方面構成了西班牙歷史見證文本,同時,它們彰顯了女作家們為實現身份認同作出的努力。
“27年一代”女作家們的自傳通過記憶書寫實現身份認同,同時體現了身份認同的流動性,本文旨在對此進行詳細分析和論證。
一、童年記憶書寫體現身份認同對過去的選擇性重塑
自傳體記憶是現在的自我對過去記憶的建構,“現在自我是個體對自己當前屬性的認知和評價,與人格、近期目標和信念相聯系,它會影響個人如何去回憶自己的過往,如何在自傳體記憶中提取信息[3]”。
幾乎所有“27年一代”女作家的自傳都投入很多篇幅描繪童年生活,其中查塞爾的自傳更是集中描寫自己生活的前十年,孔德的自傳也聚焦在她的童年生活,在萊昂、常布爾辛和桑布拉諾的自傳中,童年生活也是反復出現的主題。在孔德的自傳的序言里,傳主回憶自己離開童年生活的城市時的痛苦,并為童年時光已逝而遺憾,其他作家,尤其是桑布拉諾筆下的童年也隱藏著對過往歲月的留戀。對童年的記憶書寫一方面表現出傳主對回歸童年的渴望,另一方面是為了剖析和反思童年生活對自己人格形成的影響,從而實現自己的身份認同。
楊正潤指出,“傳記的初始形態是記錄生平;其后,傳記開始注重表現人格;到現代傳記, 傳記家又力圖解釋人格[4]14”。通過自傳來解釋生平,進而分析人格的形成,是從盧梭的《懺悔錄》開始的,它經歷了兩個時期:1.傳統的人格解釋方法,包括通過介紹作者所處的時代特征和生活道路來解釋傳主;2.進入20世紀后,出現了新的方法,“主要依賴于心理學,特別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給傳記的解釋指出了三種主要途徑:俄狄浦斯情結或性心理,精神創傷或變態,童年經歷[4]15”。根據弗洛伊德的研究,童年生活的經歷是解釋作家人格形成的關鍵,童年時代被看作“是決定自己一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4]15”。
在“27年一代”女作家關于童年的自傳記憶書寫中,都對自己的出身、家庭關系作了交代。菲力浦·勒熱訥對“自傳”定義如下:“一個真實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為素材用散文體的回顧性敘事,它強調的是他的個人生活,尤其是他的個性的歷史[5]”。家庭的起源是個體存在的一個基本條件。
在萊昂的《憂傷的記憶》中,她介紹自己的父親:“我父親曾跟隨里維拉將軍進行獨裁冒險,并組建了他的團[6]157”;她還追溯到她外曾祖母的時代:“她是總督女王的侍女[6]149”;關于她的外公外婆:“在我的記憶里,外公是個花花公子。我不知道我是否曾見過他。他住在巴黎,死在馬德里[6]147”。她用將近兩頁的篇幅來敘述外祖父母的軼事,主要反映外祖父對家庭的不負責任,這讓我們看到作者是如何間接地揭示外祖父的大男子主義和當時社會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現象。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自傳并非按線性時序撰寫,關于她的家庭情況介紹留有許多空白。這樣的安排表明,作者進行記憶書寫的意圖是實現身份認同,而非記錄家族歷史。
在查塞爾的自傳中,祖父原先是軍人,后來成為一名律師;查塞爾的父親也打算成為士兵,但沒有走上這條路:“他認為他的性格使他無法遵守軍事紀律,他太暴力,不會接受任何人的命令[7]23”。作者用半頁篇幅介紹她父親的家族歷史,用更多篇幅介紹母親家族,并說明原因:“我重新追溯到上個世紀,描摹一下我的父親和母親家族人們的生命軌跡,從而解釋為什么原先被大洋隔離的兩個孩子最終在西班牙的一個城市相遇,并劃出了共同的軌跡……也奠定了我的命運[7]23。”
除了家族記憶,女作家們的書寫都關照了對自己童年產生影響的人或物。如查塞爾記錄父母對自己在藝術和閱讀方面的重大影響;萊昂花大篇幅介紹自己的姑姑(西班牙第一位女博士)如何對她進行啟蒙;桑布拉諾大力夸贊自己的學校,因為學校促進了她的健康成長。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自傳都提及童年的自己對書籍的無比喜愛。莫羅伊指出書籍在西班牙自傳體寫作中的重要性:“自我與書籍的相遇是至關重要的:閱讀經常被戲劇化,在一個特定的童年場景中被喚起,突然賦予整個生活以意義[8]”。
作家們追溯家族歷史回答了身份認同的根本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對自己成長產生影響的人或物是自我人格形成的條件,對其進行回憶是為實現身份認同奠定基礎。童年是一個人最具有完整“自我”的時期,自傳中大量關于童年的記憶表明她們對自己的根的追尋,這是傳主們實現自我身份認同的第一步。同時我們看到,傳主們對童年生活的素材有目的地進行篩選,都是為了服務于身份認同的建構。
二、消解男權主義定義的女性特質,體現身份認同的流動性
身份認同具有流動性,這一特點與記憶的本質相同。“記憶就是一個根據現實需求不斷對過去進行確認、篩選、改造、重組和想象性創造的過程”。“所有認同都在一套社會關系體系內構建起來……不應把認同……看作個‘事物’,而應看作‘關系與表述的體系’……維系一者的認同是……一個持續重組的過程,而不是個已知物……認同被看作是動態的自然發生的集體行為[1]36”。
根據建構主義理論,“主體通過日常行動持續不斷地構建自己的身份認同[2]43”。“27年一代”女作家筆下的自己都具有獨特的個性,日常行為與同時代的其他女性有明顯差異,尤其是童年時的自己。此外,她們用日常行動挑戰傳統的社會規范,認為這些規范限制了她們。
首先,她們不約而同地塑造了“淘氣”“叛逆”的女孩形象。如常布爾辛在自傳中突出自己童年時的淘氣,并強調在童年時就知道自己與其他女孩兒不同:“我們住在一個有花園的別墅里,花園里有很多蘋果樹,綠色的果實是我們貪婪攻擊的對象。盡管有蛀牙的威脅,但雨后潮濕的青蘋果吃起來很不錯。我和哥哥不顧一切禁令,毫不留情地攻擊它們[9]”。女孩兒像男孩兒一樣爬樹摘果子,這在常布爾辛所處的時代是不可思議的。萊昂兒時叛逆的例子很多,如學生時代在天主教學校看禁書,導致被學校開除的后果。在20世紀初一個女孩兒看禁書的行為,無疑是對傳統社會強加給女性的種種桎梏發起的挑釁。
值得一提的是,查塞爾表現自己兒時的獨特個性時,沒有塑造自己“淘氣”的形象,而是極力展現自己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非凡的智慧。她在《從天明開始》中不斷強調幼年的自己是個“嚴肅、有判斷力和有主見的女孩兒,習慣于不斷觀察別人,保護自己的空間不受大人影響[10]”。她對事物的判斷都基于自己的思考,不受他人影響,甚至有些固執:“我不是對別人的意見充耳不聞,我根據自己的判斷來評價它們。這就是說,別人的某些意見對我有很大價值,而其他意見則不[7]64”。她對自己與父母關系的分析也持這種態度:“我含蓄地、不斷地評判我的父母:他們是我唯一堅持不懈地、系統研究的對象……我只認可我自己的結論[7]35-36”。她還稱自己從閱讀中獲知她自己不能發現、不能創造的東西,她堅信自己能理解和吸收所有讀過的內容。上述話語構建出一個自信、有主見、智慧的女孩兒形象。
除以上列舉的大量女作家們消解男權主義定義的女性特質所作的嘗試,這些女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對其他社會傳統提出挑戰。如萊昂雖然非常年輕時就結婚生子,但是當發現家庭生活禁錮了她,她毅然離婚,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主動擺脫婚姻桎梏的女性。在認識詩人阿爾維蒂后,她清楚自己后面要走的路,于是堅決地離家,跟祖母道別:“祖母,我要離開了,我要繼續我的旅程。拉法埃爾和我的手永遠不會分開[6]203。”就此,她擺脫了傳統家庭和父權社會為女孩準備的生活。
桑布拉諾對男權社會給女性定下的規則也表現出不滿:“如果不是為了哲學,為了那個愚蠢的野心,她——一些愛她的人認為——會成為這個或那個,她至少會結婚,……[11]31”。當時人們都認為女性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智力活動上,桑布拉諾的話對此進行反駁。
上述事例中,或淘氣、叛逆,或有主見、智慧的女孩形象,通過對自我的堅守成功實現了身份認同。根據女作家們兒時所處的傳統社會標準,淘氣是男孩兒的屬性,與女孩兒無關,后者應該安靜、聽話。但是,淘氣的形象事實上是女孩兒“完整自我”的體現。根據埃里克·伯恩的人格結構理論,所有人都表現出三種基本的自我狀態:父母、兒童和成人。在兒童狀態下,他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地表達感情;惡作劇是“兒童”狀態的本質。
女作家們所處的傳統社會用其傳統意識形態為女性設立身份,給女性貼上“溫柔、順從、無主見、依附男性”的標簽,使她們與“智慧”“主見”無緣,這是一種話語霸權。女作家們用她們的自傳消解男權主義定義的女性特質,顛覆這種霸權,完成身份認同。上述女作家們為實現此身份認同所做的努力也證明,身份認同是個建構的過程,具有動態的特性。
三、記憶書寫實現社會身份認同
“人們會用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群的成員資格來建構自己或他人的認同。依據社群成員資格來建構的認同被稱為社會認同,而依據個人的獨特素質而建構的認同被稱為個人認同。社會認同是個體對自己與有相同背景的他人(即我們) 的相似性的感知, 同時也是對我們與其他群體或類屬成員(即他們)的差異性的感知[12]”。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指出,“自我身份認同”是“社會身份認同”和“個人身份認同”在爭斗中最終達到的和解和妥協[2]44。不可否認,“27年一代”女作家在社會身份認同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這些女作家的自傳,幾乎在每本開篇都先確立自己的社會身份,如萊昂自傳的序言,查塞爾日記的開篇,都亮明了自己流亡者的身份;桑布拉諾的自傳雖然將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用于記錄自己的流亡生涯和心情,但是從第一部分開始,就以一個流亡者的視角回顧自己的童年。流亡者這一特定身份讓她們在書寫歷史時的角度有別于留在西班牙的人,也有別于非共和派的人。敘述主體在孤立、無根的情況下通過自傳來實現自我表述,此時她們的身份與第二共和國時期、西班牙內戰乃至流亡前所有的身份都構成對立和沖擊。這些自傳在書寫歷史時,從個人焦點轉向了群體,轉向了對西班牙內戰及之后狀況的揭露。歷史對于這些自傳而言不再是背景,而是重要內容。萊昂用吶喊的方式書寫那段特殊的歷史;查塞爾用緘默作為反抗的手段;常布爾辛用平靜的、局外人的角度來敘述;桑布拉諾以哲思方式來書寫……她們的書寫都是對當時西班牙國內已經寫就的社會記憶發起的挑戰。
作家身份也是她們著力構建的社會身份。查塞爾、萊昂和桑布拉諾的文本都記錄自己的文學創作生涯,如查塞爾的自傳很大篇幅回憶如何從父母處繼承對文學鑒賞的天賦;萊昂的自傳中記錄很多她與同時代著名作家的交流;桑布拉諾在自傳中強調書籍對她生命歷程的重要性,并坦言,在30年代的西班牙,作為女哲學家、女作家,她幾乎被視為“異端,是馬戲團的奇葩[11]20”。然而,寫作的成功增強了這些女作家掌握自己命運的信心,作家的身份讓她們從男權傳統社會觀念中的客體轉變為主體。
四、結論
筆者認為,通過“27年一代”女作家們的自傳記憶書寫,我們看到了其與身份認同的種種關系,一方面,記憶對過去進行選擇性地重塑,從而成為實現身份認同的手段。正如《文學、記憶、身份理論初探》一文所述:“回憶讓我們形成對自我的意識。通過記憶我們構建起自己的身份[13]。”另一方面,記憶書寫體現和證明了身份認同是個動態的過程。因為身份認同“總是以個體的行為能力和與社會環境的交互影響能力為前提,并且在個體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中不斷地被重新界定[2]43”。記憶和身份認同都沒有終點,它們永遠在流動,而“流動本身,正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這種生活,乃至這其中的一切有關自我認知的行為,最根本的核心價值所在[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