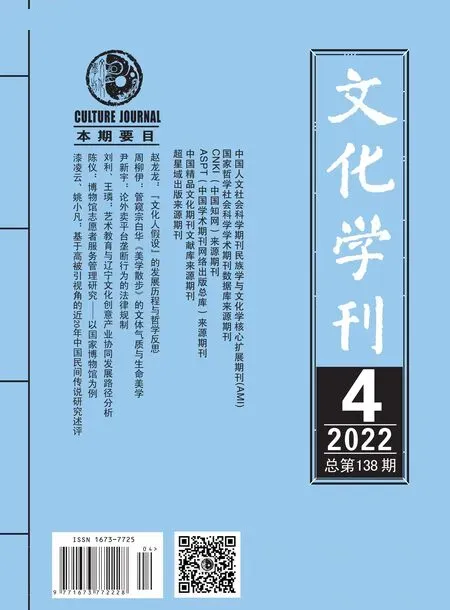顫栗的突圍者
——從《使女的故事》看女性自我意識的缺失與重構
趙琳琳 徐鵬飛 馮晨晨
美劇《使女的故事》改編自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小說,作家憑借這部小說摘得了英國文壇最高榮譽布克獎,根據該小說創作的同名美劇“橫掃”了第69屆艾美獎,引起廣大觀劇愛好者和小說愛好者的關注。
影片講述的是執政者為了解決生育率低下這個社會難題,將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保護”起來,通過訓誡和教導后分配給上層執政官,為執政官生育后代,但是在規訓過程中遭到女性不斷反抗的故事。本文通過層級研究、角色分析、主體消解以及意識重構等多種視角對《使女的故事》中的女性群體進行深度剖析,來探究其自我意識的缺失與重構過程。
一、階級的分化和被賦“使命”的群體
同小說描繪的社會狀況相似,影片展現了一個文明正在逐漸崩塌的社會。在社會經濟發展的背后,隱藏著諸多隱患,人類的身體健康和繁衍的后代正遭受著自然環境的威脅,造成整體社會生育率低下,面對該難題,政府迫切需要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多孕育后代,以此來提高社會的出生率。因此,執政者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將社會各階層進行明確劃分,女性被劃分為貴族夫人、教導者、使女和“非女人”。貴族夫人是執政官的配偶,負責協助丈夫出席活動并幫助丈夫維持家庭秩序;教導者被稱為“嬤嬤”,主要負責教導使女以及配合夫人管理日常瑣事,通過一些懲罰措施和感化政策來讓使女心甘情愿地為主教生育子嗣,為社會做出貢獻;使女是被控制人身自由的女性,她們具有生殖能力,被強制賦予延續后代的職責,被要求脫離原來的姓名和家庭,只負責為執政者提供生育服務;“非女人”是年齡較大、違反了規定和不具備生育功能的女性,她們被安排去做苦工或傭人。
影片主要通過抓捕、懲罰、殺戮的過程來展現社會的混亂和權力的濫用,借由人們的麻木和不茍言笑的表情來展現社會關系的緊張和冷漠。其中,具有階級劃分象征的黑、藍、紅和棕等不同顏色的服裝是一種隱形霸權,被區分的人沒有選擇服飾和裝扮自己的權利,這種區分將所有人的地位和職能置于明處,以便彼此監視。
女性在被迫接受階級劃分之前是社會事務的參與者:女主角瓊是位職業女性,她熱愛自己的事業,有戀愛的自由和娛樂的權力,她的女兒是她和丈夫愛的結晶,他們原本過著幸福的生活;瓊的朋友莫依是一個灑脫不羈,獨立并樂于享受生活的人;艾米麗是一位生物學家,具有較高的學識,同時也是一位出柜的同性戀者;高級執政官的夫人曾是參與制定政策的高層人員,因為階級劃分,她只能按照規定協助在國家權力機構工作的丈夫,做他的幕后支持者。
影片中的女性人物在最初都是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例如:瓊,對于愛情勇于追求,對于孩子疼惜萬分,對于在社會中遭遇的不公敢于挺身而出;執政官夫人,在丈夫面對社會難題時,為丈夫出謀劃策,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幫助丈夫在高層決策團中提升發言權;艾米莉,在專業領域有一席之地,在感情上敢于面對真實的自己。階級劃分之后,男性掌控和分化社會權利,女性被剔除出權力系統,喪失了社會功能,不能管理和支配自己的財產,同時,部分女性因為環境污染喪失了生育功能。女性群體迫于生存和角色功能喪失帶來的壓力,必須按照新的社會規則來規訓那些仍舊可以生育的同類:夫人和嬤嬤沒有生育功能,為了保全自己的權利和地位,用《圣經》感化和肉體懲罰來約束使女為執政者服務,不能生育的女性要想生存就需要“匍匐”在男權腳下,利用分配給她們的權利來統治另一群女性。具有生育功能的女性被劃分為使女之后在不同程度上會遭受一系列的打擊:如瓊的丈夫被槍擊(未死)、女兒被抓走、嬤嬤的懲罰、被迫和主教發生關系等都使得瓊痛苦萬分,陷入想要逃離但又尋路無門的境地。瓊被限制自由后,偶然間知道艾米莉私下通過各種途徑和境外組織取得聯系,并親眼目睹了艾米莉在逃離困境的過程中被監視機構發現并抓捕回去割除了陰蒂,伙伴的這次失敗出逃,增加了瓊對未來生活的恐懼。
女性在成為使女之后受到的是監視、懲罰和歧視,她們被重新賦予的社會角色和職責均是以犧牲她們的社會權利為出發點,社會給她們佩戴了一頂延續后代的高帽,卻期待她們的思想和意志能夠在“囚禁”與被監視中磨滅掉。
二、敵對的雙方和被單獨剝離的器官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真正社會主義的倫理學,就是說尋求正義,而不取消自由,給個體負擔但不消滅個體性。由于女人的狀況問題,它處于非常尷尬的局面,不可能把懷孕簡簡單單地比作像服兵役一樣的一種工作或服務”[1]81。影片中,女性被按照所屬功能進行分配后,女性生育子嗣被當作是一種工作或者是服兵役,這些具有生育功能的女性承載著整個社會存續下去的希望,她們本身享有的社會價值被磨滅,人的存在價值被壓制,尊嚴不再被提及,只剩下被過分放大的“優秀”的生育功能。這種安排深入而徹底地破壞了使女的生活,迫使她們無條件地將自己交付于社會掌權者,可是掌權者不直接掌控和摧殘使女,他們要保持高高在上的形象,需要借由不能生育的女性作為第三方來控制能夠生育的使女,使不同階級的女性成為敵對的雙方,形成制衡的關系。
影片中,訓誡和教導使女是嬤嬤的職責,安排使女和主教共處一室是夫人的職責。在訓誡過程中,使女會因為反抗而當眾遭受到酷刑和侮辱,這種被圍觀受罰也是一種規訓手段,可以起到震懾其他人的作用。夫人和嬤嬤,是使女反抗和斗爭的對象,她們是反抗的直接“受體”,會在規訓使女的過程中受到她們的憎恨,在她們的反抗過程中可能會受到使女的殺害。使女的身體“被作為一種工具所利用”,是各種力量交匯沖突的“地盤”,是“暗藏著各種危險的所在”[2]。使女的身體是所有人的關注點,使女如果違反了規定,其他人會受到懲罰,使女會因為生育功能而減輕懲罰。人們在暗地里進行角逐,女性和女性之間的關系非常微妙,她們都處于男性權威的籠罩下,受到男性權威的壓制,失去原本擁有的權力,她們想要生存必須依附于這個權力,按照男性所規定的那樣去敵對同性:夫人想要生存和保持地位需努力讓丈夫擁有后代,嬤嬤想要生存需依附《圣經》和懲罰手段讓使女“聽話”,使女想要生存需“隱藏”自我,依附和交出自己的身體。女性被男性設定為臣服者,同時女性和女性之間又是施壓者和反抗者,但是事實上她們都是男權社會的犧牲品和獻祭者。
身體是被鞭笞的對象,子宮是被崇拜的器官,意志是被消解的終點。“要求女人生孩子比管理公民的日常事務要更深入地破壞女人的生活:任何國家都從來不敢強制性交”[1]81。在列基國,夫人在床上懷抱使女,任由丈夫和使女發生關系,強迫使女附屬于所服務的主教,背離原來的姓名和家庭,代替夫人生育孩子,整個過程他們都不能直視對方,不然將被認為是一種冒犯,這種沒有任何感情的關系,深度地破壞了兩個家庭,打碎了女性的心理防線。使女的真正價值在于擁有可生育的子宮,如果子宮可以脫離母體而存在,可以設想女性在這個社會中幾乎沒有存在價值;使女的身體會受到懲罰和折磨,但是子宮不可以受到傷害;使女可以被殺害,但是孕育生命的子宮可以挽救她們的性命;使女的器官比生命更有價值。教導嬤嬤們通過使用嚴酷的電擊和《圣經》近乎“洗腦”般的訓誡來打造一個“被馴化了的身體”,以限定使女的活動范圍和行為規范來“消滅”使女頭腦中原本的認知和產生的抗爭意識,使其服從于社會分配的新的角色。影片主人翁瓊把自己比作“行走的子宮”,誠然,當靈魂和主體意識尚存時,女性遭到了“生育機器”般地對待,用“行走的子宮”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但是當權者制定規則和實施懲罰的目的在于消解女性的主體性,在那些失去主體意識和靈魂的那些女性身上,她們無異于子宮這個器官本身,是喪失了權力庇護而裸露在大眾面前的子宮,是因眾人聚焦的期望目光而顫栗的器官。
三、獻身的困境和在絕境求生的意志
影片中女性是要被秘密篩選的,生育過孩子的女性在通過安檢時,就會被國家機關強制留在國內并統一安排到一個地方,這些女性被告知她們擁有了一個光榮的職責:成為使女,生育孩子。人們不會強迫女人生孩子,但是會把她禁閉在某種處境中,孕育生命是她們唯一的出路:法律和風俗把婚姻強加給她,禁止避孕措施和人工流產,禁止離婚[1]82。在列基國,盡管當權者對使女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強迫女人懷孕不是最體面的做法,于是便有了冠以新的姓名,配予當權者,以及隨處可以看到的對《圣經》的誦讀以及對使女身體的管控和行為姿態的要求;作為使女的她們如果想獲得更近一步的自由和地位,那就是生育。這一群被劃分出來獻身的女性,是一群被訓練的肉體,按照權威的規定來進行揉捏和伸展,原本自由而激情的肉體在訓練中逐漸僵硬,最終實現思想上被馴化。影片中有一個細節:新孕育出來的小生命被眾多夫人圍觀,她們對這個小生命和這個家庭的夫人贊不絕口,而生育了這個孩子的使女被隔離在包圍圈外,完成生育職責的使女在面對被剝奪孩子的那一刻,也由最開始的喜悅變為驚訝和惶恐,最后語調中轉為哀求。處于此種獻身困境中的女性,她們就算依附于當權者也無法擺脫被左右的命運,也無法真正擁有自己的權力。
世上一向都有反抗自己社會角色的女人[3]。這個角色是周圍環境或社會現實安排給她的,不是女性心甘情愿接受的角色,也不是女性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形成的角色,所以女性要么被動接受,要么奮起反抗。影片中的使女們被安排了使女這樣一個角色,這個角色由社會需求創造而來,由設定好的場合、服裝、姿勢和態度將使女困在這個角色中,這些規則都是使女求生或逃離途中需要打破的藩籬。
規訓權力的成功無疑應歸因于使用了簡單的手段: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以及它們在該權力特有的程序—檢查—中的組合[4]。影片中的層級監視很明顯,里面的“天眼”是用來監視除了權力機構之外的人的,“天眼”之外還有教導嬤嬤以及家里的傭人,是為求得自己生存而為權力機構服務的人,她們滲透在“天眼”看不到的位置,也正是這些監視網絡導致使女在逃離困境的過程中屢次失敗。所以使女僅僅逃離這個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完全與當權者抗爭,只有聯合了所有類似于瓊這樣的反抗者,才能真正地重獲屬于自己的權力和自由。上文提到,使女被困于社會安排的角色中,主體性盡可能地被壓制和消解,但是在困境中求生是人的本能,重重壓制之下是人的反彈。燒掉衣服、改變迎合的態度和走出固定的場所等都是打破困境或逃離出角色設定的必要方式。使女在規訓中被壓制和消解主體意識,同樣在圍觀受刑和強制性交中重新構建主體意識,這個重構過程就是使女的反抗過程,而承受直接傷害的對象就是貴族夫人和嬤嬤:莫依和瓊將前任嬤嬤鎖在地下室,使得莫依成功逃出困境;艾米莉在垃圾場毒死了之前所屬家庭的夫人,作為對她的報復;夫人也逐漸意識到這個生病的社會不能再這樣發展下去,向當權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女們也認識到生育子嗣也不一定能獲得所謂的自由,私下逐漸聯合起來。
影片1—2季中,使女的抗爭過程尚未觸及到權力層級,但是她們一直試圖打破禁錮她們的條條框框:走出限制自由的場所,拒絕集體懲罰“犯錯”的使女,嘗試和境外組織取得聯系等等。這些抗爭只是對不想被看作是生育機器,反抗被分配的角色而做的努力,而聯合起來,反抗整個病態的社會才是救贖本身。強制女性生育本身就是對人性的踐踏,為了人口延續而剝奪女性的社會權力,只能刺激到那些被強迫的女性,使得尋求生的渴望和對公平的向往變成拯救自我的信念,這個信念促使女性強烈地想要在這個男權社會為自己吶喊,從而為自己的主體地位和自由而不斷抗爭。
四、結語
在現代社會,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依舊存在影片中表現出的現象。過分推崇女性生育功能和男性權威的情況正在導致女性的自我價值和自我肯定在喪失,但是也迫使女性逐漸向男性權威發起對抗,找尋自我。
無論是小說還是影視劇作都將著眼點放在女性這個本體上,以女性階級地位的弱勢和角色選擇的無奈來展現女性生殖力量的強悍,側面掩蓋了女性的社會價值和能力。在男性權力的滲透和運作中,以階級分化和身體懲罰為手段,以精神和意志消解為終點的權力壓制,使得女性急需尋回在社會上的主體地位,成為為自己權力和自由戰斗的發起者,成為打破男性權力網絡的一個突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