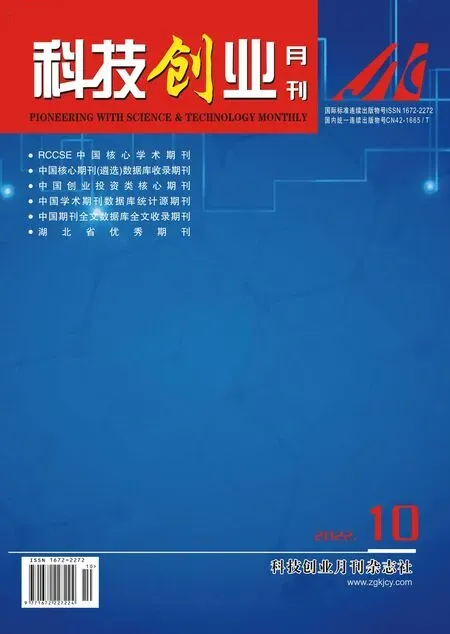組態視角下科技合作影響高校創新能力路徑
張明親,王曉宇,劉 璇
(1.西安工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2.陜西高校軍民融合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021)
0 引言
高校作為知識生產以及高層次創新人才培養的搖籃,是原始創新、前沿創新和顛覆性技術攻關的戰略高地,是從源頭上提升一個國家科技創新水平的關鍵[1]。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院校,在“211工程”“985工程”“2011計劃”以及“雙一流建設”的引導和推動下,高校科技創新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相比于世界一流大學,我國高校科技創新水平整體不高,尤其是引領性科研成果不足、頂級學科數少、在國際學術界擁有的話語權有限[2]。當前,我國正處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關鍵期,面臨著復雜的國際貿易保護以及技術封鎖的國際環境,如何提升高校科技創新能力,成為日益重要的戰略問題,這對深入落實創新驅動戰略,實現高等教育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為厘清高校科技創新的內在機理,學者們從多個角度進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總結起來可以概括為,高校科技創新能力是一種綜合能力,體現在知識生產、傳播和應用的全鏈條中,受創新資源的投入與利用[3]、科研組織模式[4]、國際化發展[2]等諸多先發條件的影響。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特征的不斷顯現,以共享共性知識為基礎的創新網絡越來越龐大,高校與政府、企業之間的合作以及跨越國家邊界的國際合作成為高校提升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現實中,我國政府為高校開展科技合作,從政策、資金、場地、平臺等方面加大了扶持力度,然而,高校科技合作對創新能力的驅動作用還具有明顯的“短板效應”[3],還缺乏與多元主體特征相對應的資源配置體系[4]。盡管已對高校科技合作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往往局限于校政企合作或國際科技合作的單一層面,忽視了開放式創新下多重因素并發的影響,導致現有研究結論仍然充滿爭議[5]。鑒于此,本研究運用組態思維,采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簡稱QCA),探究高校科技合作影響創新能力的多重因素以及內在機理,以期為高校深化科技合作,提升創新能力提供決策依據。
1 文獻綜述與理論模型構建
1.1 文獻綜述
為厘清科技合作影響高校創新能力的內在機理,學者們主要從官產學三螺旋[6]、知識創新[7]、協同創新[3]、跨組織合作[8]等視角展開研究,認為校政企合作與國際科技合作是高校提升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2,9]。從校政企合作來看,現有文獻主要從校企合作、校政合作兩個層面展開研究,但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從校企合作來看,研究結論有正向影響、負向影響和倒U型關系。李濤等[3]認為校企合作通過知識主體和技術主體的動態對接和優勢集成,對提升高校技術創新效率具有重要價值。李強等[10]發現校企合作渠道深度對高校科研績效有顯著的正向效應,且隨著合作渠道深度的增加,合作廣度和科研績效的關系也逐漸從倒U型變為正相關。Zhang等[11]研究發現產學合作強度對學術績效有負面影響。劉笑等[12]研究發現產學合作數量對學術績效的影響呈倒U型關系,李秀坤等[13]從校企合作網絡特性角度也得出了倒U型關系的結論。從校政合作來看,學者主要關注政府資金投入對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影響,但結論仍然充滿爭議。如原長弘等[5]通過對我國523所高校面板數據的分析表明,以政府資金支持表示的政府“引擎”對高校技術創新能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易紅郡等[14]則認為過高的政府投資會淡化企業對高校科技創新活動的成本分擔責任, 削弱高校創新活力。
與校政企合作不同,國際合作是高校從全世界范圍內尋找合作伙伴,可以獲得具有更高異質性和多樣性的知識與資源,更有利于思維的碰撞與智慧火花的激發[15]。事實上,位于知識鏈上游位置的高校在校企對接、國際合作、資源整合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16],能通過知識、人力、資本的跨組織動態集成[17],形成知識主體和生產主體的上游協同體[18],促進創新資源在“轉移能動性”和“轉移效力”的合作激勵[19];通過知識和技術的深度鏈接,形成外生資源整合和內生優化驅動效應[20],促進知識密集型經濟體形成[21]。功能豐富和類型多樣的異質性合作伙伴能給高校帶來更深層次的知識和技術交互[17],由不同異質性合作伙伴形成的科技合作之間具有交互效應。具體來說,高校的國際科技合作越活躍,從全球傳導到校政企合作系統的知識和信息就越多[22];而從國際性知識的學習、傳播再到新知識的產生,不僅依賴于專業的科研人員,更依賴于校政企合作系統內各創新主體在知識生產和使用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然而,現有研究多關注校政企合作或國際科技合作的單一層面,忽視了兩者的協同聯動效應以及多重因素的并發影響。事實上,高校科技創新受國際科技合作以及高校與政府、企業等創新主體多重合作情境的共同影響,需要充分挖掘多個層面前因條件的協同聯動。基于此,本研究從組態視角,探究校政企合作和國際科技合作兩個層面的不同前因變量組成的組態與高校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具體回答以下問題:校政企合作與國際科技合作的聯動能否促進高校創新能力的提升?其路徑有哪些?不同路徑間有何聯系?
1.2 理論模型構建
1.2.1 校政企合作與高校科技創新
校政企合作是指高校與政府、企業等異質創新主體以共同參與、共同投資、共享成果、共擔風險為準則而達成的契約安排[23]。在知識經濟時代,高校成為知識中心的關鍵是作為跨邊界組織,為隱性知識和編碼知識的交流搭建橋梁。高校與政府、企業之間的合作可以通過組織之間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協調機制,形成有效的知識傳播模式,進而促進創新系統的演化和升級。在校政企合作中,政府作為制度創新者,主要負責為良性有效的創新環境提供資金扶持與制度支持;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主要負責研發成果的轉化與應用;高校作為知識創新的主體,主要負責知識的生產、傳播和轉移。在大學、產業、政府三螺旋創新體系中,高校與政府和企業的相互作用是改善創新條件的關鍵,能夠帶動高校在實現知識資源共享的基礎上提升自身整體實力和影響力[24]。根據組織特性以及創新主體的聚集情況,將校政企合作劃分為校企合作(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簡稱UE)、校政合作(university-government cooperation,簡稱UG)以及校政企協同(university-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簡稱UGE)3種形式。
校企合作(UE)是高校與企業之間通過知識、人力、資本的動態集成[17],實現雙方間知識的互補[25],以提升研發成果的科學性、實用性和市場性,進而促進校企雙方創新績效的提升。校企合作不僅能將高校現有研究成果運用于企業實踐,也能將企業實踐中的問題反饋到高校,促進高校應用研究與科研績效的提升[26]。同時,高校與企業合作可以增加科研人員研究活動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提高科研人員對生產技術和市場知識的理解、拓寬科學研究的思路與知識邊界,提高科學研究的產量和質量[27]。事實上,高校與企業的合作可以通過技術咨詢、聯合研究、衍生企業、學術論壇和會議等多種渠道展開[10],不同的渠道能使高校科研人員更好地發現和認識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企業所面臨的技術難題,拓寬知識邊界,提升高校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效果[28]。
校政合作(UG)是高校與政府攜手共同解決產業轉型升級以及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問題。在我國,政府作為高校的管理者與投資者,高校與政府之間具有天然的合作關系。一方面,政府通過資金扶持、項目對接等方式引導支持高校的科技創新活動;另一方面,政府通過科技創新政策,引導高校科研資源與產業資源的有效融合,促進高校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根據市場失靈理論,高校作為基礎研究的承擔者,其科技創新活動具有“公共性、基礎性、社會性”等特征,政府以社會效益為目標驅動,對高校科技創新活動進行引導和資助,其資金撥款及地方政府的經費支持是高校科技創新活動的重要保證[4],尤其是在基礎研究和科學知識的產出方面,校政合作有助于以專利數量衡量的高校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28]。
校政企協同(UGE)是高校以自身的特色學科以及優勢知識,通過集聚政府與企業的創新資源,形成政府與企業共建高校科研創新平臺、共享高校知識創新成果的格局。高校擁有廣泛的校友資源以及知識創新平臺,是各類知識流動的關鍵節點。從知識生產II模式角度來看,高校的科技創新涉及從科學研究到科技創新以及從科技創新到產業化的過程。盡管校政攜手有利于解決高校科學研究中的資金問題,校企合作可有效對接產業需求,然而緊密的校政合作可能會淡化企業對高校科技創新活動的成本分擔責任、削弱高校創新活力[14],緊密的校企合作也可能使高校以犧牲基礎研究和科學知識為代價,忽視科學知識發展的長遠目標[30]。而校政企三方的合作與協同有利于高校平衡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開發創新之間的關系,強化其在創新鏈上的定位與分工,促進高校整體創新績效的提升。
1.2.2 國際合作與高校科技創新
國際合作是高校提高自身應對性和國際競爭力的必然要求[31],是將國際的和跨文化的維度整合到大學的教學、研究和服務功能中的過程,是大學全球擴張和知識傳播的產物。一所大學的國際科技合作的決定性因素并不在于規模、位置、預算,而是高校教師與科研人員的跨國流動與雙向信息傳遞[32]。一方面,高校教師與科研人員通過跨國交流能使其學術成果傳達到國際學術圈,產生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跨國的學術交流能使高校教師與科研人員接觸到學科前沿,快速更新知識和能力結構。相對于沒有跨國流動經歷的本土科學家,外籍科學家以及海歸科學家搭建的國際科研合作網絡規模更大,發表論文的影響因子也更高[33]。從知識管理角度來看,高校的國際科技合作是以自我完善為目的的知識資源整合過程。一方面通過國際化聯合研發、國際會議等增加顯性知識的國際傳播;另一方面通過教師與科研人員的國際交流增加隱性知識吸收[22]。從國際性知識的學習、傳播再到新知識的產生, 不僅依賴于高校對新知識的傳播和吸收能力,更依賴于國際科技合作的路徑。高校國際科技合作按照教師與科研人員的去向不同可劃分為走出去合作(go out cooperation,簡稱GO)和引進來合作(come in cooperation,簡稱CI)。
走出去合作(GO)是高校將優秀教師和科研人員派往國外訪學、進修、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以及開展多種形式的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以提高教師與科研人員的國際視野與高校學科影響力。從個人層面來看,走出去合作能使高校的教學與科研人員增加接觸新知識的機會,便捷利用國外先進的學術資源以及科研平臺進行知識更新,有效地進行顯性知識的交換和隱形知識的吸收,較快地抬高學術研究的起點,達到學術上的位能平衡。從高校層面來看,走出去合作是高校與國外不同學術組織之間的跨國知識網絡形成的過程。走出去合作的范圍越廣、程度越深,高校更有可能建立一個包含多元化、互補性的跨國知識網絡[34],并通過教師、學術組織的知識鏈接,觸發和產生多樣化的知識,進而通過知識流動擴大多元化知識組合和轉化為創新的組合空間,推動高校學術創新產出與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
引進來合作(CI)是高校通過科學有效的人才激勵與人才流動機制,吸引國外知名高校以及科研機構的一流學者來校授課、講學、合作研究等,為高校的人才培養、學科建設以及科研創新提供支持。高校科技創新不僅涉及新知識的創造和應用,更涉及新舊知識要素的新穎組合。引進來合作通過集聚不同國籍、不同領域的外籍專家,能使高校獲得不同領域的學科發展前沿,幫助科研團隊選擇更合適的創新方向,有效識別和獲取創新所需要的重要知識[35]。同時,由于大量的知識具有隱性特征,只有通過頻繁的人際溝通和互動才能夠克服“粘性”,跨越組織邊界和地理邊界進行有效傳遞。引進來合作能通過與外籍專家的面對面交流增加對新知識的學習和獲取途徑,促進對復雜知識和隱性知識的理解,利于知識在更多受眾、更多主體間全方位、多形式的傳播,進而提升高校整體科技創新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高校科技合作驅動創新能力的機制模型
2 研究方法與設計
2.1 研究方法
QCA是一種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旨在解決多重并發因果關系的復雜現象[36],其基本思想是運用集合論和布爾運算方法,探究前因條件組合如何引致被解釋結果出現多條等效路徑[37]。與單一因果模型的主流統計方法相比,QCA方法解決了單個變量的獨特效應可能被相關變量掩蓋的問題,能在多個可比較的案例之間確定不同因果模型的數量和特征,解決了大樣本分析不能解決的因果復雜性問題[38]。高校科技創新是一個多要素投入、多主體互動的復雜過程,采用QCA方法可以更加真實反映高校的科技創新實踐,能深入挖掘校政企合作與國際科技合作2個層面的5個條件所構成的組態與高校科技創新之間的聯系。
2.2 變量選擇與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高校作為承擔教學、科研及社會服務的機構,科研活動及知識產出成果類型各異,用單一的指標難以客觀反映高校真實的科技創新能力,需要用復合指標去衡量。艾瑞深校友會的自然科學排名由國家科技獎勵、省部級科技獎勵、國際科技獎勵、高水平論文、專利獎、著作獎、技術成果轉讓收入等七大指標組成,旨在體現中國高校服務國家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以及國際學術影響力,較為全面地反映了高校科技創新能力,故本研究以其自然科學得分衡量高校科技創新能力。
考慮到高校的科技經費是高校創新能力得以形成的關鍵,且數據具有較高的可比性,本研究用政府對高校的人均科技經費撥入衡量校政合作,用企事業單位委托的高校人均科技經費投入衡量校企合作,用政府科技經費投入與企事業單位委托經費的匹配情況衡量校政企協同。具體地說,用兩者的比值減去1后的絕對值測算協同程度,若計算值接近0,認為校政企高度協同;反之,若計算值遠大于0,則認為校政企低度協同。對高校國際科技合作的衡量,考慮到教師是國際合作的“引擎”,以科研和學習為目的跨境流動是教師參與國際合作的主要形式。借鑒以往研究[22],以合作研究的派遣人次和接受人次分別衡量高校走出去合作和引進來合作。這5個前因變量的數據均來源于《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
考慮到高校科技創新投入的波動性與產生效益的滯后性,本研究以2015-2017年的平均值作為測算前因變量的依據,以2016-2020年的自然科學得分衡量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為了保證案例總體的充分同質性和最大異質性[38],本研究將案例限定在教育部直屬高校,剔除師范類、藝術類和政法類等非科研類高校,最終進入 QCA分析的高校共有56所,樣本規模與QCA方法的5個條件變量匹配。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1。

表1 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2.3 變量校準
模糊集具有定性和定量的雙重屬性,通過變量校準使案例的集合隸屬于0~1 之間。變量校準需要依據理論和實踐知識或標準設定3個臨界值:完全隸屬、交叉點以及完全不隸屬。參考已有研究[37],本文將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的3個錨點分別設定為其樣本數據的上4分位數、上4分位數與下4分位數的均值以及下4分位數。對于非高創新能力而言,其校準規則與高創新能力正好相反,即取高創新能力的非集。各變量的校準錨點如表2所示。

表2 各變量校準錨點
3 實證分析
3.1 單項前因變量必要性與充分性
運用FsQCA對各個前因變量是否為結果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進行檢測(見表3)。由表3可知,無論是從必要性視角還是從充分性視角看,各個單項前因變量對高創新能力以及非高創新能力的影響均未超過 0.9,說明5個單項前因變量對高校科技創新能力不構成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意味著各個單項前因條件對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解釋力較弱。因此,下文將這些前因條件納入FsQCA,進一步探索產生高創新能力的組態。

表3 條件變量必要性與充分性檢驗結果
3.2 組態分析
運用FsQCA3.0對56所教育部直屬高校校準后的數據進行處理,得到了復雜解和簡約解,經過反事實分析獲得了中間解。通過對簡約解和中間解的比對,對組態中的核心條件和邊緣條件進行區分。由表4可知,產生高創新能力的組態有4條,且一致性指標分別為 0.782、0.819、0.852、0.875,說明4個組態都是高創新能力的充分條件。總體一致性指標為 0.816,覆蓋度為 0.695,說明4個組態解釋了約70%的高創新能力的原因。同時,假設每個條件變量缺失都可能導致非高創新能力,得出產生非高創新能力的組態有3條,且一致性指標分別為 0.867、0.885、0.940,總體一致性指標為0.853,說明這3個組態都是非高創新能力的充分條件。

表4 產生高、非高創新能力的組態
3.2.1 高創新能力
校政企協同型。該路徑表示校政企的協同可以產生高創新能力,此路徑的構型是組態H1(UE*UGE*~GO)。該構型表明在缺乏走出去合作時,校企合作與校政企協同的聯動可以產生高創新能力。可能原因是,校企合作在將高校現有研究成果運用于企業實踐的同時將企業實踐中的問題反饋到高校,促進高校科技創新活動的開展[29],然而,校企合作和學術產出之間具有替代效應,導致高校可能會以犧牲基礎研究和科學知識為代價,承擔更多的應用研究和商業活動[32]。而校政企的協同可以弱化校企合作對高校創新活動產生的擠壓效應,強化校政企三方在創新鏈中的功能與定位,發揮高校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中的主力軍作用。因此,在缺乏走出去合作時,校政企的協同能使高校真正成為知識創新的中心,在實現知識生產、傳播和轉移的基礎上,帶動高校自身整體實力和影響力的提升。此組態的典型案例有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華北電力大學、長安大學等行業特色鮮明的工科類大學。
校政企協同-引進來合作聯動型。該路徑表示校政企協同與引進來合作的聯動可以產生高創新能力,此路徑的構型是組態H2(UGE*~GO*CI)與組態H3a(UE*UGE*CI)。可能的原因是,大學作為知識生產、擴散和開發的主戰場,其科技創新活動具有公共性、基礎性、社會性等特征,校政企協同有利于高校在政府政策以及資金支持下強化在創新鏈上的定位與分工,主動與企業實現創新鏈上的無縫對接。然而,從建設科技強國、服務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言,我國高校在基礎研究、前沿創新等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而引進來合作能夠充分發揮海外專家的作用,幫助高校科技人員掌握全球知識創新與生產轉化的動向,發揮高校在原始創新、突破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同時,在實現全球性知識資源共享的基礎上,促進對復雜知識和隱性知識的理解,有效識別創新所需要的重要知識,提升高校在整個創新鏈條上的創新水平。因此,高校通過校政企協同與引進來合作的聯動可以產生高創新能力,此組態的典型案例有中國礦業大學、江南大學、天津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南交通大學、東北大學等學科特色較為明顯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學。
全方位合作型。表示校政合作、校企合作、走出去合作與引進來合作的四方聯動可以產生高創新能力,此路徑的構型是組態H3b(UG*UE*GO*CI)。可能原因是,現代大學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校政合作有利于高校在政府資金的支持下,面向前沿創新開展科學研究。校企合作有利于高校科研人員精準把握企業在實踐中面臨的實際問題,提升科研工作成效。走出去合作有利于科研人員便捷地利用國外先進的學術資源與科研平臺進行知識更新,抬高學科的學術起點。引進來合作能使高校針對科技創新的實際需要,充分發揮海外專家的引領作用,推動高校向世界一流水平發展。因此,校政合作、校企合作、走出去合作與引進來合作的四方聯動,能使高校在全球建立廣泛的社會聯系,促進知識跨越國家邊界進行流動,助推高校進入世界一流大學。此組態的典型案例有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東南大學、浙江大學等綜合性研究型大學。
3.2.2 非高創新能力
為更全面深入地探索提升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驅動機制,本文基于QCA方法的因果非對稱性進一步分析導致非高創新能力的組態。從表4可知,產生非高創新能力的組態有三條,但通過對案例高校的路徑隸屬度的對比發現,出現在組態NH2中的高校均以更高的路徑隸屬度出現在組態NH1或組態NH3中,因此,本文重點對組態NH1與組態NH3進行分析。
組態NH1:~UG*~UE*~UGE,表示非校政合作*非校企合作*非校政企協同的聯動會抑制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高校科技創新活動是一個投入產出的過程,其科技經費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投入以及企事業單位的資金投入。若缺乏校政合作,高校可能享受不到各級政府的科技政策紅利或關鍵科研設施建設得不到政府資金支持;缺乏校企合作,高校的科研活動可能會與實踐脫節,創新成果也可能因不能有效轉化而失去應用價值;缺乏校政企協同,高校的科研活動可能會因經費不足或與實踐脫節而無法落地轉化。因此,非校政合作*非校企合作*非校政企協同的聯動會抑制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
組態NH3:~UE*~UGE*GO*~CI,表示非校企合作*非校政企協同*走出去合作*非引進來合作的聯動會抑制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可能的原因是,走出去合作盡管可以使高校科研人員較快地抬高學科的學術起點,短期內會在學術創新上有所成就。但如果缺少校企合作,可能會導致科研活動與實踐的脫節;缺少校政企協同,可能會導致科研活動得不到政府與企業的支持;缺少引進來合作,可能會導致卡脖子科學問題得不到突破,進而抑制高校創新能力的提升。因此,非校企合作*非校政企協同*走出去合作*非引進來合作的聯動會抑制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
4 研究結論與管理啟示
4.1 研究結論
本文以教育部直屬高校為樣本,應用組態思維與QCA方法探討校政企合作與國際科技合作影響高校創新能力的多重并發因素和因果復雜機制。通過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1)校政企合作與國際科技合作聯動產生高創新能力的路徑包括校政企協同型、校政企協同-引進來合作聯動型以及全面合作型3條。通過對案例高校的進一步分析發現,校政企協同型更能促進行業特色鮮明的工科高校提升創新能力;校政企協同-引進來合作聯動型適用于學科特色突出高校和多科性研究型大學;而全方位合作型對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創新能力提升更為有利。
(2)相較于走出合作,引進來合作更能促進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在組態H2、H3a、H3b中,引進來合作均作為核心條件出現,說明引進來合作是產生高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構念。同時,引進來合作與校政企合作的聯動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在缺少走出去合作時,引進來合作與校政企協同的聯動可產生高創新能力;在存在走出去合作時,引進來合作與校企合作、校政合作的聯動也可產生高創新能力;當引進來合作與校企合作、校政企協同聯動時,則不受走出去合作的影響。
(3)研究發現影響高校科技創新活動的組態內部各要素之間的替代性與互補性。對于高校科技創新活動而言,校政企協同與校政合作之間存在替代作用,即在產生高創新能力的組態中,若存在校政企協同,校政合作必不出現。因此,在以高校主導的創新體系中,校政企協同和校政合作具有完全替代作用。
(4)研究發現了抑制高校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前因變量。在產生非高創新能力的組態中,非校企合作均出現,說明缺少校企合作是抑制高校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前因變量。同時,產生非高創新能力的組態與高創新能力的組態存在因果的非對稱性。
4.2 管理啟示
(1)高校要根據自身學科優勢及發展定位選擇科學的路徑以促進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對于行業特色鮮明的高校可選擇校政企協同型,即充分發揮行業特色的優勢,面對國家戰略需求,密切與行業龍頭企業的合作,通過共建國家級協同創新中心、共同承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等提升創新能力。對于學科特色突出與多科性研究型大學可選擇校政企協同-引進來國際化聯動型,即充分發揮特色學科的優勢,圍繞國家戰略需求,整合校政企之間的資源,通過搭建國際合作平臺,吸引高層次的海外專家以促進學校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對于綜合研究型大學可選擇全方位合作型,即通過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密切與政府、企業的合作關系,通過全方位、多層次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高校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
(2)校政企協同是促進高校創新能力提升的關鍵。高校作為知識生產與擴散的中心,具有顯著的知識溢出效應。校政企協同能使高校充分發揮知識對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實現科技成果的落地轉化。高校應充分利用自身的學科優勢、研究力量以及平臺資源,積極對接國家戰略需求,通過協同攻關、開放共享形成前沿研究集聚效應;通過對政府、企業科技創新資源的集聚與合理配置,提升科技資源投入效率及科技成果產出質量,進而促進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
(3)選擇引進來合作對創新能力更具有促進作用。在知識傳播和研究越來越全球化的時代,跨越國家邊界的科技合作是推動高校創新能力提升重要途徑。相對于走出去合作,引進來合作能使高校集聚全球優秀研究者的智慧,激發科研人員的研究熱情、盤活高校的科技資源,從而提高科研產出的數量和質量。高校應以國際化的視野創新大學國際合作模式,通過成立國際學院、建設國際合作平臺、舉辦國際學術交流會議等吸引海外優秀專家來校進行科技合作,促進我國一流高校盡早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科技創新的戰略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