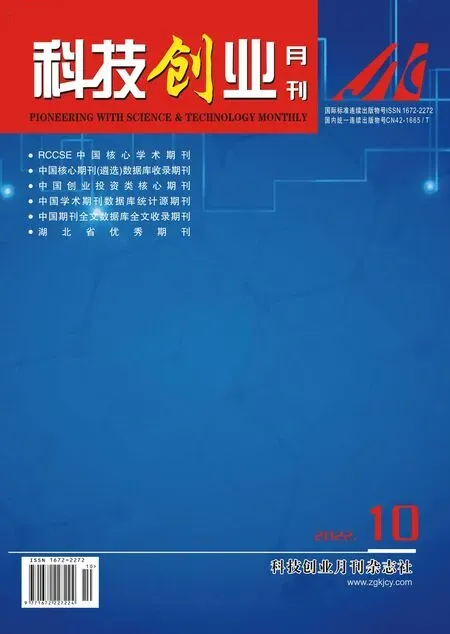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特征研究
李心怡,楊中華,2,3,姚詩奧,杜宇萌
(1.武漢科技大學 恒大管理學院;2.湖北省產業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3.武漢科技大學 服務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65)
0 引言
數字技術在現代經濟活動中得到了廣泛應用,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1]。長江中游城市群具有承東啟西、承南啟北的獨特區位優勢,作為我國中部地區唯一一個國家“十三五”規劃確定的重點區域,該城市群的數字化進程在全國范圍內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以長江中游城市群為研究對象,研究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特征,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長江流域的發展形勢,促進長江中游地區縱深發展,為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新格局提供科學依據。
學者對數字經濟的研究主要從3個方面展開。首先是對數字經濟發展程度的衡量,趙濤等[2]對2011-2016年全國222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城市經濟發展質量,同時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非線性增長和空間外溢的特征。其次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分析,主要是從宏觀經濟角度和數字基建角度進行。賈奇[3]通過構建VAR結構模型,實證分析表明數字基礎設施的滲透、投資和規模將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第三是數字經濟效應研究。胡躍藍[4]認為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影響有顯著的空間溢出特征,主要體現在數字經濟的提升對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對周邊地區均有正向作用。
目前學者對數字經濟屬性特征的研究較多,對數字經濟的空間關聯性的研究較少;對省級數字經濟的研究較多,對市級數字經濟研究較少;研究對象大部分都是全國城市或者是長三角地區,對于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研究較少。本文運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社會網絡分析法,選取合適的指標數值測度來分析2019年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情況,揭示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特征。
1 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1.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
數字經濟是建立在信息技術與網絡技術應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繼農業革命后人類社會又一次偉大變革[5]。左鵬飛和陳靜[6]認為,數字經濟不是獨立于傳統經濟社會系統之外,而是以新的動力嵌入到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體系中,融合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中,推動經濟體系的發展。本文依據賽迪顧問發布的《2021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報告》選用的數字經濟評價指標數據,從數字基礎、數字產業、數字融合三方面選取代表性指標,通過計算相關指標的幾何平均數來評價各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其中,以移動電話用戶數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作為量化數字基礎指標,以電信業務收入作為量化數字產業指標,部分城市由于缺乏數字融合的指標數據,選擇了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指數、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數和數字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指數作為量化數字融合指標。
1.2 空間關聯關系的確定
Tinbergen在1962年提出引力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利用兩個物體間存在相互吸引或排斥作用來描述物質運動規律。參照余海華[7]和趙放等[8]所構建的引力模型,進行修正后測算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引力水平,公式如下:
(1)

利用公式(1)可以計算出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的引力矩陣。采用引力矩陣中每一行的平均值作為該行的閾值。當大于或等于臨界值時,表明這個行和其他行間具有較高的關聯度,并將引力矩陣的元素設定為1;如果小于該行臨界值,說明它們之間無關聯性,并將引力矩陣的元素設定為0。由此可以求得一個0-1型矩陣。
1.3 空間關聯網絡的構建與分析
將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各個城市看作是一個節點,將各個城市群間的數字經濟聯系看作是邊,同時考慮到它們的聯系方向性,構建一個有向的關系網絡。使用Ucinet軟件可以分析網絡的關聯性特征、中心性特征、凝聚子群等。
(1)網絡關聯性。一般用網絡密度刻畫社會網絡中的節點之間的連線的緊密程度,密度越大,網絡關聯越緊密;用關聯度表示網絡結構內各點之間關聯的可能性,關聯度越大,網絡聯結程度越強;用效率代表網絡中多余的連線所占比例,效率越大,關聯網絡穩定性越差;用等級度衡量網絡節點之間在多大程度上非對稱可達,等級度越大,網絡層級結構越森嚴[9]。
(2)網絡中心性。網絡“中心性”能夠描述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在社會網絡中的權力或中心位置[10],通常采用點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來刻畫網絡中心性。點度中心度代表著某一節點在整個網絡中所起作用的大小,點度中心度越大表示這些點的影響力也就越大,說明該城市與其他城市產生的數字經濟聯系越多;接近中心度是從該點到其它點之間的捷徑距離的總和,接近中心度越大,該點經濟交流就越容易;中介中心度是一個點位于圖中其他“點對”的“中間”程度,它衡量了行動者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資源。
(3)塊模型。凝聚子群分析是當網絡中的部分成員之間關系尤為密切,形成了多個子群與小團體時,分析網絡中存在的不同子群特點以及子群相互關系。本文采用基于“子群內外關系”的凝聚子群分析進行塊模型分析,將數字經濟的空間關聯網絡分為凈受益板塊、凈溢出板塊、雙向溢出板塊和經紀人板塊4個主要板塊[11]。
1.4 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長江中游城市群共有31個城市,因數據缺失問題排除潛江、仙桃、天門后,共計28個城市;用百度地圖測量求出各個城市間的地理距離,涉及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標來自北京大學數字金融普惠指數第二期數據;其他計算數據變量均參考《中國統計年鑒》,選取2019年數據作為樣本數據。
2 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的實證分析
2.1 關聯網絡的關聯性
將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強度矩陣引入Ucinet中并使用NetDraw軟件繪制得到2019年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圖(圖1)。

圖1 2019年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
由圖1觀察到,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數字經濟發展網絡具有明顯的通達性,即每一個節點都連接著多個地區;同時也表現出集聚性特點。從整體來看,武漢和長沙作為核心樞紐城市對整個城市群有著極大影響,是主要的關聯關系發出者與接受者,能相互聯通3個省份。其次,南昌、宜昌、襄陽、黃岡是促進周邊城市共同發展的橋梁,梯度特性明顯。除此之外,在地理空間上呈現了三省“核心區域強”的總體態勢。
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密度為0.166 7,觀測到的聯動溢出效應僅為16.67%,表明網絡中城市間的關聯度不夠強,城市間的重疊關聯冗余溢出效應相對較弱;網絡關聯度為1,表明城市間互聯互通程度高;網絡效率為0.820 5,說明城市間存在一定的關聯冗余,網絡凝聚力較差;網絡等級度為0,表明各個城市的級別分布較為均勻,沒有出現“金字塔”式的區域格局。總體而言,從密度、關聯度、效率和等級度的指標上可以看出,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存在明顯的溢出效應且穩定性較差,在互通可達的基礎上不存在等級結構,但各城市之間的關聯不緊密。
2.2 關聯網絡的中心性
表1為2019年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數字經濟的空間關聯網絡中心性指標測評結果。

表1 2019年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中心性指標
(1)點度中心度。點度中心度最大值為77.778,最小值為11.111,均值為23.810。超過點度中心度平均值的城市有8個:武漢、長沙、南昌、宜昌、襄陽、鄂州、黃岡、新余。其中武漢和長沙是我國中部地區最大的省會城市,其點度中心度均不低于74.074;在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中,這些城市與其它城市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處于關聯網絡中的領導地位。
點度中心度最高的是武漢,這主要是因為它與其他27個城市中21個城市有空間關聯關系。超過點度平均值的8個城市中,有5個位于湖北,這意味著湖北在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數字經濟發展中居于核心位置。數據顯示,岳陽、咸寧、黃石的點度中心度排名靠后,說明這些城市在與其他城市的數字經濟的空間關聯較少。
武漢、長沙和南昌的點度中心度均高于平均水平,表明省會城市對整個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相關性和溢出效應有較強的影響。同時,通過對表1中點出度、點入度的計算,得出以下結論:平均點出度為4.5,高于平均水平的有13個城市,主要分布在湖北、江西等省;平均點入度為4.5,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有9個,是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主要承載地。
比較點度中心度的出度與入度,出度小于入度的城市有南昌、武漢、鄂州、黃岡、孝感、長沙、株洲、湘潭、益陽,這些城市大力發展數字基礎設施,能夠實現區域內的集聚效應。在出度不小于入度的其他城市,數據要素資源溢出規模大于數據要素資源聚集規模,這可能是因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尚處于萌芽階段,對新興數字產業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不大[12]。
(2)接近中心度。長江中游城市群接近中心度最大值為81.818,最小值為45,均值為54.255。超過接近中心度平均值的城市有8個:武漢、長沙、襄陽、新余、九江、鷹潭、上饒、黃岡,表明這些城市能夠迅速與其他城市關聯。這些城市擁有較強的產業集聚優勢,而且不斷優化數字化建設和技術創新,使其更有能力獲取數字經濟要素資源,使技術流、資金流、數據流等更具流動效率。
在數字經濟空間網絡中,武漢的接近中心度最大,為81.818,這意味著在數字經濟空間關聯網絡中,其他城市與武漢的“距離”最短,是整個數字經濟空間關聯網絡的中心。而低于接近中心度平均數值則說明這些城市缺乏對周邊區域的吸引力,無法帶動周圍城市發展。長江中游城市群內部存在明顯不均衡現象,排名最后3個城市鄂州、宜昌和株洲,它們是空間關聯網絡體系中的邊緣行動者。其中鄂州和株洲存在傳統模式難以適應數字經濟產生的新商業模式、數字基建尚起步、經濟發展規模較小等問題。但宜昌的經濟規模較大、有較好產業基礎,位于湖北省中部地區,地理位置特殊,也能享受到更好的政策優惠。其數字經濟接近中心度小的原因可能在于行業規模不大、應用場景不多。
(3)中介中心度。長江中游城市群中介中心度最大值為33.449,最小值為0.263,均值為3.348。超過接近中心度平均值的城市有3個:武漢、長沙、南昌。武漢作為核心城市具有較強的中介服務功能;長沙的中介中心度級別較高;但南昌的中介中心度略高于中等水平。這3個城市合計占2019年數字經濟空間關聯網絡中介中心度總數的69.933%,表明這3個城市的數字經濟資源占有較大比重,是其他城市關聯溢出的關鍵節點,是數字經濟發展關聯網絡“橋梁”。
綜上所述,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的城市個體結構特征是不平衡、不充分的,數字經濟聯動主要通過武漢、長沙、南昌等發達經濟體來實現。其中武漢3項中心度指標均排第一位;長沙3項中心度指標均排第二位;南昌的點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2項指標排第三位,但接近中心度指標排名卻不理想。這說明南昌與武漢、長沙相比,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些許差距,且更易受網絡中其他行動者的控制。
2.3 關聯網絡的塊模型
本文采用塊模型進行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凝聚子群分析,選擇最大分割深度為2,可將28個城市劃分為4個板塊(表2)。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的關聯性和區域差異性。其中,第一板塊成員數量為4個,分別是南昌、鄂州、宜昌、武漢;第二板塊成員數量為4個,分別是湘潭、株洲、長沙、新余;第三板塊成員10個,分別是萍鄉、上饒、九江、景德鎮、鷹潭、吉安、黃石、撫州、咸寧、宜春;第四板塊成員10個,分別是荊州、黃岡、孝感、襄陽、荊門、衡陽、岳陽、常德、益陽、婁底10個城市。

表2 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板塊的溢出效應
板塊1的內部關系為0,也就是說,板塊1內的南昌、鄂州、宜昌、武漢4個城市之間沒有直接聯系。從圖1可以看出,板塊1內部城市間的聯系是通過其他板塊所屬城市間接聯系,如南昌到武漢經九江、上饒等,武漢到宜昌經襄陽、岳陽。該板塊接收關系數遠大于板塊發出關系數,屬于“凈受益板塊”。該板塊產業集聚數字經濟發展資源的能力較強,且接收資源水平大約是外溢資源水平的2倍。
板塊2對其他板塊有較強的外溢效應,板塊內部也有較強的溢出作用,屬于“雙向溢出板塊”。該板塊既要抓住數字經濟從其他城市流入,又要抓住數字經濟向其他城市流出。該板塊促進區域內數字經濟的良性互動并產生了顯著的雙向外溢作用。湘潭、株洲、長沙、新余等城市擁有良好的數字經濟基礎建設和創新技術,可以把它歸為“雙向溢出”板塊。
環鄱陽湖城市群及武漢城市圈所構成的板塊3內部關系比例低,而且接收到的數字經濟要素資源也相對少,因此可歸為“凈溢出”板塊。該板塊對其他板塊的溢出作用要大于收到其他板塊的溢出作用,數字經濟要素資源會向其他板塊流動。從城市角度觀察,在板塊3中的大部分城市都有箭頭指向長沙、武漢兩城市。結合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圖,從板塊角度觀察,板塊3的數字經濟要素資源主要向板塊1和板塊2流出。
板塊4接收和傳輸來自其他板塊的聯系,是一個典型的“經紀人板塊”。在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傳遞資源要素能力較好,且通過“經紀人板塊”與其它板塊相互連通,形成了區域內的整體聯動。
同時,為了研究數字經濟在板塊之間的溢出效應,需要計算出每個板塊的分布密度矩陣。2019年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的網絡密度為0.166 7,若密度矩陣值大于0.166 7則賦值為1,若密度矩陣值小于0.166 7則賦值為0,可以把密度矩陣轉換成像矩陣(表3)。

表3 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板塊的密度矩陣與像矩陣
從表3可以看出:板塊1和板塊2對板塊3、4都有溢出效應,且板塊1的溢出效應大于板塊2,但板塊2有內部溢出效應;板塊3和4對板塊1、2都有外溢作用,且板塊3的溢出效應大于板塊4。綜合表2、3,可以看到長江中游城市群中的數字經濟傳導機理,數字經濟發展關聯網絡的核心是板塊1(武漢、南昌)和板塊2(長沙),對板塊3和板塊4的數字經濟發展發揮著引領作用。這一特點也反映了三省數字經濟發展策略:以省會城市為牽引極,帶動網絡邊緣城市的發展潛力,構建“一極兩帶”“一圈三群”“一主兩副”的發展格局。
3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3.1 研究結論
本文使用修正的引力模型與社會網絡分析法分析了2019年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空間關聯網絡的特征,可得如下結論:
(1)網絡關聯性特征表明,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冗余,相關性較小,網絡結構不太穩定,但城市間網絡沒有等級結構,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互通互達。
(2)網絡中心性特征顯示,武漢、長沙、南昌、宜昌、襄陽、鄂州、黃岡、新余這8個城市是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網絡中的先行者。同時武漢、長沙、襄陽、新余、黃岡這5個城市在數字經濟空間關聯網絡中也占據核心地位;另外,武漢、長沙、南昌等地的控制力也比較強。
(3)從塊模型看,長江中游城市群可以劃分為4個板塊。南昌、鄂州、宜昌、武漢等4個城市構成板塊1,屬于“凈受益板塊”;板塊2有湘潭、株洲、長沙、新余4個城市,該板塊內部及對板塊3、板塊4均有大量溢出關系,屬于“雙向溢出板塊”;板塊3有萍鄉、上饒、九江、景德鎮、鷹潭、吉安、黃石、撫州、咸寧、宜春10個城市,屬于“凈溢出板塊”;板塊4有荊州、黃岡、孝感、襄陽、荊門、衡陽、岳陽、常德、益陽、婁底10個城市,該板塊從其他板塊接受并傳輸數字經濟要素資源,屬于“經紀人板塊”。
3.2 政策建議
首先,促進各城市之間的協調與互動發展。著力解決數字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合作和聯動,保持足夠的網絡密度。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要充分發揮其他試點地區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成功經驗,把重點放在新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等方面,建立起數字經濟發展高地,從而實現區域均衡。
其次,注重關聯網絡溢出效應,提高網絡關聯密度。長江中游城市群數字經濟空間關聯網絡雖存在溢出效應,但仍處于較低層次水平,其產業間的關聯度不高。發展數字經濟,需要發揮優勢、補短板、釋放潛力,根據網絡特定區域特點,推動創新發展,充分利用雙向溢出板塊與凈受益板塊在網絡中的核心優勢,加強“邊緣”城市和“中心”城市對接。
最后,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律是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高回報性,可依據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健全數字經濟法律法規,完善數字產業鏈條。加大技術創新力度,促進要素資源合理流動,解決“數據孤島”問題,出臺科學的扶持政策,創新數字經濟保障機制[8],加強資金、人才、平臺等要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