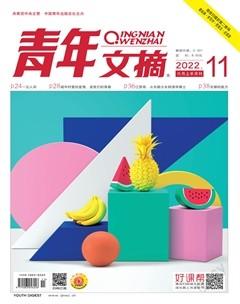“老人”李棉
王霽平

一
在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平日幾乎毫無來往,甚至被全班男生都孤立的同班同學,且還要與其相處十日,張康一想到這一點,就覺得渾身尷尬。
他做夢都沒想到,暑假時會在三維建模興趣班上遇到李棉。人如其名,李棉長得又高又胖,性格也如棉花般綿軟。從小學四年級到高一,他們好巧不巧地做了近7年同班同學。張康大部分時間是班里的高人氣班長,但即使如此,他和李棉的關系依然僅能用“不熟”來形容,可見李棉是有多不合群了吧!
印象中,眼鏡片厚厚的李棉從沒跟班里的男生打過游戲,更不會踢球。沒人知道他喜歡什么,只知道他大概率不喜歡同齡男生喜歡的一切,以至于現在班里男生們私下都形容他“活得像個老人一樣”。不過,他也有優勢——力氣大,對女生們請求出力的工作從不拒絕,對學校里的流浪貓狗也非常溫柔。
但現在,誰能解釋解釋,“老人”李棉為什么會出現在如此時髦的建模課上?看著教室里正在東張西望尋找合適座位的李棉,張康還是不受控地伸出了召喚之手——這大概就是身為班長的自覺吧!
二
“我媽媽的同事給了她報建模班的7折券,我也覺得暑假挺長的,學學建模沒什么不好,就來了。”坐在食堂里,李棉一邊啃著雞腿,一邊斷斷續續地說,“你呢?”這個體現不出任何傾向性的理由真的“很李棉”。
在陌生的地方,熟悉的人總是下意識地抱團。上課都坐在一起了,午餐自然沒有理由不一起吃。
“我大學打算學游戲設計專業,所以想提前感受一下。”張康的語氣中透著得意。不同于對方孩童打發時間般的隨意,他參加興趣班可是出于明確而又長遠的目的,這讓他陡然覺得自己更像個大人。
“哦,那你報這個課正合適。”李棉點點頭,語氣中不夾雜任何情感。可就是這樣平靜的態度,讓張康莫名惱怒,一種羞恥感也涌上心頭。這太奇怪了。
百無聊賴地坐在回家的地鐵上,張康兩眼放空地看著對面的乘客。一個小男孩正用忽高忽低的語調,夸張地讀著耳熟能詳的成語故事,努力吸引父親的注意。幾次勸說男孩保持安靜失敗后,坐在男孩身邊的中年男子先是夸了句“你讀得真好”,隨后從包里掏出一塊水果糖塞到了男孩嘴里。男孩的臉上肉眼可見地掛上了滿足和喜悅,繼而邊吃糖邊安靜地看起故事書來。
就是這樣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生活場景,讓張康冷汗直流。他突然發現,自己在李棉面前就像這個一開始沒討到大人的夸獎和糖果的孩子一樣幼稚。
不過,換個思路考慮,自己學什么專業其實和李棉沒有任何關系,他也確實沒有必要表現出某種態度。另外,把一次簡單的對話都能想成一場暗地里的比較,張康不禁為自己感到臉紅。而聯想到幾年來,在班里既沒有好朋友,也沒獲得過什么關注的李棉,卻也能和所有人和平相處,并保持著不差的成績,張康不免對他好奇起來。
三
一旦認定某個人與眾不同,張康就想接近對方,弄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接下來的相處也沒有讓他失望,李棉每天都有讓張康驚訝的地方。
就拿建模來說,熟悉建模軟件的操作方法后,模仿制作老師的成品很容易,自由創作卻很難。和班里大部分同學一樣,一整節課都快過去了,張康依然對著空白的操作界面發呆,手一握鼠標就不受控地緊張。
沮喪之余,張康瞥了瞥李棉,對方的電腦屏幕竟已從凌亂的線條變成了一只跳動的足球。一節課下來,李棉成了班里極少數完成作品的人。不同于其他完成者在課間前后左右地大聲炫耀,李棉默默關上電腦屏幕,和往常一樣到樓道里散步去了。
還挺低調。雖然不想承認,但張康對李棉又多了幾分佩服。
第二天午休時,張康硬著頭皮向李棉取經。他昨天回家悄悄試了下,足球看似簡單,但它畢竟是個立體圖形,若沒有足夠的空間想象能力還真做不好。
“我覺得你可以在學習建模的同時,也練練素描。”說著,李棉從大背包里掏出一個本子打開,里面有對簡單模型的模仿,也有對校園場景的重現。
“你還學過畫畫?”張康驚訝了,語氣中卻帶著不屑。他完全想象不到李棉那如同香腸般粗壯的手指是如何夾住細長的鉛筆在紙上作畫的。
“也不算學過,我就是喜歡畫著玩,閑著沒事時就會看看網上的視頻教程,多練練就能提高很多。”李棉似乎沒有聽出張康話中的任何不妥,很認真地解釋著,“我的意思是,素描基本上畫的是現實中存在的東西,可以提高空間想象能力。”
“所以,你平常不和我們玩,就是因為畫畫?”張康抓住機會,刨根問底。他自以為這個問題很刁鉆,一定會讓對方把注意力放在“不和我們玩”上,并且會為此難堪,瘋狂而慌亂地解釋并不是不想和大家玩。
“我除了畫畫還喜歡看繪本,拍攝學校里的小動物,做觀察小視頻。”李棉推了下眼鏡,語氣依然平緩,“我性格比較內向,不喜歡熱鬧,不喜歡打游戲,也不喜歡踢球。不過,為了避免再胖下去,每天早上我都會到學校操場上跑三圈。”
這個回應太意外了。它不僅完美地回答了問題,還讓張康明白:李棉有自己想干的事情,這些事在他眼中比踢球和打游戲更值得花費精力和時間;他不在乎,甚至都沒意識到,自己早已被男生們孤立;他是一個有著自己獨特小世界的人,要比同齡的男生成熟自信得多。
看著對方真誠的眼神,張康忽然有了種不敢再和他繼續相處下去的感覺。他越發覺得,自己就是讓高中班里的男生不喜歡李棉的罪魁禍首。
四
張康是四年級時轉入李棉所在的小學的。一進班,他就對這個身材遠超一般同齡人的“大塊頭”感到恐慌。不過,善于交際的他很快融入了新班級。班里男生們告知他,李棉不過是只性格沉悶的紙老虎,外號“木頭”,大家和他的相處模式是:保持沉默,互不打擾。
入班隨俗,為了不給自己惹麻煩,也為了交到更多新朋友,他自然遵守這種模式,也默認了李棉的人設。大部分人往往還是習慣以貌取人,經過三年初中生活的沉淀,“木頭”又被叫成了“呆子”。而到了高中,不知道是急于在男生中樹立威信,還是想討好新同學,又或是玩得太忘乎所以,男生們第一次踢球時,一聽見有人問“李棉怎么沒來”,張康就自然而然地脫口而出:“不用管他。他這個人可沒意思了,從不參加集體活動。我們小學管他叫‘木頭,初中叫他‘呆子。所以,你們懂的。”僅這一次,所有男生就都懂,并記住了。
從“木頭”到“呆子”,又變成現在的“老人”,總之長久以來,沒人去真正了解過李棉,大家要么直接采用別人口中對他的負面描述,要么只根據他簡單的行為進行最膚淺的推測,一次次地與了解真實的彼此相互錯過。
踩壓別人,又自欺欺人。就算李棉心智強大到從未受到干擾,張康自己也在扮演著傷人的角色。“我怎么會干出這種無聊的事啊?”張康后悔地小聲叨念著,一激動,拿起手機就給李棉發了條微信:“李棉,一直以來真的太對不起了。”然而,這讓他更后悔了——太無厘頭了,可消息已經來不及撤回。
果然,李棉回了個問號。太丟人了!就在張康冥思苦想如何解釋自己的冒失時,李棉又發來了一條消息,里面只有一個笑臉和一個擁抱。然而就是這兩個最簡單的小表情,讓張康一愣,心里豁然開朗起來。他相信,明天自己一定會勇敢起來,以全新的面貌對待寬容而又早慧的李棉。
(摘自《中學生》(青春校園)2022年第4期,豆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