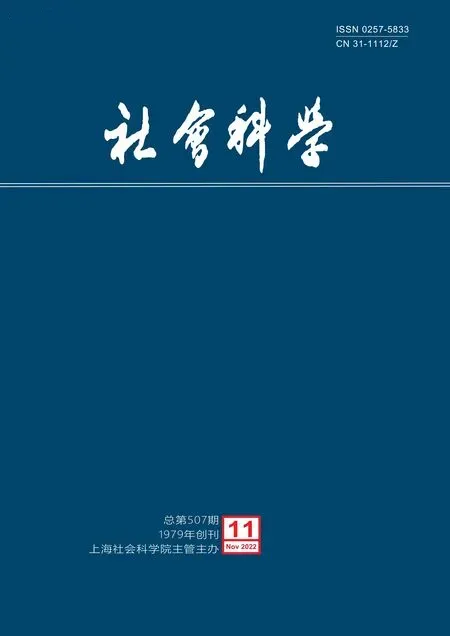數字金融提升我國資本要素配置效率研究*
張宗新 張 帥
引 言
長期以來,我國資本投入型經濟增長模式引致的要素錯配問題,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如何實現投資驅動型向效率驅動型經濟模式轉變,優化資本配置效率,切實解決資本錯配難題,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義。 2022年3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文件指出,要加快我國統一資本市場建設步伐,改善資本要素錯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因此,關于如何優化資本要素配置,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重大現實問題。
資本要素扭曲是指要素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受到信息不對稱、不完全契約、所有制歧視、行政干預等影響,造成要素無法在市場中自由流轉,資本配置效率受到抑制,對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以及均衡性帶來嚴重挑戰。①李青原、章尹賽楠:《金融開放與資源配置效率——來自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證據》,《中國工業經濟》2021年第5期;Bartelsman E., Haltiwanger J.and Scarpetta S.,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Allocation and Sele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3, No.1, 2013, pp.305-334.在微觀層面,Hsieh等采用工業企業數據分析發現我國市場扭曲造成30%-50%的全要素生產率損失。②Hsieh C., Klenow P.,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4, No.4,2009, pp.1403-1448.羅德明等進一步將生產率動態納入到企業決策中,認為偏向國企的政策扭曲導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降低9%。③羅德明、李曄、史晉川:《要素市場扭曲、資源錯置與生產率》,《經濟研究》2012年第3期。靳來群從部門間角度出發,認為所有制歧視造成的資本要素錯配使我國TFP下降50%,而制造業內部各行業間的要素價格扭曲造成15%的經濟產出缺口。①靳來群:《所有制歧視所致金融資源錯配程度分析》,《經濟學動態》2015年第6期。Brandt等從時間、空間、部門三維度對我國宏觀層面資源配置效率進行分析,發現1985—2007年間雖然我國要素流動性顯著增加,但公有和非公有部門的資本配置效率在不斷下降。②Brandt L., Tombe T.and Zhu X.,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cross Time, Space and Sectors in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Vol.16, No.1, 2013, pp.39-58.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國整體資源錯配問題不但沒有緩解反而逐漸惡化,截止到2018年要素錯配造成我國TFP損失10.23%,其中資本扭曲造成的損失最為嚴重。③陳翼然、李貽東、靳來群、張瑞:《我國要素配置優化的著力點在哪?——基于多維度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比較分析》,《管理評論》2022年第2期。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系統性風險因素不斷積累,宏觀經濟不確定性逐漸提高,造成我國信貸資金配置扭曲,限制經濟效率的進一步提升。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學術界從定量角度針對如何實現資本帕累托改進問題進行廣泛討論。De Melo通過構造一般均衡模型測度資本錯配與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④De Mole J., “Distortions in the Factor Market: Some General Equilibrium Estim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s, Vol.59, No.4, 1977, pp.398-405.而后,大多學者針對資本要素錯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場的不完善對經濟影響方面。⑤Galor O., Zeri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60, No.1, 1993, pp.35-52.在研究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優化資本要素配置對提高經濟效率,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Levine認為要不斷完善金融體系建設,克服信息不對稱、不完全契約等問題實現資本配置帕累托改進,從而刺激經濟增長。⑥Levine 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5, No.2,1997, pp.688-726.此后,關于如何完善金融市場,推動金融發展,改善資本要素錯配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問題。Wurgler認為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以股票市值和信貸規模占GDP比重的方式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發現金融在不斷發展過程中會提高資本配置效率。⑦Wurgler J.,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58, 2000, pp.187-214.然而,韓立巖等著重考察股市流動性、銀行信貸規模與資本配置效率的關系,認為二者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⑧韓立巖、蔡紅艷:《我國資本配置效率及其與金融市場關系評價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第1期。陳國進等突破傳統線性約束條件,認為兩者表現為“倒U型關系”,在金融發展初期,資本的迅速積累會加劇資本扭曲程度,而當金融發展到一定水平時,資本錯配會逐步得到緩解。⑨陳國進、陳睿、楊翱、趙向琴:《金融發展與資本錯配:來自中國省級層面與行業層面的經驗分析》,《當代財經》2019年第6期。關于金融發展與資本錯配兩者關系研究,學術界莫衷一是,仍未得出一致性定論。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我國金融產業逐漸加強了與信息技術的有機融合,催生出新型金融模式——數字金融。數字金融的發展與演進,拓寬傳統金融市場業務邊界,提高金融體系資金流動速度,緩解金融市場摩擦。目前學術界有關數字金融如何改進資本要素錯配影響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尤其是關于數字金融與資本錯配相關機制的探討不夠深入,并且僅考慮了二者間的線性關系。⑩田杰、譚秋云、靳景玉:《數字金融能否改善資源錯配?》,《財經論叢》2021年第4期。針對我國資本要素錯配問題嚴重的事實,深入探討數字金融發展對資本要素錯配的扭正機制與實現路徑,以數字金融發展為支點實現資本配置帕累托改進仍是值得探究的關鍵問題。為此,本文基于資本要素錯配糾偏的研究視角探究:數字金融能否改善中國資本要素錯配?數字金融又是如何提高資本配置效率?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是否存在非線性特征?
本文的研究創新有:(1)將數字金融納入到資本要素錯配分析模型,利用省級面板數據對數字金融改善資本要素錯配,實現資源帕累托配置進行實證檢驗。(2)進一步探究數字金融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內在影響機制,打開數字金融影響資本錯配的作用機制“黑箱”。(3)拓展已有文獻對數字金融與資本要素錯配的線性約束關系,采用門檻效應模型分析不同發展水平的數字金融對資本要素錯配的帕累托改進效果,從而更深入地識別二者之間的關系,為政府部門科學制定數字金融政策,實現資本要素帕累托最優配置提供研究依據。
一、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伴隨金融改革深化與金融體系發展,我國金融市場結構不斷優化,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快速發展,金融相關率、資產多樣化水平也不斷提高,企業部門對銀行信貸融資依賴性有所下降。與海外成熟市場相比,當前我國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體系為主導,企業部門直接融資占社融總額比重仍不高,金融體系對創新驅動型經濟體制的支持力度仍不夠,不能滿足我國在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要求。根據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完善的金融體系、合理的市場結構可以提高社會資本利用效率、提高金融風險管理能力、促進金融機構競爭、加強金融市場信息生產,其核心要義是能夠有效緩解金融摩擦,將資本引導至最具生產效率的經濟部門,充分發揮資本價值最大化效應。①Rajan R., Zingales L.,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8, No.3, 1998, pp.559-586.
從資本供給側角度來看,一方面,數字金融能夠改善金融市場結構,提升市場投融資效率。數字金融可以優化傳統信貸融資途徑,減少資本要素在部門間流動時產生的摩擦阻力,以信息生產減少金融摩擦,緩解因資本流動受阻而引起資本擁擠或稀缺的現象,改善資本要素錯配。此外,數字金融可以通過發揮金融風險管理能力,提高金融體系彈性,滿足多元化融資需求,為技術性創新型企業提供必要的資本支持,提高技術研發效率,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進而優化資本要素配置促進經濟增長。②戴偉、張雪芳:《金融發展、金融市場化與實體經濟資本配置效率》,《審計與經濟研究》2017年第1期。另一方面,數字金融是推動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動力。在我國金融市場體系中,國有商業銀行處于相對壟斷的地位,數字金融可以降低銀行業準入門檻,強化金融機構之間、金融中介與互聯網公司之間的競爭,通過發揮鯰魚效應提高信貸利用率和資本配置效率,③李宗顯、楊千帆:《數字經濟如何影響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現代經濟探討》2021第7期。實現以效率為先的信貸資金配置方式。
從資本需求側角度來看,一方面,數字金融借助互聯網、分布式技術優勢有利于打破地域約束,將服務延伸至傳統金融所排斥的地區,在拓寬金融服務覆蓋面的過程中滿足尾部地區市場需求,使得各區域根據不同的資本要素需求進行高效連結和雙向匹配,從廣度和深度上加速跨區域資本的整合效力。另一方面,數字金融能夠為個體和企業及時、精準的提供信貸資金信息,資金需求者可通過智能支付、智能網點、智能投顧等數字技術體驗個性化金融產品和全天候金融服務,從而促進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④Hopenhayn H., “Firms, Mis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6, No.1, 2014,pp.736-770.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
假設1:數字金融能夠扭正資本要素錯配,顯著提高資本配置效率。
以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為導向,實現資源配置優化和資本要素效率提升,是我國實施科技驅動國家戰略的關鍵步驟。而數字金融作為新型金融服務模式,具有提高金融服務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實現金融普惠共享與精準服務等功能,能夠有效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通常而言,創新技術項目往往具有風險高、投資周期長、資本投入高等特征,這與傳統金融機構交易成本高、中小企業信貸歧視等形成沖突,而數字金融能夠有效利用信息技術緩解資金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提高資本市場價格信號功能和風險分散功能,有效識別可以實現技術創新的科創項目,通過事前采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科學高效篩選項目、事中動態監測項目進程、事后動態監督評價,從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支持企業創新活動,使資本以合理的成本流向創新型企業,緩解傳統信貸市場對科技創新企業和技術進步的資金供給約束,進而實現資本要素與技術創新的高效對接。
數字金融通過促進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重構市場結構和產業體系,進而優化資本要素配置。⑤Bruhn M., Love I., “The Real Impact of Improved Access to Finance: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finance, Vol.69, No.3,2014, pp.1347-1376.一方面,數字金融能夠有效緩解不完美市場所帶來的金融摩擦,解決先導產業與金融資本有效融合的難題,促進資本與實體經濟良性循環,引導資本向未來競爭力高的產業部門集聚,實現社會存量資本結構優化,從而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數字金融可以將信息技術應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推動企業生產經營的要素重配,提升企業部門的產業效率,改善資本錯配問題。基于此,本文考慮到數字金融能夠有效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進一步提出研究假設2。
假設2:數字金融能夠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改善資本要素錯配,實現資本配置的帕累托改進。
數字金融可以有效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促進有效生產金融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改善資本要素錯配。但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條件、要素稟賦、制度環境等存在差異,各地區數字金融與資本要素錯配關系會受到數字經濟發展非均衡的影響。在數字金融較為發達地區,配套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市場化程度也相對較高,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發展相對較快,能夠建立起高效的資本形成和轉化機制,促進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自由流動。在數字金融發展滯后地區,信息技術基礎設施、風險防控機制等建設尚有待進一步完善,數字金融不能充分發揮普惠性和便捷性優勢,對優化資本要素配置仍存在較大進步空間。因此,本文考慮到數字金融與資本要素錯配之間并非是簡單的線性關系,進而提出研究假設3。
假設3: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改善效果存在門檻特征,且隨著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其改善效果會逐漸趨強。
二、研究設計
(一)指標構建
1.被解釋變量
資本錯配指數(dist)。本文借鑒陳永偉、胡偉民的研究,①陳永偉、胡偉民:《價格扭曲、要素錯配和效率損失:理論和應用》,《經濟學(季刊)》2011年第4期。假定各地區生產函數滿足規模報酬不變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同時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和勞動要素,在滿足利潤最大化條件下,采用拉格朗日乘數法便得到要素價格扭曲的均衡解,如下所示:

式中,i表示我國各省份以及直轄市;θKi、θLi分別表示各地區資本以及勞動要素扭曲系數,Ki、Li分別表示各地區的資本存量以及勞動力數量;si表示競爭均衡時,地區i產值占整個經濟體GDP的比重,即si=Yi/Y;αi、βi分別表示地區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且滿足αi+βi=1 的約束條件;α=∑siβi、β=∑siβi分別表示按產出加權衡量的資本、勞動平均貢獻度。Ki/∑Ki(Li/∑Li)表示地區資本(勞動)實際使用比例,siαi/α(siβi/β)表示在有效配置情況下資本(勞動)理論使用比例,因此當二者比值大于1,說明資本(勞動)配置過度,當比值小于1時,說明資本(勞動)配置不足。由于式(1)和式(2)的資本和勞動扭曲程度測算是以地區平均水平作為參考,忽視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不可完全替代性,故而本文參考許捷、柏培文的處理方式,②許捷、柏培文:《中國資本回報率嬗變之謎》,《中國工業經濟》2017年第7期。以資本相對勞動配置扭曲系數來表示資本的錯配程度,如式(3)所示:

此外,考慮到存在資本錯配過度以及資本錯配不足的情況,本文進一步將資本錯配指數改寫為:

通過上述調整重新構建資本錯配指標θ,當θ>0時,說明資本配置過度;當θ<0時,表示資本配置不足。另外,為統一后文計量回歸方向,本文對該指數進行絕對值處理,③季書涵、朱英明、張鑫:《產業集聚對資源錯配的改善效果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16年第6期。數值越接近于零,表明資本配置效率越高,數值越大則說明資本錯配程度越嚴重。
根據上述各式可知,若想得到資本錯配指數θ首先需要計算資本產出彈性αi,則勞動產出彈性可表示為βi=1-αi,本文運用索洛余值法進行測算,生產函數如式(5)所示:

等式兩邊同時取對數并加入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則上式可轉變為:

上式中Yit表示各地區GDP水平;Lit表示勞動力投入,用各地區三次產業從業人數表示;Kit表示資本投入量,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主要參考張軍等測算思路,①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經濟研究》2004年第10期。計算方法如下:

式中,K表示資本存量;I表示新增投資額;P為投資價格指數;δ為折舊率,本文取9.6%。
本文根據上述測算方法計算2011—2019年我國各地區資本錯配指數,并且根據沿海和內陸地區的劃分標準繪制要素錯配指數的時間序列趨勢圖,②沿海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內陸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由于數據缺失嚴重,暫不包括西藏以及中國港澳臺地區。如圖1所示。基于地區平均水平的資本和勞動扭曲指數趨勢圖如(a)、(b)所示,資本相對勞動錯配指數趨勢圖則在(c)中給出。由圖1可得,沿海地區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扭曲得到緩解,內陸地區資本要素扭曲程度有所增加,但勞動要素配置效率有所提升。進一步分析資本相對勞動錯配情況,沿海地區資本配置效率在不斷提高,而內陸地區資本錯配程度有所增加。

圖1 分地區要素錯配情況
2.核心解釋變量
數字金融指數(df)。本文選用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衡量我國各地區數字金融發展水平,③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濤、張勛、程志云:《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經濟學(季刊)》2020年第4期。表1列出我國數字金融指數變化情況。近十年間,我國數字金融呈加快的發展態勢,整體來看省級數字金融指數均值已由2011年的40.80增長到2019年的324.73。但是各地區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差距較大,依然存在非均衡性特征。沿海地區的數字金融發展水平最高,尤其以上海、北京、浙江和江蘇為代表,內陸地區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稍顯不足。我國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存在非均衡性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沿海地區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先進技術、高素質人才、充足資本等要素稟賦,地區金融產業數字化轉型更為成功,而對于內陸地區,雖然數字技術能夠有效緩解時間、空間等發展限制,數字金融發展速度也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但與沿海地區相比仍存在明顯不足,并且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表1 中國各地區數字金融發展水平

(續表)
3.中介變量
技術進步指標(pat)。衡量技術進步主要包括投入法、產出法以及TFP測算法等,①舒元、才國偉:《我國省際技術進步及其空間擴散分析》,《經濟研究》2007年第6期。考慮到中國資本統計數據存在缺失情況,不同的估計方法會導致TFP測算結果大相徑庭,因此本文參考姚耀軍處理方式,采用每萬人專利申請授權數作為技術進步代理變量,②姚耀軍:《金融中介發展與技術進步——來自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證據》,《財貿經濟》2010年第4期。一方面該變量能直觀體現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專利授權標準經過專利局審批、認證,具有統一性和客觀性的特點。
產業結構升級指標(is)。本文借鑒魯釗陽的處理方法,用各地區三次產業增加值占一二次產業增加值和的比重來描述各個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情況。③魯釗陽、李樹:《農村正規與非正規金融發展對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財經研究》2015年第9期。
4.控制變量
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1)經濟發展水平(en),采用各地區占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來表示經濟發展情況;(2)人口變量(popu),用各地區年末人口數表示;(3)固定資產投資(ifa),本文用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額來表示,并利用固定資本投資價格指數以2011年為基年進行平減計算得到,最后進行對數化處理;(4)市場化程度(mar),本文采用王小魯等測算的中國省級市場化指數來表示。④王小魯、樊綱、胡李鵬:《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16—217頁。表2中列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從表2可知,各地區資本要素錯配均值為0.734,標準差為0.663,可以看出我國地區間資本錯配存在差異。數字金融指數均值為2.034,標準差為0.916,我國地區間數字金融發展水平非均衡性較強。此外,經濟發展水平、固定資本投資以及市場化程度標準差較大,說明現階段促進我國地區間經濟社會均衡發展仍存在較大提升空間。
(二)數據說明
考慮到數據的完備性和準確性,本文選取2011—2019年中國30個省份及直轄市(不包括西藏以及中國港澳臺地區)面板數據對數字金融與資本要素錯配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對于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填補。
(三)模型構建
本文構造面板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考察數字金融對資本要素錯配的影響,如下所示:

式(8)中,distit表示地區i的資本要素錯配程度;dfit表示地區i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其回歸系數α1及其顯著性水平反映數字金融對資本要素錯配的作用方向及效果;controlit表示控制變量;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λ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三、實證檢驗與結果解釋
(一)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影響效果的實證檢驗
本文首先考察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的影響效果,結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之后,在回歸模型(1)-(3)中逐步增加控制變量,可以看出數字金融的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說明數字金融可以顯著改善資本要素錯配問題。考慮到可能出現的雙向因果關系會造成估計結果有偏,故而本文將數字金融指數滯后1期,采取同樣的方式在回歸模型(4)-(6)中逐步增加控制變量,可以看到滯后1期的數字金融回歸系數依舊顯著為負,可以認為數字金融確實可以改善資本要素錯配。進一步分析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固定資產投資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當前我國一些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并不高,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普遍存在,政府干預等行為會加劇金融摩擦,抑制金融體系資本配置效率,不利于實現資本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改進。此外,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變量以及市場化程度的回歸系數雖然不顯著,但其數值整體上為負數,因而這從側面反映,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以及市場化程度的提升可以引導資金有序流動,從而提高資本配置效率。

表3 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改善效果的實證檢驗
本文采用變換估計方法、補充變量法、縮尾處理和分樣本回歸四種方式對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其結果如表4所示。首先,更換計量方法。本文采用差分GMM和系統GMM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回歸模型(1)-(2)所示,發現數字金融回歸系數顯著性水平均無明顯改變。其次,補充控制變量。本文在回歸模型中增加城鎮化率以及人力資本變量,①城鎮化率變量用各地區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比重表示。人力資本變量用平均受教育程度表示。回歸結果如模型(3)所示,發現回歸結果仍未發生明顯變化。再次,縮尾處理。為消除數據異常值影響,本文將所有變量進行上下2.5%縮尾處理后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列于模型(4),驗證回歸系數大小及其顯著性水平均無明顯變化。最后,分樣本回歸。本文將我國各省份及直轄市劃分為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兩個分樣本,回歸結果如模型(5)-(6)所示,不同地區的回歸結果仍未發生明顯變化,說明數字金融對資本要素錯配的改善效果是穩健的。據此假設1成立,數字金融能夠改善資本要素錯配。

表4 穩健性檢驗估計結果
(二)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的中介效應檢驗
本文進一步考察數字金融影響資本錯配的內在機制,構建了檢驗中介效應的回歸模型:

式(10)和式(11)中的medit表示中介變量技術進步(pat)以及產業結構升級指數(is),其余變量均與前文所述一致。本文對式(9)-(11)所表示的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若式(9)中的α1顯著為負,說明數字金融可以改善資本要素錯配。繼續探究式(10)中β1和式(11)中γ2的顯著性水平,若同時通過顯著性檢驗,則可以說明數字金融將通過影響此中介變量進而改善資本要素錯配。同時,若式(11)中的γ1依舊顯著,則證明此為部分中介效應;反之,若式(11)中的γ1不顯著,則表明為完全中介效應,即數字金融僅通過作用于該中介變量來影響資本要素扭曲。上述回歸模型在表5中所示。

表5 中介效應的實證檢驗
1.技術進步的中介效應分析
回歸模型(1)-(3)是技術進步的中介效應檢驗。回歸(1)結果表明,數字金融能夠有效改善資本要素錯配,與前文所述相同。在回歸(2)中,數字金融回歸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說明數字金融能夠推動技術進步。回歸(3)顯示,技術進步對資本要素錯配的回歸系數在5%顯著性水平下為負,數字金融回歸系數也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技術進步是數字金融影響資本要素錯配的部分中介機制,其中介效應占總效應比重為22.0%。同時,中介效應的sobel檢驗P值為0.021<0.050,說明中介效應成立,即存在“數字金融→促進技術進步→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的傳導機制,數字金融能夠有效緩解創新型企業所面臨的資金約束困境,促進企業經營發展和技術進步,提高資本使用效率。
2.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分析
回歸模型(4)-(6)是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檢驗。其中回歸(4)結果與前述一致。回歸(5)結果表明,數字金融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系數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且符號為正,說明數字金融能夠有效推動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回歸模型(6)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升級對資本要素錯配的回歸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為負,說明產業結構升級能夠改善資本要素錯配。同時,數字金融回歸系數也通過顯著性檢驗,據此可判斷產業結構升級是數字金融改善資本錯配的部分中介機制,其中介效應占總效應比重為48.8%。另外,在中介效應的sobel檢驗中,P值為0.000<0.050,表明中介效應成立,即存在“數字金融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改善資本要素錯配”的傳導機制。因此,研究假說2得到驗證。
(三)數字金融改善資本錯配的門檻效應檢驗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對資本錯配改善效果存在非線性影響,因此,本文以數字金融指數作為門檻變量構建面板門檻模型,如式(12)所示,式中df為門檻變量,η為待檢驗門檻值,I(?)為示性函數,若括號內為真,則I為1,否則為0,其余變量則與前文提及的保持一致。

首先,本文參考Hansen“門檻回歸”模型檢驗思想,①Hansen B.,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93, No.2, 1999, pp.345-638.采用Bootstrap抽樣模擬1000次得到F統計量的近似分布以及相應概率P值和置信區間,計算得到的F統計量和P值列于表6。根據表6可以發現,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效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三重門檻未通過。因此,本文將基于雙重門檻模型分析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的影響效果。

表6 以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為變量的門檻類型檢驗表
其次,在確定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存在雙重門檻效應之后,門檻檢驗搜索出來的第一、第二門檻值分別為2.402和2.729,而后進行門檻回歸,其回歸結果列于表7。基于回歸結果可以發現,不同區間數字金融回歸系數均在1%置信水平上為負,在金融數字化發展初期,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改善效果最弱,而隨著數字金融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其對資本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效果也在逐漸增加,當數字金融發展到較高水平,即當數字金融指數跨越第二門檻值(2.729)時,數字金融對資本要素錯配的改善效果最大。據此,本文研究假說3得到驗證。

表7 面板門檻實證檢驗
四、簡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2011—2019年中國30個省份及直轄市為研究樣本,將數字金融納入到資本要素錯配模型中,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分析數字金融對資本要素錯配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機制分析、門檻效應分析等。研究發現:(1)數字金融可以有效緩解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企業信貸融資約束等問題,促進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先導產業的發展,加強資本要素流動,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2)數字金融能夠扭正資本要素錯配,并且通過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實現資本要素帕累托改進;(3)以數字金融作為門檻變量,發現資本配置效率會隨著數字金融的發展而逐漸提高,總體呈現出動態趨勢性上升態勢。
根據本文研究,在此提出數字金融發展與資本配置效率提升的相關政策建議:(1)推動數字金融深化與廣化發展,充分發揮數字金融對資本要素錯配的改進效能,為企業創新與技術進步提供數字金融支持,優化資本要素配置效率;(2)因地制宜實施有差別的數字金融發展策略,優先促進落后地區數字金融發展,提高數字金融改善資本錯配的總合力,同時,要注重較高發展水平地區的數字金融發展情況,著力促進數字金融跨越第二門檻值,最大化發揮數字金融對資本錯配的改善效果;(3)進一步推動數字貨幣革新發展,不斷為新興產業和長尾客戶群體融通資金,通過搭建數字貨幣生態體系支持數字金融發展;(4)規范數字金融發展,強化配套金融監管、風險管控機制建設,提高數字金融風控技術的有效性、數據質量的完整性以及數據隱私的安全性,堅持安全可控與創新發展并舉,更好地為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