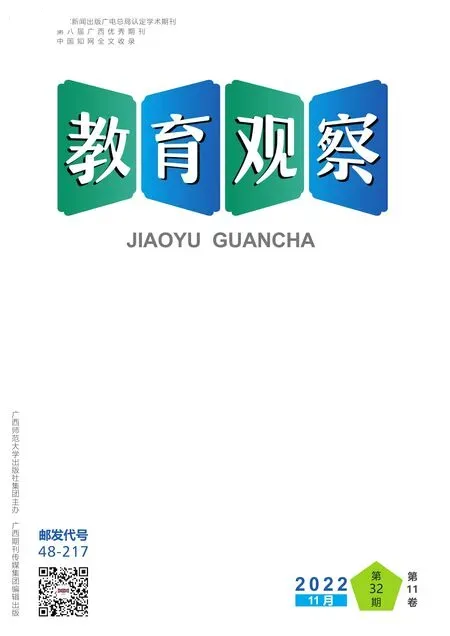領悟社會支持與大學生親社會行為的關系
——共情的中介作用和自尊的調節作用
郭 焱
(廣西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工處,廣西南寧,530008)
一、引言
親社會行為是指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所表現出的正能量的行為,是衡量個體心理健康狀況與品德發展的重要指標。[1]相關研究表明,親社會行為表現較多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生命意義感和幸福感,較少地產生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體驗。[2-3]大學生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其親社會行為狀況不僅影響其自身的發展,而且關乎社會的發展。因此,探討大學生親社會行為的影響因素至關重要。
生態系統理論為開展大學生親社會行為研究提供了線索。此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發展是個體感知到的環境因素與個體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4]其中,領悟社會支持是影響個體行為發展的重要環境變量。領悟社會支持是指個體感到被重要他人關心、尊重、支持和理解的滿意程度。[5]大學生體驗到的支持越多,越有可能愿意幫助他人。在與他人交往中,個體感到的社會支持越多,對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歸屬感也越強。因為他們會覺得人與人之間是可信賴的,這個世界是溫暖和美好的,所以他們會溫柔以待他人,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相關研究也證實,人際信任能夠顯著影響個體的親社會行為,高人際信任的個體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6]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認為,身邊重要他人(家人、朋友、同學、教師、親戚)的行為和態度會對個體行為產生強化、認同、模仿和榜樣作用[7],大學生可能會受重要他人的親社會行為影響而習得或形成親社會行為。實證研究也表明,社會關系質量可以顯著正向影響親社會價值觀和利他行為。[8]對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領悟社會支持能夠促進大學生習得或形成親社會行為。
社會認知理論認為環境、個體認知因素和行為相互影響,即環境因素(如領悟社會支持)會對個體認知因素(如共情)產生影響,個體認知因素(如共情)又可以對個體行為(親社會行為)產生影響。由此可以得出環境因素→個體認知因素→個體行為研究路徑,領悟社會支持這一環境因素可能會通過共情的中介作用對大學生的親社會行為產生影響。已有研究也證實,共情在家庭環境(環境因素)與助人行為(個體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9]共情是指個體可以設身處地感受、識別和理解他人的情感,并產生感同身受的情感體驗。[10]一方面,共情與親社會行為關系密切。共情是個體親社會行為產生、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是諸如幫助他人、志愿行動、分享、合作、關心與安慰等親社會行為的動機基礎,是個體產生親社會行為的推動器。共情—利他理論認為,當個體對需要幫助的人產生共情時,會激發個體的利他動機,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11]另一方面,共情與領悟社會支持關系十分密切,即領悟社會支持可以正向預測共情。一個人體驗到的領悟社會支持越多,共情能力也更強。[12]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共情在領悟社會支持與大學生親社會行為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自尊是個體自我概念的核心組成部分,指個體對自我的態度,表征了個體知覺到的自我價值。[5]斯托布的親社會行為共情理論認為,個體共情能力受到自我概念的影響。[1]在與他人交往時,個體的自我概念越好,個體越能設身處地地感受他人的情緒。自尊是促進個體產生共情的保護因素。“保護因子—保護因子”模型的促進假說認為,不同的保護因子之間通過交互作用促進個體心理發展。[13]也就是說,保護因子(自尊)可能會強化或促進另一種保護因子(領悟社會支持)對結果變量(共情)的積極影響,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根據相關理論,本研究提出假設3:自尊可能在領悟社會支持與共情之間起調節作用。
綜上所述,在生態系統理論、社會認知理論視角下,整合共情—利他理論及“保護因子—保護因子”理論的基礎上,考察領悟社會支持對大學生親社會行為的影響,提出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并將從以下方面進行驗證:領悟社會支持顯著正向預測大學生親社會行為;共情在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自尊調節領悟社會支持與共情之間的關系。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樣法,在南寧市四所高職院校抽取721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整理數據時,為提高數據質量,研究者刪除了用時過短、胡亂作答或故意規律作答的問卷30份,最終獲得有效問卷691份,有效問卷率為95.84%。其中,男生251人,女生440人;生源類型為高中起點的528人,中職對口的163人;家庭所在地在城鎮的123人,農村的568人;漢族430人,少數民族261人。
(二)研究工具
1.領悟社會支持
本研究采用姜乾金編制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評估大學生領悟社會支持水平,并根據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將“領導”改為“教師”,“同事”改為“同學”。該量表共有12個題目,包含朋友支持、家人支持以及其他支持3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分別有4個題目,采用7點計分法(1=“極不同意”,7=“極同意”),得分越高領悟社會支持越高。[5]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40。
2.親社會行為
本研究采用Carlo編制、寇彧等人修訂的親社會行為傾向量表,主要測量大學生自我評定的六種親社會行為傾向。該量表共26個題目,測量匿名的、公開的、依從的、利他的、情緒的及緊急的6個維度的親社會傾向,采用5點計分法(1=“非常不像我”,5=“非常像我”),得分越高親社會行為傾向越強烈。[14]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59。
3.共情
本研究采用Davis編制張鳳鳳等人修訂的人際反應指針量表,主要從認知和情感角度測量大學生自我報告的共情情況。該量表共22個題目,分別是測量觀點采擇(5個題目)、個人痛苦(5個題目)、想象力(6個題目)、共情性關心(6個題目),采用5點計分(0=“不恰當”,4=“非常恰當”),得分越高表示個體共情能力越強。[15]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44。
4.自尊
本研究采用Rosenberg編制的自尊量表測量大學生自我評定的自我價值和自我接納的總體感覺。該量表共10個題目,采用4點計分法(1=“很不符合”,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自尊水平越高。[5]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19。
(三)數據處理
本研究的描述性統計采用SPSS 22.0進行分析和處理,有調節的中介效應采用Hayes開發的process宏程序進行分析。
三、結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數據是通過大學生自我報告的形式獲得的,結果可能會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因此,調查時采用匿名方式對大學生進行調查,設置了反向計分題目及同一維度的題目分開編排等方式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控制。在獲得有效數據后,本研究采取Harman單因子檢驗法對領悟社會支持、親社會行為、共情、自尊的所有題目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發現,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共有13個,并且最大公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6.56%,低于40%的判斷標準。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二)領悟社會支持、共情、自尊與親社會行為的相關關系
如表1所示,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呈顯著正相關,說明大學生領悟社會支持越高,其親社會行為傾向越強;共情與領悟社會支持、親社會行為之間呈顯著正相關;自尊與領悟社會支持、共情、親社會行為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表1 描述統計、相關分析結果
(三)共情的中介效應檢驗
在進行數據分析時,本研究對性別、生源類型、家庭所在地三個變量進行控制,采用簡單中介效應(模型4)檢驗共情在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回歸分析表明,領悟社會支持對親社會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且當納入中介變量(共情)和控制變量后,領悟社會支持對親社會行為的直接預測作用依然顯著,如表2所示。領悟社會支持正向預測共情,共情正向預測親社會行為。由表3可知,領悟社會支持對親社會行為的總效應95%CI為[0.37,0.51],不包含0;共情的中介效應95%CI為[0.08,0.16],不包含0,表明共情在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0.12)占總效應(0.44)的27.27%。

表2 共情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

表3 中介效應顯著性檢驗的分析結果
(四)自尊對共情中介效應的調節作用檢驗
本研究對性別、生源類型、家庭所在地三個變量進行控制,采用模型7檢驗自尊的調節效應。結果如表4所示,在自尊加入模型之后,自尊可以正向預測共情,領悟社會支持和自尊的交互項對共情的預測作用也顯著,說明自尊調節了領悟社會支持→共情→親社會行為的前半路徑,即領悟社會支持對共情的影響受到了自尊的調節。

表4 領悟社會支持對親社會行為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
為進一步探討自尊調節效應的實質,本研究進行了簡單斜率分析,分別按自尊的Z分數為1(高自尊組)和-1(低自尊組)分組,分析領悟社會支持對共情的影響,并繪制了調節作用圖,如圖1所示,領悟社會支持對共情的影響受到自尊的調節。自尊水平較低(M-1SD)的個體,領悟社會支持對共情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β=0.19,t=3.85,p<0.001);自尊水平較高(M+1SD)的被試,領悟社會支持對共情的正向預測作用變得更強了(β=0.31,t=6.33,p<0.001),表明相對低自尊的個體,領悟社會支持對高自尊個體的共情影響更大。此外,在自尊的三個水平上,自尊在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關系中的中介效應也呈上升趨勢,即隨著個體自尊水平的提升,共情在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明顯增強,如表5所示。

表5 在自尊的不同水平上共情的中介效應
四、討論
基于以往研究,以及共情—利他理論和“保護因子—保護因子”理論,本研究在生態系統理論、社會認知理論視角下構建了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深入考察了領悟社會支持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揭示領悟社會支持如何影響及在什么條件下影響親社會行為的問題,研究結果對促進大學生親社會行為、提升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具有一定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一)領悟社會支持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領悟社會支持可以預測大學生親社會行為,即大學生領悟社會支持水平越高,其親社會行為就越多,支持了假設1。這與李溫平等人對青少年群體的研究結果一致[16],表明社會支持對親社會行為的重要性,具有跨越年齡的一致性。一方面,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家庭、朋友、教師等重要他人是大學生重要的學習榜樣。大學生會學習和內化重要他人的親社會行為,從而產生更強烈的親社會行為傾向。另一方面,高領悟社會支持的個體,能夠從重要他人身上得到較多的溫暖和愛護,會更有安全感,更能以積極心態看待他人,也更傾向于向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
(二)共情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揭示了共情在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印證了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證實了假設2。這說明領悟社會支持作為重要的環境因素可以影響個體認知因素(共情),促使個體產生更多的助人、利他等親社會行為。一方面,領悟社會支持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大學生的共情水平。這與邊盛楠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17]相較于領悟社會支持水平低的個體,領悟社會支持高的個體人際交往能力更強,更善于體察他人情緒,設身處地地從他人的角度和立場考慮問題,表現出較強的共情能力。另一方面,共情會對大學生親社會行為產生積極影響。這與扈芷晴等人對醫學生的研究結果一致[18],驗證了共情利他假設,共情可以喚起個體的親社會行為動機。個體對陷入困境和需要幫助的人產生的同情、憐憫越多,越有可能產生助人行為。
(三)自尊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結果表明,自尊調節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具體而言,領悟社會支持與共情之間的關系受大學生自尊水平的調節,這一結果支持了假設3。總體而言,隨著自尊水平的提高,領悟社會支持對大學生共情的預測作用呈逐漸增強趨勢,驗證了“保護因子—保護因子”的“錦上添花”模型,自尊會放大或增強領悟社會支持對共情的影響。高自尊者的自我價值感較高,更能對他人進行積極關注,表現出更多的共情,也更容易產生親社會行為。
總體而言,本研究結果將有助理解親社會行為的形成機制,對提升大學生親社會行為具有一定實踐意義。首先,要為大學生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家庭層面,家長要采用引導式的教養方式,給予子女足夠的溫暖和支持。因為父母的愛有助于個體親社會行為的發展。學校層面,學校和教師要與大學生建立良好師生關系,讓大學生感受到重要他人的關心和愛,形成對社會的信任,建立親社會價值取向。其次,可以從大學生的認知因素(共情)進行干預。在日常教育中,教師可以通過共情訓練增加大學生的親社會行為。最后,應對大學生多進行積極的反饋,以幫助他們形成親社會的自我認知。
(四)研究不足與展望
第一,本研究只探討了領悟社會支持這一環境變量的影響,今后研究可以考慮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第二,大學生認知因素(共情)在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占比27.27%),這說明還可能存在其他認知變量或情緒變量在兩者之間起作用,需進一步探討。第三,本研究采用的橫向設計無法得出變量之間因果關系,未來的研究將采取實驗和追蹤研究設計,從發展和動態的視角進行深入考察。
五、結論
第一,領悟社會支持對大學生的親社會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第二,大學生的共情在領悟社會支持與親社會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自尊可以顯著調節領悟社會支持與共情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隨著個體自尊水平的提升,領悟社會支持對共情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