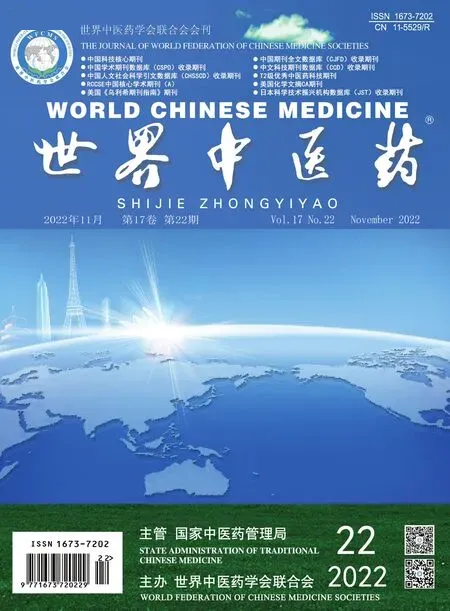276例特發(fā)性膜性腎病中醫(yī)證候分布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劉玉旋 李 平 梁昌昌 王新慧 曾 勤1, 陳 楠1, 余仁歡
(1 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研究生院,北京,100029; 2 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第三附屬醫(yī)院心血管科,北京,100029; 3 河北醫(yī)科大學(xué)第三醫(yī)院腎病科,河北,050051; 4 中國中醫(yī)科學(xué)院西苑醫(yī)院腎病科,北京,100091)
膜性腎病(Membranous Mephropathy,IMN)是一個病理學(xué)診斷名稱,以腎小球基底膜上皮細(xì)胞下大量免疫復(fù)合物沉積伴基底膜增厚為病理特征,臨床表現(xiàn)以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癥、水腫居多[1]。根據(jù)發(fā)病病因可將MN分為2種類型,約80%發(fā)病原因不明的病例稱為特發(fā)性膜性腎病(Idiopap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IMN),而剩余20%由于自身免疫病、藥物、感染及腫瘤等引起則稱為繼發(fā)性膜性腎病(Secondary Membranous Nephropathy,SMN)[2-3]。近年來,IMN的發(fā)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且發(fā)病年齡年輕化[4-6]。IMN發(fā)病機制尚不完全明確,西醫(yī)的治療方案以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tǒng)抑制劑為基礎(chǔ)治療,對高危患者建議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劑、生物制劑等治療,但存在不良反應(yīng)大、藥物撤停困難以及病情反復(fù)等問題。
近20年來中醫(yī)學(xué)對IMN的認(rèn)識不斷深入,運用中醫(yī)藥治療方案在提高IMN臨床緩解率、減少西藥不良反應(yīng)等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但目前中醫(yī)腎病學(xué)界對IMN中醫(yī)證候特點的認(rèn)識尚不完全一致,治療方案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本研究采用流行病學(xué)橫斷面調(diào)查的方法,收集IMN患者的基本信息、疾病資料、中醫(yī)癥狀、舌脈信息,在此基礎(chǔ)上全面分析IMN的中醫(yī)證候分布特點以及影響中醫(yī)證候的相關(guān)因素,以期提高IMN的中醫(yī)病機的認(rèn)識,并為IMN中醫(yī)辨證論治提供依據(jù)。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中國中醫(yī)科學(xué)院西苑醫(yī)院IMN患者185例,河北醫(yī)科大學(xué)第三醫(yī)院IMN患者91例,總計276例。其中男156例,占56.52%,女120例,占43.48%,男女之比1.3∶1。年齡18~83歲,平均年齡(51.07±13.90)歲。平均體質(zhì)量指數(shù)(25.09±3.53)kg/m2。本研究通過中國中醫(yī)科學(xué)院西苑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zhǔn)(倫理審批號:2016XLA127-2)。
1.2 診斷標(biāo)準(zhǔn)
1.2.1 西醫(yī)診斷標(biāo)準(zhǔn) IMN的診斷參考原發(fā)性腎小球疾病分型與治療診斷標(biāo)準(zhǔn)專題座談會紀(jì)要中有關(guān)IMN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1]。IMN的病理分期參照Ehrenreich關(guān)于IMN的病理分期(Pathological Staging,PS)標(biāo)準(zhǔn),分為Ⅰ、Ⅱ、Ⅲ、Ⅳ期[7]。
1.2.2 中醫(yī)辨證分型標(biāo)準(zhǔn) IMN多屬中醫(yī)“尿濁”“水腫”“腰痛”等范疇。中醫(yī)證候分型標(biāo)準(zhǔn)參考2002年國家藥品管理局制定發(fā)布的《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dǎo)原則》中關(guān)于“慢性腎炎的中醫(yī)診斷標(biāo)準(zhǔn)”[8]。本虛證為脾腎氣虛證、脾腎陽虛證、肺腎氣虛證、肝腎陰虛證、氣陰兩虛證;標(biāo)實證為水濕證、濕濁證、濕熱證、血瘀證。將水濕證、濕濁證、濕熱證與血瘀證兼夾者歸為濕瘀互結(jié)證。
1.3 納入標(biāo)準(zhǔn) 1)經(jīng)腎活檢病理診斷為特發(fā)性膜性腎病的患者;2)年齡18~85歲的患者;3)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 Disease,CKD)1~4期的患者;4)神志清楚,對答切題的患者;5)簽署知情同意書的患者。
1.4 排除標(biāo)準(zhǔn) 1)紫癜性腎炎、紅斑狼瘡性腎炎、腫瘤、藥物相關(guān)性腎炎等繼發(fā)性膜性腎病的患者;2)合并IgA腎病、糖尿病腎病等其他類型腎小球疾病的患者;3)合并有心、肝、腦、和造血系統(tǒng)等嚴(yán)重疾病的患者;4)已接受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及腎移植的患者;5)語言理解或表達(dá)障礙的患者。
1.5 觀察指標(biāo) 1)一般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年齡、身高、體質(zhì)量等;2)病史資料包括病程、糖皮質(zhì)激素使用情況,伴高血壓、糖尿病情況等;3)實驗室檢查包括24 h尿蛋白定量、血漿總蛋白、血漿白蛋白、血肌酐、血尿素氮、血尿酸等;4)中醫(yī)癥狀是基于望、聞、問、切四診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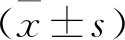
2 結(jié)果
2.1 臨床特點 276例患者中以男性居多,青、中年發(fā)病居多,病理分期以Ⅰ期、Ⅱ期為主,CKD分期以1、2期為主,體質(zhì)量指數(shù)、血漿白蛋白、尿蛋白定量分層情況及具體臨床特點見表1。276例患者的實驗室指標(biāo)見表2。

表1 276例患者的臨床特點及分布情況

表2 276例患者的實驗室檢查指標(biāo)
2.2 中醫(yī)癥狀頻數(shù) 中醫(yī)癥狀出現(xiàn)頻次最多的是神疲乏力(89.13%),其次分別是腰酸痛(85.14%)、浮腫(63.04%)、肢體困重(54.71%)、睡眠差(52.54%)、食少納呆(48.55%)、夜尿多(44.20%)、便溏(38.77%)、少氣懶言(38.77%)、口干(37.68%)。出現(xiàn)頻次前20位癥狀見表3。

表3 中醫(yī)癥狀頻數(shù)[次(%)]
2.3 舌苔 在本研究中,出現(xiàn)頻次最多的是紫暗、瘀斑舌,其次是淡白、胖大、齒痕舌,淡白舌,淡紅舌,紅舌有裂紋。苔質(zhì)分布中,白厚膩苔>薄黃苔>水滑苔>薄白苔>黃厚膩苔,具體舌苔分布情況見表4。

表4 舌苔分布情況
2.4 中醫(yī)證候分布特征 純虛證54例,占19.57%,純實證30例,占10.87%,虛實夾雜證192例,占69.57%。虛證中以脾腎氣虛證(37.04%)、脾腎陽虛證(29.63%)為主,實證中以濕熱證(50.00%)、濕瘀互結(jié)證為主(30.00%)。見表5。

表5 IMN虛證、實證分布情況
在192例虛實夾雜證中,脾腎氣虛證、肺腎氣虛易兼水濕證;脾腎陽虛易兼濕濁證;肝腎陰虛虛、氣陰兩虛易兼血瘀證。見表6。

表6 虛證兼夾實證分布情況[例(%)]
2.5 臨床因素對中醫(yī)證型的影響
2.5.1 不同病程IMN患者中醫(yī)證型分布 病程≥2年肝腎陰虛證比例較<2年明顯偏高(26.39%對比12.07%),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見表7。

表7 病程與中醫(yī)虛證關(guān)系[例(%)]
病程≥2年與<2年實證總體構(gòu)成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見表8。

表8 病程與中醫(yī)實證關(guān)系[例(%)]
2.5.2 體質(zhì)量與中醫(yī)證型的關(guān)系 體質(zhì)量正常和超重間虛證分布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見表9。

表9 體質(zhì)量與中醫(yī)虛證的關(guān)系[例(%)]
超重濕瘀互結(jié)證比例較正常明顯偏高(41.96%對比19.23%),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1)。見表10。

表10 體質(zhì)量與中醫(yī)實證的關(guān)系[例(%)]
2.5.3 血漿白蛋白與中醫(yī)證型關(guān)系 血漿白蛋白≤30 g/L脾腎氣虛證比例較血漿白蛋白>30 g/L明顯偏高(55.15%對比34.55%),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1)。見表11。

表11 血漿白蛋白與中醫(yī)本虛證關(guān)系[例(%)]
血漿白蛋白≤30/L血瘀證比例較血漿白蛋白>30/L明顯偏高(31.40%對比17.82%),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1)。見表12。

表12 血漿白蛋白與中醫(yī)實證關(guān)系[例(%)]
2.5.4 糖皮質(zhì)激素使用情況與中醫(yī)證型分布 使用糖皮質(zhì)激素的肝腎陰虛證和肺腎氣虛證比例較未使用糖皮質(zhì)激素明顯偏高(27.27%、20.00%對比13.09%、7.33%),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P<0.01),其余證型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見表13。

表13 糖皮質(zhì)激素使用情況與中醫(yī)虛證關(guān)系[例(%)]
使用糖皮質(zhì)激素與未使用糖皮質(zhì)激素實證總體構(gòu)成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見表14。

表14 糖皮質(zhì)激素使用情況與中醫(yī)實證關(guān)系[例(%)]
3 討論
3.1 臨床特征 本研究對276例IMN病例分析結(jié)果顯示,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比例1.3∶1,與國內(nèi)外相關(guān)研究一致[9-11]。不同于既往研究IMN多為中老年,本研究病例多見于中青年(86.23%),發(fā)病年齡趨于年輕化[12-14]。本組病例體質(zhì)量指數(shù)(25.10±3.53)kg/m2,超重134例,占48.55%,肥胖與IMN的發(fā)病是否有關(guān)值得深入研究。本調(diào)查中腎病綜合征有124例,占44.93%,與楊柳等[15]報道的60%~80%的患者呈現(xiàn)腎病綜合征的狀態(tài)有一定差異,這可能與患者使用藥物治療、疾病緩解以及證候調(diào)查時間有關(guān),也可能與本組病例主要集中在病理分期以Ⅰ、Ⅱ期,CKD分期以1、2期為主有一定關(guān)系。伴高血壓、血尿、高尿酸等臨床表現(xiàn)與諶貽璞教授[16]的研究報道相近。
3.2 舌苔 舌苔能反映感邪的輕重、病位的深淺、臟腑氣血的盛衰、預(yù)后的好壞,是中醫(yī)診病的重要依據(jù)。淡白舌的形成多歸因陽氣不足,血液運行緩慢,不能上榮舌質(zhì),故舌色淺淡,主虛證或寒證;淡白、胖大舌,有齒痕多因脾虛運化功能減弱,水濕痰飲阻滯而致;二者合計占比45%,反映了IMN以虛為本的特點;紫暗、瘀斑舌多為氣血瘀滯之象,在本研究中,占比43.12%,提示瘀血在IMN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通過舌苔的厚與薄可辨別邪氣的深淺,以推測病情輕重。薄苔為胃氣所生,為正常舌苔,即使在患病之人中出現(xiàn),也屬于病情較輕的階段;厚膩苔乃因胃氣夾濕熱濁邪之氣熏蒸所致,臨床見之,患者多有痰飲或濕濁或飲食積滯在內(nèi);水滑苔多為脾陽虛而痰飲水濕停滯于內(nèi);在本研究中以白厚膩苔最多,其次為薄黃苔,水滑苔,反映出IMN常伴有濕濁、水濕、痰飲、濕熱等邪氣。
3.3 中醫(yī)證候分布特征 IMN在中醫(yī)學(xué)中多屬“尿濁”“水腫”“腰痛”等范疇。其病機多為中醫(yī)學(xué)的“本虛標(biāo)實”,虛證多強調(diào)脾腎虧虛,其中包括了脾腎氣虛和脾腎陽虛,實證則包括水濕、痰濕、濕濁、濕熱、氣滯、血瘀、風(fēng)擾等。現(xiàn)代中醫(yī)關(guān)于IMN中醫(yī)證候分布的研究尚不統(tǒng)一。在相關(guān)研究中,以脾腎陽虛證居首位,次之脾腎氣虛證[10,17]。也有研究認(rèn)為脾腎氣虛證最多,其次為脾腎陽虛證,肺腎氣虛證、肝腎陰虛證、氣陰兩虛證的排名有先有后;實證以血瘀證、濕熱證、濕濁證為主。本研究同以上3個研究既有相似,又有不同[18-20]。本虛證中脾腎氣虛證最多,其次為脾腎陽虛證,實證中以濕熱證、濕瘀互結(jié)證為主。濕瘀互結(jié)證為本研究的一個特色,將水濕證兼血瘀證、濕濁證兼血瘀證、濕熱證兼血瘀證歸為濕瘀互結(jié)證。如上所述,IMN的發(fā)生及進(jìn)展,責(zé)之肺脾腎3臟,若此3臟功能失調(diào),津液代謝失常,濕邪為其產(chǎn)物。誠如《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云:“經(jīng)為血,血不利則為水,名曰血分。”《血證論》亦曰:“瘀血化水,亦發(fā)水腫,是血病而兼水也。”因此水腫可導(dǎo)致血瘀,血瘀亦可導(dǎo)致水腫。余師認(rèn)為瘀血不僅是本病的病因,同時也是本病的病理產(chǎn)物,貫穿疾病始終。在臨床中,濕、熱、水、瘀常相互攀援,交相濟惡,并進(jìn)一步壅塞三焦,阻礙氣化,循環(huán)往復(fù),導(dǎo)致疾病越來越嚴(yán)重。
俞欣等[19]、張小鳳等[21]、張文華[22]的研究均證實脾腎氣虛證與水濕證、濕濁證呈正相關(guān),脾腎陽虛證與水濕證正相關(guān),氣陰兩虛證與血瘀證正相關(guān)。在本研究虛實夾雜的證型中,脾腎氣虛證、肺腎氣虛證常易兼夾水濕證。在《景岳全書·腫脹》明確提出水腫病機與肺、脾、腎三臟功能失常密切相關(guān),若肺失宣降則不能通調(diào)水道,氣不得化而為水;脾氣虧虛,脾土不能制約腎水而反克,水濕內(nèi)停;腎氣虧虛,蒸騰氣化功能減弱,則水無所主而肆意妄行,可見肺脾腎三臟失調(diào)可產(chǎn)生水濕,也最易與水濕之邪合而致病。又脾為后天之本,腎為先天之本,若脾陽不振,溫煦運化功能失調(diào),分清泌濁功能減退,水谷精微不化反成穢濁;若腎陽衰微,氣化蒸騰功能減弱,津液不化反成水濕,水濕與穢濁交結(jié)而成濕濁,故脾腎陽虛證常與濕濁證合而為患。如若患者久病則脾胃虛弱,氣血漸衰,陰液不足則致脈道涸澀,血行澀滯,“無水舟停”而易產(chǎn)生血瘀;又氣為血之帥,氣虛無力推動血液運行,血瘀成之,因此肝腎陰虛證、氣陰兩虛證常易兼夾血瘀證。
3.4 影響中醫(yī)證型分布的因素分析 既往大多研究IMN中醫(yī)證型的臨床特點,關(guān)于臨床因素對證型影響的研究尚少。在一項IMN中醫(yī)證候調(diào)查中,中醫(yī)虛證Ⅰ、Ⅱ期分布無差異,Ⅱ期濕熱證比例較Ⅰ期多;女性肝腎陰虛證比例較男性高,實證分布在性別間無差異;應(yīng)用糖皮質(zhì)激素組與未使用糖皮質(zhì)激素組中醫(yī)虛證總體構(gòu)成有差異,但未詳細(xì)說明具體證型[17]。另一項IMN中醫(yī)證型分布規(guī)律的研究,發(fā)現(xiàn)肝腎陰虛證在5~10年分布較多,氣陰兩虛證在10~15年分布較多[18]。
本研究發(fā)現(xiàn),病變初期以脾腎氣虛、脾腎陽虛證為主,隨著病情的進(jìn)展,陽損及陰,加之久病患者肝氣郁結(jié)、氣郁化火,常耗傷陰液,故病程長的患者肝腎陰虛證比例高。隨著人們飲食結(jié)構(gòu)改變和生活水平提高,肥胖已經(jīng)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研究發(fā)現(xiàn),本組病例中近一半(48.55%)IMN患者超重。誠如《丹溪治法心要》曰:“肥白人多痰濕。”《醫(yī)法律》亦云:“肥人素有痰熱。”超重者多因嗜食肥甘厚膩,損傷脾胃,水谷精微不化反成痰濕,痰濕阻滯血脈運行,濕瘀互結(jié),進(jìn)而影響肺脾腎的功能。低白蛋白血癥為腎病綜合征的典型表現(xiàn),血漿膠體滲透壓下降加之毛細(xì)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清白蛋白從毛細(xì)血管壁濾出,隨著血清白蛋白的下降,患者長期營養(yǎng)不良,在中醫(yī)多表現(xiàn)為氣虛證;同時血清白蛋白降低多易形成血栓,在中醫(yī)表現(xiàn)為血瘀證。長期使用激素者,免疫功能低下,常易誘發(fā)感染、腹瀉等加重疾病甚至引起腎衰竭。中醫(yī)多認(rèn)為激素屬陽性藥物,易助熱生火,耗傷陰津,導(dǎo)致陰傷,故在使用激素的初期證型上表現(xiàn)為肝腎陰虛;同時由于過熱過亢極易耗傷元氣,腎氣虧損,加之肺衛(wèi)虧虛,腠理常開,致使邪氣入內(nèi),則可見惡寒、出汗等癥狀。因此使用糖皮質(zhì)激素組肝腎陰虛證、肺腎氣虛證比例較未使用糖皮質(zhì)激素組明顯偏高。
本項研究通過對IMN的中醫(yī)證候分布特點的分析,并對影響中醫(yī)證候分布的因素進(jìn)行了初步探索,但是本研究僅限于北京與河北的2個醫(yī)院,樣本收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病例來源可能有一定的偏倚,同時由于研究時間有限,樣本量偏少,其研究結(jié)果尚不能代表IMN的整體水平。其次,在本研究中中醫(yī)辨證是參考慢性腎炎的辨證分型及結(jié)合患者臨床特征和專家經(jīng)驗而得,存在一定的主觀偏倚,缺乏統(tǒng)一的中醫(yī)辨證規(guī)范,從而影響IMN的中醫(yī)證候分析的準(zhǔn)確性和客觀性。希望今后嘗試開展大樣本多中心研究,進(jìn)一步深入研究IMN中醫(yī)證候分布規(guī)律,以及影響IMN證候變化規(guī)律的臨床、病理、病程、治療等多種因素,從完善IMN中醫(yī)辨證論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