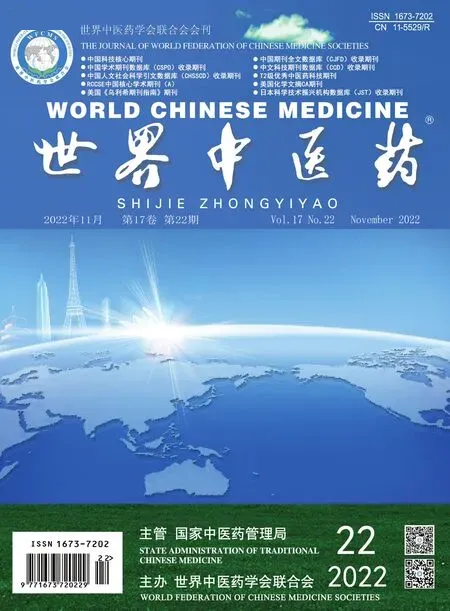基于國家專利的中藥復方治療抑郁癥用藥規律研究
熊霞軍 胡志希 鐘森杰 楊 夢 葉嘉豪
(湖南中醫藥大學,長沙,410208)
抑郁癥也被稱為抑郁障礙,是以情感性精神障礙為主的嚴重精神疾病[1]。主要表現為情緒低落、思維遲緩、言語動作減少、睡眠障礙,重者有自殺傾向,嚴重危害身心健康,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2]。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顯示抑郁癥總患病率為10%,其中每年約15%死于自殺,并預測到2020年抑郁癥將為全球第二大類疾病,高患病率、高死亡率使得抑郁癥已經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與難點[3-4]。抑郁癥病因復雜,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清晰,臨床以對癥治療為主,耐藥性、復發性、服藥依從性差是西藥治療抑郁癥療效欠佳的主要原因[5-6]。相較西醫治療的局限性,中醫藥治療抑郁取得較好療效[7]。本文借助中醫傳承輔助系統分析中醫藥治療抑郁癥的用藥規律,為臨床治療提供新思路,并為臨床選方用藥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登錄國家知識產權局中國專利公布公告網站(http://epub.sipo.gov.cn/)中國專利公布公告界面。
1.2 檢索策略 在“中國專利公布公告”的“高級查詢”界面中同時勾選“發明公布”與“發明授權”,分別將“抑郁癥 and 中藥”及“郁病 and 中藥”作為“名稱”項目進行檢索,合并檢索結果。
1.3 納入標準 納入國家專利數據庫中治療抑郁癥的全部中藥復方專利及含中藥提取物專利,中藥藥物組成相同但用量不同的專利可重復錄入。
1.4 排除標準 中藥藥物組成及用量相同的專利僅錄入1次;中藥專利屬于保健品、酒水、食品等不錄入。
1.5 數據的建立與數據庫的規范
1.5.1 數據庫的建立 共收集到治療抑郁癥的中藥復方專利126項,運用Excel軟件建立抑郁癥中藥復方專利數據庫,使用中醫傳承輔助平臺(V2.5)錄入中藥,最終由2人分別錄入數據,并再次對數據進行審核。
1.5.2 數據庫的規范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8]對中藥名稱及中藥提取物(中藥提取物轉換成對應的中藥)進行規范,同一中藥不同名稱,如夜交藤、首烏藤統一按夜交藤錄入,遠志、細草統一按遠志進行錄入。
1.6 數據分析 應用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研制的中醫傳承輔助平臺(V2.5)分析數據。采用頻次統計方法對納入的中藥藥物頻數進行分析,對四氣、五味、藥物歸經進行歸類統計;設置合理支持度與置信度,運用關聯規則方法分析中藥復方專利的配伍規律、核心藥物,展示相關復雜網絡;設置合理相關度與懲罰度,運用熵聚類得出核心組合及新處方,展示相關復雜網絡。
2 結果
2.1 藥物頻次 對錄入的126項專利中藥組成進行頻次分析,共得到176味藥物,按照從高到低的頻次排序,篩選出頻次≥15次以上的藥物,共26種。見表1。

表1 126項國家專利數據庫治療抑郁癥中藥復方單味藥分布(次)
2.2 藥物歸經 對統計出的176味中藥進行歸經分析,并按使用的頻次進行排序,結果治療抑郁癥的中藥主要歸肝、心、脾三經。見圖1。

圖1 治療抑郁癥中藥歸經頻次(次)
2.3 藥物性味 對統計出的176味中藥進行性味分析,結果治療抑郁癥的中藥藥性主要為溫性、寒性。見圖2。藥味主要為甘味、苦味、辛味藥。見圖3。

圖2 治療抑郁癥中藥四氣頻次分布

圖3 治療抑郁癥中藥用五味頻次分布
2.4 對藥頻次 設置支持度個數15(支持度8.5%),置信度0.8,分析126項專利中成藥對藥頻次≥15次的使用情況,頻次由高到低排列。見表2。

表2 126項專利數據庫治療抑郁癥中藥復方專利前11對藥(次)
2.5 基于關聯規則的配伍規律及復雜網絡 在系統的方劑分析模板中,使用“組方規律”分析,設定“支持度個數”為12,“置信度”為0.55,結果顯示,置信度最高為:當歸,白芍->柴胡。其中置信度前13的藥對關聯規則見表3。基于配伍規律的復雜網絡,挖掘得到核心藥物為柴胡、白芍、郁金、遠志、當歸、合歡皮等。見圖4。

表3 126項專利數據庫治療抑郁癥中藥復方專利中藥關聯規則

圖4 專利數據庫治療抑郁癥中藥復方專利核心藥物(支持度個數12、置信度0.55)
2.6 基于熵聚類的核心組合及新處方 在系統的方劑分析模塊中,使用復雜系統熵聚類進行核心組合分析,設置相關度為8,懲罰度為2,演化得到核心方藥組合,共20組,包括“黨參-琥珀-朱砂”“熟地黃-山茱萸-女貞子”等。見表4。運用熵層次聚類方法進一步組合,得到新處方10首。見表5、圖5。

表4 新方聚類的核心藥物組合

表5 基于熵層次聚類的新處方

圖5 專利數據庫治療抑郁癥中藥復方專利熵層次聚類新處方復雜網絡
3 討論
在中醫抑郁癥屬“郁證”“躁臟”“百合病”等范疇。《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木郁達之,火郁發之,土郁奪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首次記載“郁”的概念,并指出五臟皆可致郁。《素問·舉痛論》云:“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素問·本病論》曰:“人或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即傷肝也。”[9]肝、心兩臟氣不舒是郁證的關鍵發病因素。關于“郁證”病機歷代古籍均有記載,如朱震亨《丹溪心法·六郁》其中提出了氣、血、火、食、濕、痰的“六郁”論,并創立了六郁湯、越鞠丸等相應治療方劑[10]。明代醫家徐春甫所著《古今醫統大全》云:“郁為七情不舒,遂成郁結,既郁之久,病變多端。”認為七情不舒乃郁證關鍵病機。《醫碥》曰:“百病皆生于郁。而木郁是五郁之首,氣郁乃六郁之始,肝郁為諸郁之主。”認為肝氣郁結乃郁病首要發病因素。理氣解郁、調暢氣機是郁證基本治療原則,中醫藥治療抑郁癥不僅可以改善中醫臨床癥狀,而且能夠顯著降低發病自殺率,因此該治療方式越來越受到重視。
3.1 藥物頻次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納入分析的126個復雜專利中,用藥頻次出現15次及以上的藥物共26種,主要為柴胡、郁金、酸棗仁、白芍、合歡皮、甘草、當歸、石菖蒲等。柴胡、郁金使用頻次最高,均為43次,其次為酸棗仁、白芍、合歡皮,均為39次。可見疏肝解郁藥、養血柔肝藥、安神定志藥是治療抑郁癥的常用中藥。
柴胡、郁金均為抑郁癥使用頻次最多的中藥。柴胡味苦、辛,性寒,歸肝、膽、心包絡、三焦經,主疏肝解郁、和解少陽。《雷公炮制藥性解》言:“主傷寒心中煩熱,痰實腸腸胃中……兩脅下痛,疏通肝木,推陳致新。”木郁乃郁證關鍵病機,柴胡善疏肝通木,結合頻次分析可知柴胡為治療抑郁癥代表藥之一。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柴胡皂苷具有抗炎、護肝、利膽、抗抑郁等藥理作用。有研究證實柴胡皂苷通過上調突觸蛋白水平,可顯著改善慢性皮質酮誘導的小鼠的抑郁焦慮狀態[11]。王偉斌等[12]通過對古今醫案研究發現,柴胡-郁金是治療抑郁癥常用組合,二者配伍常用來治療郁證證屬肝氣郁結者。郁金,味辛苦,性溫,歸肝、心、肺經,功善行氣解郁、涼血清心。《雷公炮制藥性解》言:“郁金,主下氣,破血,開郁……古人用以致郁遏不散者也。”可知郁金也是治療抑郁癥的關鍵藥物。李靈等[13]通過構建郁金活性成分-作用靶點網絡藥理學對郁金抗抑郁的機制進行研究,發現郁金抗抑郁的靶點主要涉及β-谷甾醇、5-羥色胺受體、多巴胺受體等關鍵靶點。酸棗仁,味酸、甘,性平,歸肝、膽、心經,功善養心補肝、寧心安神。《長沙藥解》言:“酸棗仁寧心膽而除煩,斂神魂而就寐。”現代藥理學研究發現酸棗仁主要含黃酮、三萜皂苷,具有鎮靜、抗驚厥、改善睡眠等藥理作用。睡眠障礙是抑郁癥患者常見伴隨癥狀,相關調查顯示,約83%抑郁患者合并失眠,目前改善失眠已是抑郁癥關鍵治療標靶[14-15]。白芍味苦、酸,微寒,歸肝、脾經,功善養血斂陰、柔肝止痛、平抑肝陽。《雷公炮制藥性解》言:“白芍酸走肝,故能瀉水中之火,因怒受傷之證,得之皆愈。”可知肝怒之證皆可使用白芍平肝抑陽。柴胡-白芍藥對出自《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二者配伍相使為用,使肝體陰得養,肝陽得抑,斂陰和陽,一散一收共湊疏肝解郁、平抑肝陽之功[16]。藥理學研究表明芍藥總苷是白芍主要成分,具有擴血管、鎮靜、鎮痛、護肝等作用。通過不同濃度白芍苷對小鼠抑郁癥模型干預證實白芍苷具有抗抑郁作用,其機制可能是其上調5-羥色胺受體、多巴胺受體等含量有關[17]。
3.2 藥物歸經分析 通過歸經頻次結果可知,肝經、心經是治療抑郁癥中藥重要歸經,其次是脾經。《素問·刺法論》曰:“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木欲發郁亦須待時,當刺足厥陰之井。”認為肝木升發抑郁之時,可以針刺足厥陰肝經之井穴疏肝解郁。《景岳全書》中記載:“凡五氣之郁,則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若情志之郁,則總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認為情志的抑郁皆由心主導,且抑郁之后又可導致諸多疾病。肝主疏泄,調暢全身氣機致使肝失條達,氣機不暢,而成肝氣郁結;憂思疑慮則傷脾,致使脾失健運,聚濕成痰,而成痰氣郁結;情志過極傷于心,致心失所養,神失所藏,心神失常;心之氣血不足,加之脾失健運,氣血生化不足,而致心脾兩虛;由此可知,肝、心、脾三臟是抑郁癥發病主要病位,肝氣不疏、心脾氣血兩虛是其主要病機。葉天士(葉桂)《臨證指南醫案·郁》記載大量郁病醫案,觀其治療大多為疏肝解郁、健脾和胃、養血清心之法。
3.3 組方規律分析 通過組方規律分析可知,專利中最常見的藥對有白芍-柴胡,郁金-白芍,當歸-柴胡,郁金-柴胡、酸棗仁-合歡皮、柴胡-合歡皮等。其用藥多為理氣藥、安神藥,體現治療抑郁癥以疏肝理氣、解郁安神為主。基于關聯規則進一步分析得到的核心藥物有“當歸,白芍->柴胡”“甘草,白芍->柴胡”“半夏->柴胡”等。柴胡、白芍、甘草即四逆散去枳實,四逆散出自《傷寒論》,具有透邪解郁、疏肝理脾、和解表里等功效,目前治療抑郁癥證屬肝氣不舒者大多以此方加減。通過對四逆散各味藥物成分分析表明柴胡皂苷、芍藥苷、甘草酸、辛弗林均通過其各自藥理作用發揮抗抑郁作用[18-20]。韓永祥和汪紅兵[21]通過研究證實四逆散在臨床上也有顯著抗抑郁作用。
3.4 核心藥物組合及新處方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常用核心藥物組合有“黨參-琥珀-朱砂”“熟地黃-山茱萸-女貞子”“梔子-青皮-纈草”“大棗-甘草-浮小麥”“黃芪-夜交藤-石菖蒲”等;得到10首新處方,其中有“黨參-琥珀-朱砂-龍眼肉-益母草”“熟地黃-山茱萸-女貞子-牡蠣-桃仁”“梔子-青皮-纈草-肉桂”“大棗-甘草-浮小麥-菟絲子-肉蓯蓉”等。從核心藥物組合可知,在常用佛手、香附、薄荷等理氣解郁中藥外,加入了熟地黃、山茱萸、女貞子滋腎陰,菟絲子、肉蓯蓉等補腎陽之品,琥珀、朱砂、龍骨、牡蠣等重鎮安神藥,可見滋陰補腎、重鎮安神也可以是抑郁癥的治療方法。“大棗-甘草-浮小麥”即甘麥大棗湯,甘麥大棗湯出自《金匱要略》,主治“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藥理學研究表明,甘麥大棗湯通過提高體內多巴胺5-羥色胺、去甲腎上腺素水平及活性可以顯著改善多種抑郁模型大鼠行為學特征。臨床上治療抑郁癥常用逍遙散、四逆散等配伍甘麥大棗湯,效果亦顯著[22]。
本文借助中醫傳承輔助平臺對國家專利數據庫中治療抑郁癥中藥復方進行數據挖掘及數據分析,對中藥的四氣五味、歸經、用藥規律進行了客觀分析,初步總結出理氣藥、祛濕藥是其主要用藥,新處方挖掘發現理氣解郁、滋陰補腎、重鎮安神是其主要治療方法。但本研究未對抑郁癥中藥復方所對應證型及具體用藥劑量及功效進行統計分析。
綜上所述,本次挖掘為臨床辨證論治、遣方用藥及新藥研發提供了一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