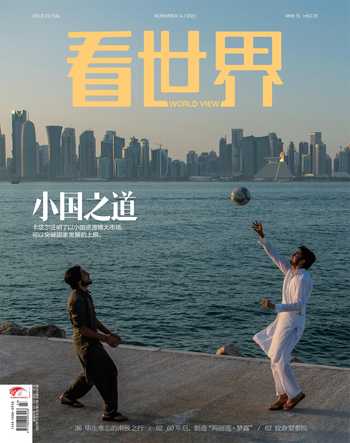黑死病仍在危害現代人類嗎?
欣宇

1656年,描繪意大利那不勒斯暴發黑死病的油畫
近700年前的黑死病,還會影響當下人類的身體健康?這并非聳人聽聞。近日一份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研究,讓人們對瘟疫所帶來的影響有了全新的認識。即使該瘟疫消寂,其對人類的影響也綿長深遠。
發表在《自然》雜志的研究,令人類重新認識流行病:在14世紀中期,黑死病席卷歐洲,多達2億人因此死亡;存活下來的人,他們的基因發生了變化,而這被認為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研究提到,科學家提取了數百年前死于黑死病的幾百具遺骸的古DNA,樣本的范圍涉及黑死病前中后各時期。當用鼠疫耶爾森菌感染這些人類細胞后,研究人員發現攜帶名為“ERAP2”的基因變體的免疫細胞,可以更有效地抵抗鼠疫耶爾森菌。
30%的死亡率讓天花看似比黑死病更為“友善”,但它卻像感冒一樣時常發病。
ERAP2的基因變體,就像是一個蛋白質“制造機”。它們制造的蛋白質,可以將入侵的微生物進行粉碎,同時“提示”免疫系統更有效地識別并讓那些細菌失效,從而讓人在感染中有更大概率存活下來。據稱,這一概率提高到了40%。
之后,從父母身上繼承到有效基因變體的下一代幸運兒,讓這種變異更加普遍,并在后代傳承中,將這種基因變體延續下來。
具有黑死病的“免疫”基因是好事嗎?不妨先回顧幾百年前的那場浩劫。
黑死病是14世紀中期鼠疫的別稱,因其會致患者皮下出血、出現許多黑斑而得名。但更為駭人的是,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只能放血治療的黑死病,致死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在黑死病大面積暴發之前,歐洲因為氣候原因,農作物死亡、糧食減產,人們營養不良、免疫力低下,為流行病提供了可乘之機。
如果此前是天災,那么黑死病因為戰爭侵略而快速傳播,更大程度上是一場人禍。蒙古大軍將帶有鼠疫耶爾森菌的士兵尸體作為攻城利器—用炮車拋進去的尸體將瘟疫帶進城池,而逃出來的居民又將瘟疫“播散”至歐洲各地。
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黑死病是由來自黑海的商船帶入意大利,并沿商路擴散至歐洲其他城市。
有多少人因這場浩劫失去生命?還沒有統一的觀點。法國編年史家傅華薩認為,當年約有1/3的歐洲人死于黑死病。且幾乎每隔一代人,黑死病又在歐洲大陸卷土重來。大約600年后,黑死病才完全消失。
如今,我們有理由相信,黑死病的消失可能源于基因的變異。在自然選擇下,可以抵抗黑死病細菌的基因被傳承下來,而繼承這種變異基因的人類得以存活。
然而,這可能并非完全的好事。在發現ERAP2的基因變體可以一定程度獲得黑死病“豁免”后,研究人員也發現,ERAP2基因成為在現代人群中引起自身免疫性疾病(例如克羅恩病,一種腸道炎癥性疾病)的風險因素。這種疾病可能令人出現腹痛、腹瀉等癥狀,長時間的反復發作或許還會引起腸梗阻甚至威脅生命,且目前尚無根治的一般方法。

2021年6月29日,一個約5000年前被埋在拉脫維亞的男子頭骨。這名男子是已知的第一名黑死病受害者,其尸體上攜帶有鼠疫耶爾森菌

顯微鏡下的鼠疫耶爾森菌

2017年10月,馬達加斯加暴發黑死病,市政工人在市場展開清理行動
雖然與死亡率幾乎100%的黑死病相比,免疫疾病“不值一提”,但卻切實影響著如今人類的健康。
此外,有相關人士認為,大約1%~4%的現代人類DNA,來自我們的祖先與尼安德特人的交配,這種遺傳影響了我們對包括新冠肺炎在內的疾病的反應能力。“過去的那些傷疤,仍然以一種非常顯著的方式,影響著我們今天對疾病的易感性。”一位來自芝加哥大學的教授表示。
瘟疫改變了基因,現在的人類還在為幾百年前的疾病付出代價。然而,疫情帶來的影響不止于此。我們如今對公共衛生、飲水安全等概念的看法,都是在防御大規模疾病中形成并留下的。
消毒隔離,如今采取的防疫措施,在600多年前已初見雛形。拉古薩城,這座曾在19世紀初期被法國占領后因奧地利入侵被滅的小國,現在是克羅地亞最大的港口城市。它在1377年率先推行隔離舉措,要求來自非流行地區的人員或車輛,在指定區域消毒隔離,一個月后才能入城。
這一措施后來在威尼斯被沿用,并且隔離時間在一個月的基礎上又增加了10天,并稱為“Quaranta Giorni”—法語中表示隔離檢疫的“la quarantaine”來源于此,英語為“quarantine”。
同樣是因為侵略,與黑死病流行相隔一個世紀后,歐洲殖民者也把天花病毒帶到美洲大陸。兩三千萬的原住民,在100年后剩下不到100萬人。30%的死亡率讓天花看似比黑死病更為“友善”,但它卻像感冒一樣時常發病。而在歷史的長河中,可以考證的因天花而死的人,數以億計。
攻克天花的鑰匙是疫苗。從唐代孫思邈提出的“人痘”到19世紀逐漸普及的牛痘,人們在與疫情的斗爭中終于取得一次全方位的勝利—1979年10月25日,被確定為“人類天花絕跡日”。
另一場世紀瘟疫,是在1918年春最早出現在美國,隨著美軍抵達法國參加“一戰”,傳遍歐洲和全球的所謂“西班牙大流感”。有數據顯示,1918年10月第二波大流感中,有20萬美國人因此死去;在德國,感染者的死亡率超過27%。
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在疫情中受到沖擊。
第二年的年底,第三波大流感不期而至。但在1920年,如它不明原因地到來一般,它又不明原因地消失。據統計,這種大流感共造成全世界約10億人感染,2500萬至5000萬人死亡。
隨后,各國陸續成立或重組衛生部門,重視醫療建設及疾病防治,同時促進醫療界從研究細菌轉向研究病毒。
14世紀中期,因為鼠疫帶來的大規模死亡,整個社會籠罩于一片愁云慘淡中。那時的文藝作品里,骷髏跳舞的造型成為主流內容。并且,人們亟須得知黑死病的防護方法和可能的治療方案,各種類型的書寫材料開始產生并傳播,除了鼠疫手冊,還有醫學建議文獻等偏醫療專科的內容。
在當時,黑死病就是一場無法解釋的災難,于是神學也頻頻出現在流傳的各種手冊中。

1665年,描繪倫敦暴發黑死病的油畫
然而,黑死病并沒有讓神權的地位再上一層樓。相反,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在疫情中受到沖擊。此前教會提出,黑死病是上帝對人類罪孽的懲罰,采取措施進行抵抗或者逃離,就是與上帝作對。當然,懺悔并沒有帶來救贖,而教會對治病的態度也讓病情愈加蔓延。
疾病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極大沖擊了固有的等級觀念。由此,權力的階層區分不再那么牢不可破,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接受知識和教育,大量如建筑師、泥瓦匠等新職業也接連涌現。
人生苦短,世事無常,人們開始關注自身并追求現實的快樂,而那正是文藝復興思想的核心—人文主義精神。基于黑死病大流行所創作的《十日談》更是強烈抨擊了教會的禁欲主義,為文藝復興點亮前進的火把。科學、理性在人民心中開始萌芽。
同時,大量生命逝去,勞動力成為“香餑餑”,土地反而淪為剩余資源。領主不得不花費更高的價格雇傭人手進行農作。有農民得到領主分租的土地,還有農民脫離土地奔向城市,城市無產階級也由此產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也隨之展開。
影響不僅在人。農作物方面,人口的急劇減少令谷物過剩、谷價下跌,畜牧業隨之發展,多種經營方式開始萌芽。而且,劫后余生的人們追求享樂,珠寶、絲綢、布匹等手工產品需求上升,商品經濟也開始走向繁榮。
看上去,歐洲世界的各個方面,都因這場疾病發生著變革。同時也要認識到,在黑死病暴發之前,無論是人們對神權專制的不滿,還是文藝復興的萌芽,都已有跡可循。可以說,黑死病加速改變了歐洲,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但這并不是一切變革發生的根本原因。
瘟疫危害健康危及生命,亦會帶來深遠影響與反思。在醫療水平進步的同時,人們對待疾病的看法也要與時俱進。世界可知而暫不可盡知,科學、理性一直是對待疾病的最好武器。
責任編輯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