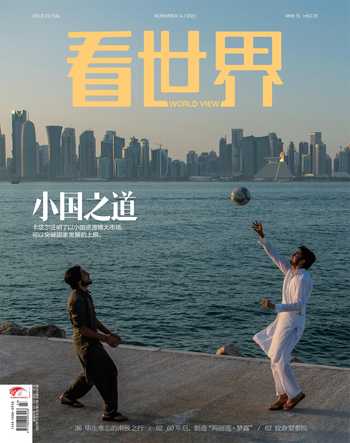“數字日本”掉隊
憐青

在日本,傳真機的使用率依然很高
今年10月,日本郵政集團啟動了“未來郵局”計劃,將利用數字技術,消除顧客對郵局服務不便的印象。
在這一名為“未來”的計劃中,顧客可以通過“窗口大廳使用的平板電腦”,自助查詢郵政編碼、費用、送達天數,閱覽本國郵政條款、郵包條款等。此外,日本郵政后續還將推進郵局窗口的告示電子化,實現無紙化布局。
消息一出,中國網友不禁感慨,上述措施在中國早已實施多年,為何日本卻當成是“未來”呢?
或許很難想象,曾以索尼、夏普、東芝等流行電子產品聞名全球的日本,信息化率竟然低得驚人,一如其人口老齡化比率,盡顯老態老鐘。
時至今日,日本主流廠商依然每年都會推出新的翻蓋手機。日劇中,辦公室里出現最多的電子產品,除了手機、電腦,就是傳真機和固話。日本政府不止一次嘗試推進電子化辦公,卻又以失敗告終,這其中既有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因素,也有產業方面的影響。
難以信息化的日本,恰是該國電子產業近年來一路潰敗的側影。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昔日稱雄全球電子市場的日本,終因未能搭上互聯網行業的車,逐漸被后來者超越。
正如日本學者西村吉雄在《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中所說,日本企業經營者和技術人員沉溺于過去的成功之中,企業最終也沒能當成蘋果,也沒能成為鴻海。
客觀來說,日本數字化的“差”并非有多不堪,而是與其經濟地位并不相襯。《2020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日本的EGDI(電子政務發展指數)排名世界第14位,與兩年前相比下降了4名;同年9月,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發布《2020年國家網絡能力指數》,日本勉強躋身世界前10。
日本的數字化道路,可謂是起了大早,趕了個晚集。世紀之交,面對洶涌的互聯網大潮,時任日本首相森喜朗成立了“IT戰略本部”,發布了《IT基本法》,提出“IT立國”和“E-Janpan”戰略,將發展電子商務、推動信息化建設作為目標,并立下了5年內將日本打造成世界最先進IT國家的誓言。
然而,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森喜朗對電子化的認知相當有限。自嘲是“電腦盲”的他,曾在公開場合將“IT革命”錯說成了“它(英文it)革命”,森喜朗的施政目標也隨著他在一年內草草下臺而付諸東流。
此后十余年里,日本政府在推動電子化和數字化上,始終沒有拿得出手的成果。2012年,安倍晉三再度出任首相,他在任的8年,也是世界互聯網實現飛躍式發展的8年,但日本卻明顯掉隊。
日本的數字化道路,可謂是起了大早,趕了個晚集。

日本動畫作品里頻繁出現翻蓋手機
在“安倍經濟學”中,數字化起初并未占重要地位。日本內閣發布的《經濟財政運營和改革的基本方針》中,在2016年至2018年間,關于“數字化”的表述都不超過10次;直到2019年和2020年,“數字化”一詞的提及次數才有了顯著上升。
2020年,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內閣中設立了“數字擔當大臣”一職,還成立了專門的行政機構數字廳,指望其成為“日本政府電子行政的司令塔”。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有78%的受訪者支持建立數字廳。但從近兩年的結果來看,除了推動政府在行政手續中不再只認印章外,數字廳在幫助日本實現數字化轉型上,并沒有更多的建樹。
在疫情沖擊下,較低的電子化程度也為日本民眾帶了諸多困擾。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就已普及了收發一體的傳真機。即便疫情來襲,東京依然在用古老的傳真方式確認新冠確診人數,平添了不少工作量,降低了抗疫效率。
對“工匠精神”有著嚴重路徑依賴的日本企業,對分工抱有抗拒心理。
據NHK報道,2020年11月起的約兩個月,東京都內18個保健所因“傳真機出現障礙未發送成功”“工作人員忘記確認”等原因,共計漏報了838例確診病例。
為了刺激日本經濟,日本政府計劃向每位國民發放1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500元)的補助金。日本民眾雖可以通過網絡申請領取,但申請完成后,仍需打印紙質版后手寫提交,因此各地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民眾扎堆前往政府部門辦理的場景。
據統計,疫情前的2019年,日本中央行政部門約5.5萬項行政手續中,僅有7.5%可以在線完成;疫情后,這一數字有所上漲,但比例也不過12%而已。
2021年4月,有感于政府工作人員在居家辦公時難以收發傳真的現象,時任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提出,日本所有中央政府部門應盡快廢止已經不合時宜的傳真機辦公,改用電子郵件傳遞文件。
這一主張旋即遭到了各部門反對,400條反對意見中,既有出于防泄密的考慮,也有直接表示不會使用電子郵件。這般蜂擁而至的反對聲,讓這一輪改革最終不了了之。
今年8月31日,已轉任數字擔當大臣的河野太郎,在推特上宣布“向軟盤宣戰”。河野太郎表示,如今日本有約1900項行政程序,要求申請者使用軟盤或者CD等完全過時的信息存儲介質,提交申請表格。為此,日本將盡快更改規定,搭建線上平臺,讓民眾可以在線提交。
對于如今容量動輒以TB計算的U盤而言,僅有1.44M容量的軟盤已經難以跟上時代需求,連索尼都在2011年就停止生產軟盤了。盡管如此,有工作人員表示反對更改規定,認為比起如今各種存儲介質,軟盤要更加可靠,而且不少用戶也不愿意更換常年使用的軟盤。
除了政府部門外,日本商界也沒少在推動數字化上傷腦筋。2021年開始,日本瑞穗銀行、三井住友銀行、三菱銀行等,相繼對新開通賬戶辦理紙質存折收取550—1100日元不等的手續費,希望以此推動電子存折業務。

日本蓋章文化
日本推進電子化阻力重重的背后,最直接原因莫過于老齡化。2020年國勢調查(即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28.6%,老齡人口數創下新高。
老齡化下的日本,不僅一般老人不理解電子化,甚至連負責該項事務的官僚,也對電子化近乎一無所知。
2018年,時年68歲的奧運大臣櫻田義孝,在面對議員提問時表示,一般他都讓秘書或者手下來操作電腦,“我并沒有使用過電腦”。此話一出,輿論嘩然—因為櫻田的另一身份是網絡安全立法的負責人。

2020年10月19日,東京當地一座寺廟為企業不再使用的印章舉行“追悼會”
除了老齡化外,電子產業的沒落也讓日本遠離了社會數字化道路。1991年,日本正處于泡沫經濟的繁榮時期,NHK當時播出了一部名為《電子立國—日本自傳》的紀錄片,驕傲地宣布電子產品是繼汽車之后,日本賺取外匯的又一得力大將。
但這一產業盛景在接連的金融危機沖擊下輝煌不再。2013年,隨著被譽為日本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最后希望的爾必達破產,瑞薩電子亦陷入困境,曾經以10萬億日元貿易順差為外匯儲備做出巨大貢獻的日本電子產業,曾經因產品過于暢銷而在全球引起貿易摩擦的日本電子產業,已經徹底轉變為了貿易赤字,絲毫找不到半分往日的榮光。
西村吉雄認為,日本電子產業曾經以“質優價廉”的產品風靡全球,之后產業整體沒有從這一成功中走出來。“或許可以說,成功是失敗之母吧。”這就像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依靠蒸汽動力成為科技霸主,卻因此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內燃機時代失去先機。
崇尚“工匠精神”的日本,將單品質量做到了極致,經久耐用一度是日本電子產品的重要標簽。新千年以來,設計與制造分工成了電子行業的必然趨勢,但對“工匠精神”有著嚴重路徑依賴的日本企業,對分工抱有抗拒心理,固執地堅持縱向聯合和獨立經營。在西村吉雄看來,這也是日本電子產業衰落的一個原因。
失去了電子產業榮光的日本,在數字化道路上舉步維艱。即便日本決心推動數字化,該國還缺乏廉價、可依靠的本國硬件作為支撐。
正如西村吉雄所說,只有當企業經營者、技術人員不再沉溺于過去的成功,或是寄希望于沒有經歷過這些成功的年輕人,才有再現昨日輝煌的可能。按照這個思路延伸下去,對于日本的數字化而言,或許只有當越來越多享受過數字化紅利的年輕人加入官僚系統,“數字日本”才不再遙不可及。
責任編輯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