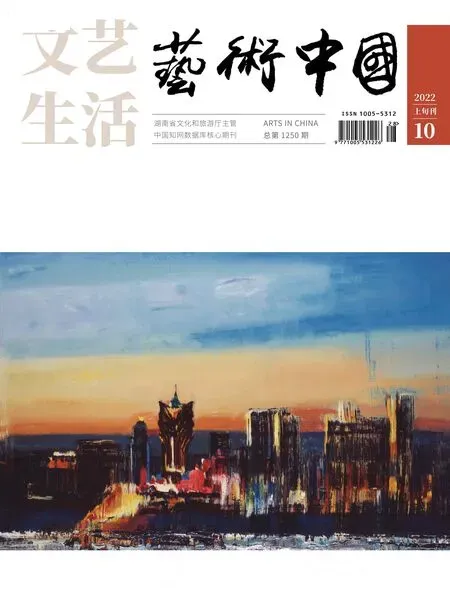宋貢硯中的雙框篆文紀年款假說
◆李守亮( 北京 )
1.引言
在新見宋硯中,見有兩方在硯背鐫刻雙框篆文紀年款,分別為“咸平元年”和“嘉定十六年”。“咸平”硯為蓋硯,硯蓋高浮雕一臥虎鈕,硯面平,硯背淺挖,在硯背正中豎刻“咸平元年”四個篆字,外飾雙線框。“嘉定”硯,上窄下寬略呈梯形,硯堂平坦,四周隱起輪廓,上方雕一正面螭龍。硯池環繞硯堂一周,呈曲水樣。硯墻較矮,硯背作淺坡,不出足。硯背正中豎刻“嘉定十六年”五個篆字,外飾雙線框。
“嘉定”硯的尺寸比“咸平”硯稍大,兩硯的紀年款與硯身成一定比例,大方得體。咸平元年(998)和嘉定十六年(1223)相距225年,但兩方硯紀年款的鐫刻風格極為相似,暗示了他們具有相同的特殊身份。贗硯歟?貢硯歟?御硯歟?

2.宋貢硯考略
貢硯來自硯石產地,有專職官員負責督辦,每年把品質優秀、稀缺珍罕的極品硯和精華硯進貢給朝廷。本節以端硯為例,略考宋代歲貢端硯的數量、采石制硯和進御后的用途。
2.1 貢硯形制
北宋歐陽修《南唐硯》記:“當南唐有國時,于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米芾《硯史》:“仁宗已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刋花,中為魚為龜者,凡此形制,多端下巖奇品也。”
可見,純薄、平淺和峻直是貢硯的特征之一。米芾所言賜史院官硯,是貢硯中的一類形制,本文“嘉定十六年”硯的造型與此比較相符。
2.2 歲貢數量
歷代史志多記各地進貢物品的條目,很少記貢品的數量。史料中僅見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某年貢硯凡四十枚,其中端硯十枚。
北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卷九記:“陜西路……虢州,虢郡……土貢(麝三兩,地骨皮一十斤,硯二十枚)……寧州,彭原郡……土貢(硯一十枚);福建路……端州,高要郡……土貢(銀一十兩,石硯一十枚)”又見南宋趙與時《賓退錄》卷十記:“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高宗建炎三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谷,余悉罷貢,盛德事也。《禹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里之書,但載土貢之目,而不書其數,惟《元豐九域志》為詳。嘗撮一歲所貢,凡為金二十四兩……筆一千管,(江寧五百管,宣五百管),墨三百枚,(兗、潞、維各一百枚),硯四十枚,(虢二十枚,寧、端各一十枚),紙四千張,(越、歙、池各一千張,真、溫各五百張)……”
蘇易簡《文房四譜》和朱長文《墨池編》均記:“《通典》云:虢州歲貢硯十枚”;高似孫《硯箋》記“端州歲貢硯十(《九域志宋包孝肅公傳》:端歲貢率數十,公知端,歲滿不持一硯)……寧州歲貢硯十枚”;吳蘭修《端溪硯史》記:“淳化二年(991)夏四月庚午,罷端州貢硯。(宋史《太宗紀》)端州歲貢硯十。(王存元豐《九域志》)仁廟以前賜史院官硯多是下巖石,其后來歲貢,惟上巖石。(《硯史》)石材之大者尤為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而無病脈者,固亦少矣。此歲所貢方硯耆硯者五,皆以文為準,然止于巖石之中品。或有眼,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唐詢《硯錄》) 蘭修按:太宗罷貢硯,而元豐時王存等撰《九域志》仍載入土貢,《米史》亦載,治平中貢硯事殆未久己復也。”
從引用關系上看,記載宋貢硯數量的出處,似乎都來自元豐《九域志》。正常歲貢,端硯的進貢數量并不離譜,但在大觀年間例外,大觀的三年之中進貢九千枚,平均每年進貢三千枚,下文有述。
2.3 采石制硯
南唐時,歙硯產地設有硯務官。宋代,在端石產地也有漕臣或本地知府負責督辦。因工程浩大,端溪采石(下巖)往往由官方組織。米芾《硯史》記:“(端溪下巖),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水浸。治平(1066)中貢硯,取水月余,方及石。”故蘇軾有:“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之句。《宋會要輯稿》記:紹熙元年(1190)七月二日,肇慶知府林次齡“輒差虞兵,監勒石匠深入巖水打硯,致傷損身故”,被廣東提舉劉坦劾奉罷官。嘉泰四年(1204)六月十七日,詔:“肇慶府之硯石,歲鑿不已,致江水滲入,今則候冬月巖水稍淺,命農夫車水,硯匠伐石。又有新坑南坑,搜挾殆遍。夫匠絡繹山間,歲失生業,不能自存……肇慶不得取硯石……”
不過,米芾《硯史》又說“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其后來歲貢,惟上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粗性硬……”從前文的《宋會要輯稿》所述,及后文的大觀三年下巖采石的記錄來看,米芾之說(后來歲貢,惟上巖石)不盡然。
宋代的筆墨紙硯都設有專門制造的小手工業作坊(作、行、鋪、店等),有的還發展為大型作坊。端石制硯,即由當地的硯作坊生產,既有小型的硯戶,也有大型的硯場,如蔡襄《硯記》述“端州崔生之才居端巖側,家蓄石工百人,歲入硯千”。 硯作坊完成貢硯之后,才可以生產市硯。
2.4 恩典賞賜
宋仁宗之前,貢硯主要賞賜國史院的史官。米芾《硯史》記:“下巖既深……聞有仁廟已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后來歲貢,惟上巖石。”“仁宗已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清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亦有:“宋貢硯惟賜史官,故端硯重于天下。”
宋徽宗的賞賜范圍,則擴展到王公大臣甚至跟隨侍從。宋蔡絳《鐵圍山叢談》記:“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觀中(1107—1110),命廣東漕臣督采端溪石研上焉。時未嘗動經費,非宣和之事也。乃括二廣頭子錢千萬,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時以三千枚進御,二千分賜大臣侍從,而諸王內侍,咸愿得之,詔更上千枚,余三千枚藏諸大觀庫。于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巖穴,蓋欲后世獨貴是研,時人或不知厥繇。今世有得此者,非常材矣。”
從元豐《九域志》可知,元豐前某年貢硯全國四十枚,其中端硯僅十枚。而在宋徽宗大觀三年的時間內,進貢的端硯數量竟達九千枚之多。作為恩惠賞賜,宋徽宗對近臣侍從出手非常大方。
2.5 國庫收藏
賞賜之外,宋徽宗將一部分貢硯收藏于國庫。除蔡絳《鐵圍山叢談》有記述之外,在南宋周輝的《清波雜志》亦有:“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余枚。”宋高宗同樣有藏硯之好,其在《翰墨志》中記:“端璞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致,潴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后歷新坑,皆不可用,制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于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但是,宋高宗收藏的貢硯卻大部分沉入海底。明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記:“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硯,載以自隨,拍浮滄波,徘徊島嶼。于斯時也,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舳艫,往往飄沒,硯之淪于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后漁人蜑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
大觀庫是宋代朝廷國庫,宋徽宗大觀中(1107—1110)置。大觀東庫主要儲存坑冶金銀及細軟、香等物,西庫主要儲存錢幣。其他御內國庫,另見宋洪邁《容齋三筆》卷十三的“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于內帑置庫,自制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于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于四榷場鬻錢銀,準備買馬,其數至于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來,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為四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熙以來,頗供好賜之用,似聞日減于舊云。
參照庫銀的形式,國庫庫藏物品或有便于識別和便于歸類的特殊標志。貢硯是按年進貢,又作為朝廷國庫的庫藏品,此“雙框篆文紀年款”,會不會是庫藏貢硯的特定標識?


3.宋御硯考略
御硯來自貢硯,也來自按樣訂制,貢硯并不等同于御硯。南宋葉樾《端溪硯譜》記:“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底耳。有四環刻海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昆侖狀,左日右月,星斗羅列,以供大上皇書府之用。”此處的“御府降樣”,降到哪里?
在清代,內務府造辦處設有“硯作”,專門負責宮廷用硯的制作。而在宋代,生產宮廷和官府用品的機構則是后苑造作所和文思院。其中,后苑造作所領八十一作,掌造禁中及皇屬婚娶名物。文思院領三十二作,外加后苑十作,掌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繪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冊寶、法器,及凡器服之用。皇帝有需求時,下詔讓后苑制造,后苑造作所據此擬定“請領憑由”從相關機構中取得原料,然后便開始生產。文思院屬于官府手工業機構,其上界打造金銀服務于皇帝,補充后苑造作所的不足。其直接生產者和人匠是雇傭而來的,早上到院中入作生產,晚上離院回家并領取報酬。但是,后苑造作所和文思院都沒有“硯作”,只有類似的“玉作”和“玳瑁作”。只要皇帝有詔,兩個官方機構就有義務找到相關的能工巧匠,這一點毋庸置疑。
宋代貢硯和御硯,莫說今人,在當朝的常人都難見真容。可以肯定的是,能到此級別的硯,無論材質,造型還是做工,必定與眾不同。如圖之硯,能到此級別嗎?
另見有文思院鑄“嘉定十六年”紀年款的官印,知文思院制器有紀年之例。那么,宋徽宗降樣制御硯,是降到文思院或后苑造作所嗎?文中硯背的“雙框篆文紀年款”會是文思院所鐫嗎?



4.雙框紀年款考略
紀年款是在器物上用寫、刻或印等不同方法,標明器物制造年代的一種款識。字體有楷、有篆,款外常見雙圈、雙線方框或單圈,也有無圈框或雙長方框,款字多為豎寫。紀年款常見于明清官窯瓷器,以雙線方框居多,且書寫規整。民窯偶有紀年款,但書寫較隨意。
宋代五大名窯因多為顏色釉且滿釉,不便于書寫,但有刻畫款(如定窯樞府款,汝官哥均見出窯后的刻畫款,少見紀年)。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有一方北宋越窯青釉硯臺,入藏編號PDF273,背部刻有“元符三年中秋佳制”紀年款。
宋代雙長方框紀年款瓷器,則見葉佩蘭主編的《海外遺珍·陶瓷》卷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P130)中記,收藏于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入藏編號50.1999的磁州窯張家造黑釉花卉紋枕,有印陽文楷書雙長框紀年款“宣和元年”,以及雙框款“張家造”。在民間藏品中,宋代磁州窯亦見有雙框“××造”款。
5.結語
宋代貢硯進御之后,一部分宮廷自用,一部分用于賞賜,一部分收入國庫。由于貢硯是按年進貢,為了便于識別和庫藏分類,雙長方框篆文紀年款,或為宋代貢硯或庫藏貢硯的一種紀年標識。大膽假設,更須小心求證。此假說是否成立,需要更多的文獻和實物進行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