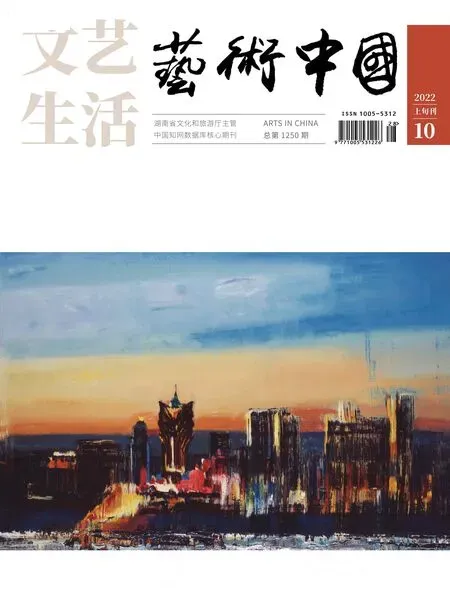“二爨”的審美價值及對當地文化形象的塑造
◆ 陳玲玲(上海旅游高等專科學校)
如果說文化人到紹興,不得不到蘭亭,于山陰道上行走,感受一下永和九年的那一場曲水流觴。那么,文化人到云南,不得不到曲靖,探訪一下“二爨”,體味一番南朝碑刻的樸茂蕭疏和古意盎然。
南朝自晉室南遷至其滅亡,從公元317年至420年,歷一百余年。南朝繼承東晉的風氣,上至帝王,下至士庶,無不以書法為雅好。但“南朝禁碑,至齊未馳”,書法傳世作品多以尺牘、書札等墨跡為主。像《爨龍顏碑》《爨寶子碑》這樣的南朝碑刻的出土,是極其罕見的。“二爨”書風標新立異,與同時代碑文幾無相同者,所以更為世人所重。
“二爨”概述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及道光七年(1827),在云南曲靖及陸良地區先后出土《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由于《爨寶子碑》字數較少,形制較小,后人常將其稱為“小爨”,《爨龍顏碑》則為“大爨”,兩碑合稱“二爨”。之所以分大小,是因其形制的差別:《爨龍顏碑》比《爨寶子碑》體積大了不少;且“大爨”的墓主龍顏享年61歲,而“小爨”的主人寶子享年僅23歲。有趣的是《爨寶子碑》比《爨龍顏碑》早刻立了50多年;在1300多年后,《爨寶子碑》重見天日的時間又比《爨龍顏碑》早了50年。
《爨寶子碑》,全稱《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墓碑》,俗稱“小爨”,立于東晉大亨四年(404),最早出土于曲靖揚旗田村,后移至曲靖城內武侯祠,1937年移到曲靖第一中學。1961年3月,被國務院將其列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撥款重修理建碑亭,加固碑座。“小爨”碑額題“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墓”,碑文400字,字口清晰可辨。通高183厘米,寬68厘米,厚21厘米,碑文13行,每行30字。碑的下部有題名13行。

爨碑亭
爨氏作為南中的大姓豪族,有悠久的歷史。至南北朝,爨氏已稱雄南中,建寧(今曲靖地區)、晉寧(今滇池地區)兩郡,就是爨氏管轄的中心地區。爨寶子是爨氏統治集團的成員之一,此碑敘述了他的家世、生平及政績。碑末的職官題名,反映了當時建寧太守的屬官情況,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近代袁嘉谷為《爨寶子》碑亭撰有一聯:
奉東晉大亨,寶子增輝三百字;
稱南滇小爨,石碑永壽二千年。
其筆畫如長槍大戟,直往直來,沉著痛快;且內剛外柔,方拙中帶勁巧,融參差錯落于端嚴整傷之中。結體古樸,每多篆隸遺姿,康有為稱它“樸厚古茂,奇姿百出”。小爨碑在用筆、結體、章法上竭盡動蕩、變化之能事。同一點畫,因字而殊,欹正互變。它的點畫節奏鮮明,用筆以方筆為主,端莊古樸,拙中有巧。此碑的可貴之處在于其書法體現了隸書向楷書過渡的一種風格,結體古樸,頗多篆隸遺意。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碑評第十八》評此碑“端樸若古佛之容”,同書《寶南第九》并說:“晉碑如《郛休》《爨寶子》二碑,樸厚古茂,奇姿百出,與魏碑之《靈廟》《鞠彥云》皆在隸楷之間,可以考見變體源流。”同書《取隋第十一》云:“吾愛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寶子》《枳陽府君》《靈廟碑》《鞠彥云》,以其由隸變楷,足考源流也。”

爨寶子碑整拓

爨寶子碑局部 (1)

爨寶子碑局部 (2)

爨寶子碑局部 (3)

爨寶子碑局部 (4)

爨寶子碑局部 (5)

爨寶子碑局部 (6)

阮元題跋
《爨龍顏碑》,全名“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鄧都縣侯爨使君之碑”。碑陰題名頗多,為研究云南的地方史、特別是研究爨氏家族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爨龍顏碑》始建于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高388厘米,寬146厘米,除碑陰題名外,僅碑陽即存文900余字,故稱“大爨”。1963年,此碑被國務院定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撥專款對原碑室進行了維修,1986年又將碑移至大殿內,并將大殿按原貌修復,對此碑進行重點保護。
康有為將《爨龍顏碑》與《嵩高靈廟碑》相比,認為“淳樸之氣則《靈廟》為勝,雋逸之姿則《爨碑》為長”,“魏晉以還,此兩碑為書家之鼻祖”(范壽銘《爨龍顏碑跋》)。康有為說此碑“與靈廟碑同體,渾金璞玉,皆師元常(鐘繇)實承中朗之正統。”他在《碑品》中將爨龍顏列為“神品第一”,贊其“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足見書家對它的推崇。
清桂馥跋此碑云:“王法兼用隸法,饒有古拙之趣。”楊守敬《平碑記》云:“絕用隸法,極其變化,雖亦兼折刀之筆,而溫淳爾雅,絕無寒乞之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碑品第十七》將此碑列為“神品”,同書《碑評第十八》云:“《爨龍顏》若軒轅古圣,端冕垂裳。”《寶南第九》云:“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體系第十三》云:“《爨龍顏》與《靈廟碑》同體,渾金璞玉,皆師元常,實承中郎之正統。”《論書絕句第二十七》并有絕句:“鐵石縱橫體勢奇,相斯筆法孰傳之。漠經以后音尖絕,惟有龍顏第一碑。”
從《爨寶子碑》隸、楷皆有的筆意、結體雙重特征,到《爨龍顏碑》漸去隸意而楷法趨于成熟的演變,書家將兩碑視為隸、楷過渡的典范作品及北朝楷書存古法的力證。“二爨”書體流變過程,是在共同的美學特征下、不同的發展階段、按一定規律衍化的書法現象。

爨龍顏碑局部 (1)

爨龍顏碑局部 (2)

爨龍顏碑局部 (3)

爨龍顏碑局部 (4)

爨龍顏碑局部 (5)

爨龍顏碑局部 (6)
“二爨”與爨文化
阮元在《爨龍顏碑尾隸書題跋》中說:“此碑文體書法皆漢晉正傳,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新纂云南通志(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頁)葉昌熾在《論各省石刻》中說:“滇疆僻在南荒,而二爨碑一晉、一宋可傲中原所稀有,足為雞足增輝。”(《語石·卷二》)“二爨”產生的時代、地域及其所具的文化價值,決定了其書法史中的地位遠遠高于其它諸碑版。“二爨”文化身份認同的特殊表現,是與傳統經典的對比。梁啟超論南北書法時說:“南帖為圓筆之宗,北碑為方筆之祖。遒健雄渾,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長也,《龍門二十品》《爨龍顏碑》《吊比干文》等為其代表。秀逸搖曳,含蓄瀟灑,南派之所長也,《蘭亭》《洛神》《淳化閣帖》等為其代表。”(《梁啟超全集》卷四,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931頁 )這里北碑中《爨龍顏碑》等碑的地位,已經上升到與《蘭亭》為代表的“二王”帖學經典相提并論。
“爨氏”從蜀漢之際就開始聞名于天下,漢武帝開滇,爨氏成為南中大姓之一。西漢王朝曾“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漢朝將軍隊中的部分將領、士兵留在云南定居,與當地的土著相結合,且“南中”戰亂較少,社會穩定,出現了《爨寶子碑》描述的“山岳吐金”“物物得所”“邑落相望,牛馬成群”的繁榮景象。內地漢民為逃避戰亂亦不斷遷入云南,從而促進了爨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隨著公元581年隋渡長江滅陳,后隋文帝兩次出兵南中,將爨氏家族首領爨翫的全家逮捕后帶回長安,將爨翫處死,“諸子沒為役”(《新唐書·兩爨傳》)。但此舉并未能控制南中地區,爨氏的其他首領繼續據有南中。公元749年,南詔政權在唐朝扶持下,建立南詔國,結束了爨氏家族在南中地區四百多年的霸主地位。
就爨文化的歷史來講,其歷史淵源上可追溯到“羌奴賦高山之句”的秦漢時期,其中可數可點的有玉琵琶、龍詠箏、菩薩蠻、打棗竽、石榴花、元鳥行、爨棘童歌、刺繡、小姑夜話等。其中,曲靖爨鄉古樂源遠流長、經久不衰,是爨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二爨”也是爨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是云南邊陲少數民族的首領受漢文化的熏陶、仿效漢制而樹碑立傳的。讓人們不可思議的是,“二爨”的書法風格,不是魏晉瀟灑飄逸之風格,反而與萬里之外的在文化交流上相互阻隔的北碑書風相似或相近,這真是一個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從清中期阮元“云南第一古石”的評價到清末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奉為“神品”,“二爨”從訪得即受到清代書家、學者的贊譽。在晚清碑學大潮中,更一躍成為北碑經典。“二爨”的存世,使得曾經在歷史上燦爛輝煌數百年的“爨文化”在現世得以挖掘,讓“遠逝的繁華”能夠“鮮活”于今世。
“二爨”之于當地文化形象的塑造
從清中期阮元以來到包世臣、吳仰賢、譚獻、汪鋆、楊守敬、葉昌熾等在金石題跋中對“二爨”的品評,兩碑在清代中晚期可謂聲名大噪。
一個地域有一個地域獨特的文化,深入挖掘自己的文化資源,能夠在傳承和創新中不斷發展。文化不僅塑造了城市的品格,展示了城市的風貌,更是城市魅力的集中體現,是曲靖之所以為曲靖的靈魂。
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以及因之而散發出來的精神氣質。曲靖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爨文化對于曲靖而言,既是一個遙遠的鄉愁,又是一段湮沒的歷史;既是曲靖的風情,又是曲靖的風骨。歷史上中原文化入滇,從地緣上,是必經的通道,曲靖是內地進入云南的門戶。爨文化是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大融匯后開出的一朵奇葩。以至于一千多年后,我們再次注目于幸存的“二爨碑”,感慨之余,眼前不禁浮現出當時社會的景象。
“二爨碑”歷經滄桑,在一千多年的歲月磨洗中能幸存于世,離不開古之賢達、今之政府對它的悉心保護,而對它們的研究,也傾注了從古至今許多人的心血。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爨文化”乃其中一支,而“二爨碑”又是“爨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擁有“二爨碑”的曲靖一直以“二爨之鄉”自居。往事已矣,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是:開創了云南第一個五百年歷史的古爨之地的曲靖兒女,應賦予這片沃土怎樣的內涵?或者說未來我們將如何定位、開發、打造曲靖的城市靈魂,是我們不得不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