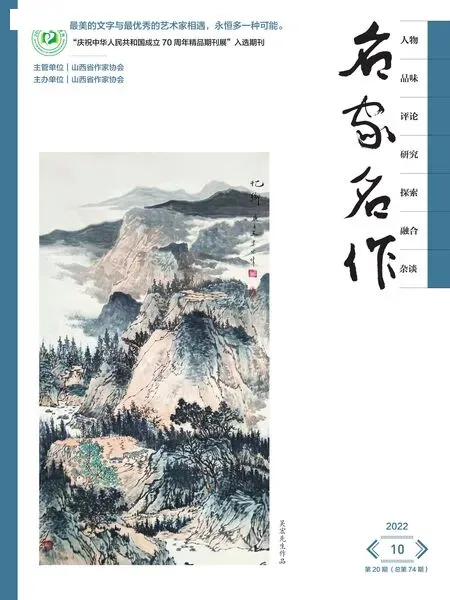淺談塞尚繪畫中的痕跡
張 起
塞尚被稱為“現代繪畫之父”,本文分三部分對塞尚的繪畫藝術進行探討:(1)不離開感覺捕捉真實;(2)形式構成;(3)圣維克托山中的顫動晶體。
一、不離開感覺捕捉真實
縱觀塞尚的一生,其藝術生涯在早期分為兩個時間段:一是浪漫主義時期,二為印象主義時期。無論是塞尚的早期繪畫,還是后期他個人風格成熟時期,他的繪畫都有著強烈的個人特色,這是他對真實、執著的追求過程,他堅持不離開感覺捕捉真實。
以他的早期油畫作品《盛宴》為例,在此作品中,畫面呈現出一種強烈的肌理厚度,畫面色彩具有斑駁陸離的印象,古典主義繪畫中陰暗的色調蕩然無存,相反更多地呈現出印象派時期的明亮色彩,整體的畫面沒有見到他執著于對細節的刻畫,而是力求尋找視覺真實,在整體光色上保留一種統一的存在的痕跡,人物在整體氛圍中以一種存在而顯現。
在他的早期水彩作品中,也有一種空氣感,即使他當時整體的繪畫相較于晚期的作品畫面更加充實。在Still Life:Flowers and fruit這幅水彩作品中,我們能感受到畫面中花的存在就是一種虛無感很強的痕跡,作為畫面主體已經沒有花的具體形象,而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內以花的感覺而存在。
在印象主義時期,他的老師畢沙羅建議他到戶外寫生,感受自然的魅力。于是他跟隨畢沙羅的腳步,細致地觀察身邊的一切色彩,在自然界中感受光所帶來的豐富的顏色變化,這使他對印象派的色彩與光線的理論了然于胸,他開始意識到藝術還是要回歸到自然中才能有更多可能。但隨著他的認知不斷加深,他意識到當時的印象派藝術家都只是把藝術表達的側重點放置于炫彩奪目的顏色變化中,而忽視了物體所固有的“形”,他們把物體固有的、輪廓的形單純地用顏色變化來替代,這只是印象派對于事物外表變化的一種瞬時性感覺上的經驗,這種經驗經不起嚴格的推敲,或者說只是感性的、表象的。這種手法使物體本身的重量感以及結構的嚴謹性蕩然無存,而更追求的是,“把印象派的繪畫變得堅實且持久,就像博物館里的藝術一樣”。他不滿足于印象派只追求光帶來的轉瞬即逝的感受,這些在他看來只是表象,失去了繪畫該有的深度,他要在繪畫中追求一種視覺的真實。所以在藝術創作中,正如他那些早期的水彩畫,他也拋棄了印象派的小筆觸,改為用一種堅實的色塊,通過色彩以及形體追求結構的真實。在他圍繞古典主義構圖所作的繪畫如《現代奧林匹亞》這幅作品中,塞尚顯然是在致敬馬奈,但是他的方式與馬奈并不相同。在他的畫面中有了自己的思想,并在整體的、強烈的、確定的筆觸中呈現整個畫面的律動之美,此時的畫面呈現完全不同于古典繪畫,而更具有一種存在其中的虛無痕跡之感。
此后,他在古典大師普桑處尋找到此前他發現印象派所缺失的那種嚴謹的、堅固的建構形式,但他也不僅僅滿足于此,很快他意識到,“不離開感覺捕捉真實”才是他所要的,他要“面對自然活化普桑”。這樣的經歷,才有了他畫面中形體疊合和色彩并置的筆觸,并借助幾何形式尋找畫面中的內在組織語言,對于物體的體塊以及造型都有著極為嚴苛的追求,這是他不離開感覺尋找真實的體現。塞尚對于畫面有著如此嚴謹的要求,才有了他最后極為完滿的結構的畫面。此時他的繪畫已經趨于成熟,以《普羅旺斯的農舍》(如圖1)為例。在這幅作品中,畫面上充滿了由小色塊構成的豐富的層次,但當你想接近這一切時,會發現他們渾然一體,處于一個混沌的虛空之中,卻又堅實地存在,畫面中任何一處都像是在運動中,但又具有完美的結構,畫面中的細節好像在不斷逃離,但真實性又在逐步顯現。弗萊把塞尚追求實物的獨特細節的創作,描述為:“他們被還原為純粹的空間和體量元素。”①羅杰-弗萊:《塞上及其畫風的發展》,沈語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第129頁。

圖1 《普羅旺斯的農舍》 塞尚/作
在對畫面完滿的追求上,塞尚晚期的作品中呈現出一種打破單個對象統一性的傾向,并且他也一直在追求不脫離感覺來尋找真實,這其實在梅洛龐蒂看來是一種“二律背反”——“追求真實,又禁止達到真實的手段”②梅洛-龐蒂:《眼與心》,劉韻涵,譯,商務印書館,2007。。在他的畫面中,他更加注重直接面對自然時最直接、最原初的感受,他把一切先驗進行“懸置”,他認為:“一種有組織能力的心靈是感性最有價值的共同工作者。”③司徒立:《終結與開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第62頁。并且在他的繪畫晚期,他圍繞家鄉圣維克托山創作了大量的素描草圖、油畫及水彩,雖然數量巨大但沒有重復的構成。我們以他的素描水彩舉例說明。在塞尚的水彩作品畫面中,基于水彩的特性,畫面中夾雜著大量的留白處理,也正由于畫面中大量的空白,我們可以更加直觀地看到塞尚對于建構真實世界的痕跡,這里不是單一的形式構成,而是整個自然中樹木、石塊或者其他物體不斷組合、拆解再組合的運動中的構成。這其實可以看作是一種不斷地反復,逐步認知的過程,也是塞尚在他的繪畫中想要不斷接近“事物本質”追求的體現。
在塞尚的藝術生涯中,他一直想要獲得一個真實世界,所以不離開感覺捕捉真實是他一直的追求。
二、形式構成
塞尚被稱為“現代藝術之父”,固然有其獨到之處,更有甚者在美術史上以他作為藝術的分水嶺。由此可見,塞尚的繪畫完全打破了繪畫的傳統。在所有這些成就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獨到的畫面形式構成。
在塞尚的形式構成中,他的繪畫主題及內容已經完全存在于形式之中。塞尚曾經說過:“視覺形式是現代藝術表現對象,畫的形式蘊含著普遍主體,尋找新的視覺形式成為現代派畫家的使命。”④司徒立、金觀濤:《當代藝術危機與具象表現繪畫》,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8,第38頁。
他一直提倡“在自然中活化普桑”的理念,他追求的是不脫離感覺來尋找真實,并且在繪畫中貼近事物,他用自己的形式構成給出了最佳答案。在離開印象主義之后,塞尚在直面自然時,最早借助的是幾何形式的關聯性,從而轉化到自己的畫面中,這成為他早期的一種形式建構,由此獲得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牢固的聯系。在這一階段,塞尚圍繞靜物展開大量的繪畫探索。
直至繪畫愈發成熟,他的繪畫依舊是以靜物為主要描繪對象。雖然結構的穩固仍是他的主要思索,但在畫面中的幾何式構建開始被一種互相交織的內在秩序所打破,這種內在性的組織語言成為一種歸納性的感性。
而在塞尚晚期的繪畫中,塞尚對于原本混沌與遮蔽的世界的認知從一個點展開,通過反復的比較,筆觸在畫面上不斷地疊加、覆蓋,此時他所追求的幾何形的秩序以及畫面中堅實的色彩建構開始被一種“廢墟”畫的表象所打破,在他的畫面中完全展現出一種萬事萬物的內在秩序,此時畫面的氛圍也變得愈發輕松,并隨著畫面的豐富不斷發生改變,這是一種持續運動的過程,具有空氣的流動感。這樣一個內在的形式構成,也正是他區別于其他畫家最重要的一點,例如普桑,也都是在預先構建好的構圖上進行繪畫,在他們看來通過先驗構成的畫面才能夠被把握。前人的這些理念,在塞尚看來繪畫失去了其該有的真實性,因為自然永遠是在一個運動場中的,本就是一個不斷隱顯的過程,藝術家只有把自己“獻給”這個不斷運動的自然,才能真正達到“天人合一”。
在塞尚的形式構成中,色彩的形式構成也是他繪畫語言的獨到之處。他要“把色彩解放出來,使色彩獲得任其自身理由的純粹應用”①司徒立:《終結與開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在塞尚的這三個階段中,均以靜物或者風景作為其描繪主體。以圖2為例,即使畫面的幾何構成逐步減弱,但是畫面的色彩構成幾乎保持著一致性。塞尚說過,畫色彩的同時也是畫素描,色彩越協調,素描關系就越準確。他用紅色、黃色、藍色、綠色的小色塊,鑲嵌在畫面之中,色彩的反復疊壓產生一種穩定的晶體感,最終幾何形的建筑形式隱藏于畫面的內在秩序中,由此塞尚的繪畫也由一種“形式構成”變為一種“境域構成”②司徒立:《終結于開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第19頁。。

圖2 《圣維克托山》 塞尚/作
三、圣維克托山中的顫動晶體
在塞尚的繪畫中,最具“廢墟”式的表象繪畫,無疑是他晚期回到家鄉圣維克托山創作的一系列繪畫,在這些畫面中,上文所說的形式構成的內在結構秩序,猶如在運動中顫動的晶體一般具有永恒的光輝。
塞尚圍繞圣維克托山創作的一系列繪畫,數量眾多,并且內在的構成都完全不同。在他的《圣維克托山》(如圖3、圖4)的畫面中,盡管最直觀的感受是畫面中的樹木、石塊、建筑物以及山體都有一種破碎之感,畫面上的色塊跳躍嬉戲,物象破碎模糊,猶如一曲混亂的樂章,但內在結構又異常堅硬。紅、黃、藍、綠四種顏色在畫面中疊加并置,形成了一種不斷流變的運動、未凝結的色彩構成。整座山和整個畫面依舊如同是大地上生長出來的一般堅實厚重,在畫面上充斥著變幻莫測的筆觸,無論是遠處的山體還是近處的細小巖體,他們的邊緣線是破碎且不連貫的,但實則是一種不斷反復推敲后的嚴謹的結構體現。

圖3 《圣維克托山》 塞尚/作

圖4 《圣維克托山》 塞尚/作
通過欣賞《圣維克多山》這一系列作品發現,塞尚舍棄了對具體對象的繪制,將其極致凝練,通過筆觸的反復疊加,構建出一個堅不可摧的、堅固的畫面結構,一種自然在不斷流變、不斷遮蔽和顯現反復發生的真實。這些反復疊加的色塊、筆觸,看似是一種由輕微的運動、稀碎的圖案營造出的類似廢墟的表象,實則是一種遮蔽與澄明的同時在場,是他在接近事物本身時的一種反復糾正的過程,也是他在與自然交流時最原初的感受。
在他的這些畫作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他直面自然時,想把自己零碎的感覺變為一種永恒的、堅實的對象。即使畫面中的樹木、石塊和山體已經喪失了其單一的外輪廓線,但依舊堅實且永恒,這正體現出一種反復、質疑的過程,他想讓物體不再受到單一存在的局限,去尋找他們之間的一種內在運動感。這也是具象表現繪畫所說的不確定性和未完成性。這也完成了他所選擇的繪畫面貌,“在自然面前實現感覺”③許江、焦小健:《具象表現繪畫文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第3頁。。最終他的畫面雖然表現類似“廢墟”,實則猶如一個個顫動的晶體,具有永恒的光輝。這種內在的力量,是繪畫的真實性、存在性的體現,同時也鑄就了火山噴發式的輝煌。
四、結語
藝術的發展,自攝影技術誕生以后,逐漸被“圖像”這一形式占據主角。隨著人們思想的變化、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社會意識形態的改變,藝術越來越多地從架上繪畫為中心轉移到觀念至上,并且“繪畫已死”的觀點占據了主流藝術思想的一席之地,繪畫已經在這個時代變得越來越淺薄,喪失了其深度。本文圍繞塞尚繪畫中的痕跡的議題,并通過其畫面中破碎的廢墟的表象,探討繪畫中的真實,并借“廢墟”這一表現背后所具有的反思性,來獲得一種大破大立之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