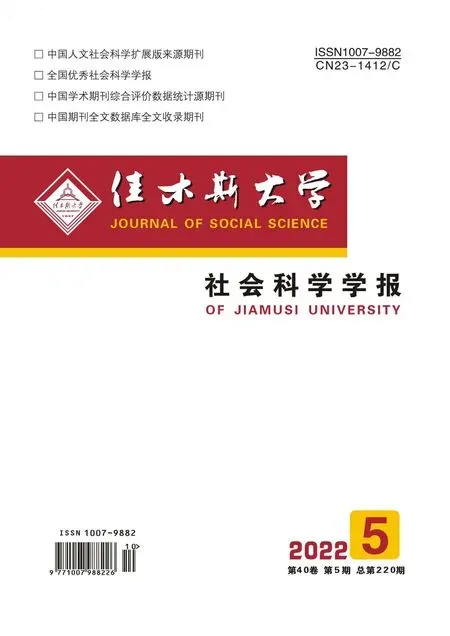收入差距、流動機會感知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響
黃云凌
(閩南師范大學 法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總書記強調,要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進一步理清收入差距、流動機會與國民幸福之間的關系,能夠讓我們提高方向感,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經濟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全體人民。當前,相關研究比較關注宏觀層面收入差距、流動機會對國民幸福感的影響,忽視微觀環境的作用。然而,人們對于外界差距的判斷受到自身所處環境的影響。社區作為個體的生活環境,影響著人們對自己收入差距的感知,進而影響幸福感。因此,本文利用深圳和廈門市的調查數據,來分析和比較不同類型社區中,收入差距、流動機會感知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及差異,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思考與建議。
一、收入差距、流動機會感知與幸福感
關于收入差距、流動機會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理論觀點。第一個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Easterlin提出的,他認為參照群體的收入會影響自己的欲望,參照群體的收入越高,個人對自身收入的要求也越高,現實收入與欲望間的差距就越大,這將降低自身的幸福感。收入差距對于幸福感的這種影響稱為“攀比效應”或“相對剝奪效應”。另一個理論的觀點則與此相反,一些研究發現收入差距的擴大,反而帶來個體幸福感的提高。學者們稱之為“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或者說“示范效應”[1]。在前期理論的基礎上,經濟學家們開始以地區、行業及受教育程度等作為參照群體篩選標準,利用實證數據來檢驗收入差距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并在美國以及歐洲各國不同社會環境下檢驗流動機會的影響[2]。一些學者開始考慮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引入機會公平感、關系信任、社會公正感受等變量的中介效應和調節作用,并開始關注比較對象差異導致的影響[3]。另一些學者研究發現,社區環境會影響居民對收入差距的心態[4]。
當前研究雖然比較全面,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國內外的研究,沒有在不同類型社區環境下,充分討論人們對收入差距與流動機會的看法。事實上,收入差距對居民的影響,有一部分通過主觀認知來實現,人們的主觀判斷受到生活環境的塑造和影響。生活環境不同的人對流動機會的感知存在差異,對流動機會的看重程度也不一樣[5]。基于已有研究,我們提出三個研究假設。根據社會比較理論得出假設1:無論在低收入社區還是富裕社區,與城市里的普通人相比,居民的客觀相對收入和主觀相對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強。社會比較理論的最新研究表明,每個群體在進行社會比較時,參照對象可能不一樣,富裕社區鄰里社會經濟較高,導致此類社區的居民對自己的期待也較高,與城市普通人收入的比較不一定能夠帶來更多幸福感。由此,我們得出假設2:相比富裕社區,在普通社區中,客觀收入差距和主觀收入差距對居民幸福感有更大的影響。其中,主觀收入差距指標中,優勢社區居民對中高階層認同可以帶來更多幸福感,弱勢社區對中低收入階層認同比較敏感。最后,社會階層結構中,富人雖然出于公平正義的天性,可能也會對機會不均感到不滿,但是對其影響相對比較小。對于普通社區的居民來說,周圍的社區生活讓他們看到更多社會流動的努力,對機會公平的要求可能更為迫切。因此,我們得出假設3:相對富裕社區來說,在普通社區中,流動機會感知對居民幸福感有更大的影響。基于以上三個假設,本文利用兩個城市的調查數據,在不同社區環境中,檢驗收入差距、流動機會感知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及差異。
二、數據與方法說明
(一)數據和方法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課題組在廈門和深圳開展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問卷調查。我們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按照經濟特征先在廈門和深圳抽取20個社區居委會,而后每個社區居委會再隨機抽取100戶居民。總共發放20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900份,回收率為95%。已有研究發現,在幸福感研究中,用多元線性回歸法處理的數據結果與ordered probit和logit回歸法基本一致。因此,為了研究結果的直觀性,本文直接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法。
(二)變量測量
自變量方面,本研究將主觀幸福感操作化為“整體來看,你對自己生活的滿意度”這一指標,將滿意度分為“1—10”10個等級,讓被訪者進行選擇,數值越大表示居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越滿意。因變量方面,本文主要將收入差距分為:客觀收入差距和主觀收入差距兩個維度,分別用以下指標來測量:其一,被訪者個人收入對數與所在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對數的差值;其二,主觀收入差距的具體指標為“您認為與本市普通家庭相比,您的家庭收入大概處于哪個層次”,答案分為5個等級:“很低=1、略低于平均水平=2、處在平均水平=3、高于平均水平=4、高出平均水平很多=5”。在我們的調查數據中,流動機會感知被量化為“您覺得一個人通過努力(如進入更好的學校,積累更多經驗等)能否達到更高的社會或經濟地位”這一問題,答案分為5個等級,從1分的“完全不可能”到5分的“非常有可能”。最后,本文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性別、婚姻、年齡、健康狀況、就業狀態、家庭收入及城市的房屋價格。
三、收入差距、流動機會感知對居民幸福感影響的統計結果
本文首先基于總體樣本,建立一個模型討論總體影響,然后在不同社區類型樣本中建立回歸模型(見表1),討論影響差異。具體分析結果如下:

表1 收入差距、流動機會感知對居民幸福感影響的線性回歸模型
首先,在全樣本模型中,在控制人口統計學特征和地域特征之后,收入對數差值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居民幸福感就提升0.082分,但不具有統計顯著性。主觀收入差距和流動機會感知,則具有很強的統計顯著性。從標準回歸系數上看,收入“處在平均水平”的居民的幸福感最強。從回歸系數上看,城市居民對均等機會的感知每增加1個單位,幸福感就提升0.403分。流動機會感知指標的影響力遠超過客觀收入差距。這從側面說明居民對社會流動比較關注。
其次,從不同類型社區來看,收入差距的幾個指標在各個模型中,表現得比較穩健,大部分結果具有統計顯著性。在客觀收入差距指標上,個人收入對數的差值只在普通商品房社區中有統計顯著性,差值每提高1個單位,幸福感增加0.428分。說明,普通商品房社區居民對客觀收入差距更敏感,而對高檔社區的居民來說,與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較并不能帶來心理滿足感。從主觀收入差距上看,中間階層認同對普通社區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最大。我們發現:在老城區、單位社區、保障房社區及城中村中,那些認為自身收入“處在平均水平”的居民的幸福感分別比認為自身收入“很低”的居民高0.524、0.508、0.417及0.422個單位。標準回歸系數反映出一些階層差異,在城中村和保障房社區中,居民對中間階層的認同最大,而隨著階層的提高,影響力急劇下降,“高于平均水平”參照類的影響力較小,并在“高出平均水平很多”這個參照類里出現了缺失值。可見,相對其他社區居民來說,他們并不能從對高收入階層的認同中獲得幸福感。相比之下,普通商品房社區居民則比較認同中上層,認為自身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居民的幸福感比認為自身收入“很低”的居民高0.242個單位。高檔住宅區居民比較認同上層,認為自身收入“高出平均水平很多”的居民的幸福感比認為自身收入“很低”的居民高0.346個單位。
從流動機會感知指標上看,標準回歸系數體現出明顯的社區差異和階層差異,保障房社區、老城區和城中村居民對流動機會的關注度較高,而單位社區、普通商品房社區及高檔住宅區居民對流動機會的敏感性較差。從回歸系數上看,機會平等感知每增加1個單位,保障房社區、老城區和城中村居民的幸福感分別提高0.925、0.524和0.476分,而單位社區、普通商品房社區及高檔住宅區居民的幸福感分別只提高0.335、0.287和0.232分。其中,機會感知對高檔住宅區居民幸福感的影響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通過標準回歸系數的縱向比較,我們發現:在保障房社區、老城區和城中村中,機會感知對居民的影響大于客觀收入差距,在普通商品房社區中,流動機會感知對居民的影響小于客觀收入差距。在經濟上處于弱勢的保障房社區居民、城中村居民更渴望擁有平等的機會,以便他們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階層流動。機會不均對他們的影響和傷害,甚至超過貧富差距。而對單位社區、商品房社區的居民來說,由于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稍高,機會不均可能導致的負外部性有所降低。高檔住宅區居民則不用擔心機會不平等對自身利益的直接損害。
四、總結與結論
本研究使用社區數據來討論收入差距、流動機會感知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及差異。通過回歸分析及不同類型社區的比較,我們發現:總體上,收入差距和流動機會感知都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產生顯著影響。在社區分組檢驗中,收入差距和機會感知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個人收入對數的差值只對普通商品房社區居民有正向影響,且具有統計顯著性。這與研究假設1不符。在主觀收入差距上,認為自身收入“處在平均水平”,給城中村和保障房等弱勢社區居民帶來的幸福感最大,認為“高于平均水平”的影響力非常小。相比之下,普通商品房社區居民則比較認同中上層,高檔住宅區居民比較認同上層。以上結論部分證實研究假設2。這種收入差距帶來的影響差異部分由于階層認同的差異,還有一部分可能源于社區環境的影響。個人生活環境與內在特質之間的互動會潛在改變認知和態度,影響個人幸福感。至于社區環境如何起到中介作用并調節收入差距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最后,在流動機會感知指標上,經濟上處于弱勢的保障房社區居民、城中村居民更渴望擁有平等的社會經濟機會,這個結論直接證實研究假設3。流動機會對強勢社區居民的幸福感的影響小于弱勢社區的居民。因為在強勢社區生活的人們,可能沒有過多突破階層壁壘,向上流動的需求。基于此,政策層面上,可通過社區服務及社區支持,降低貧富差距的影響,提高國民幸福感和獲得感。
[注 釋]
①參照類為“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