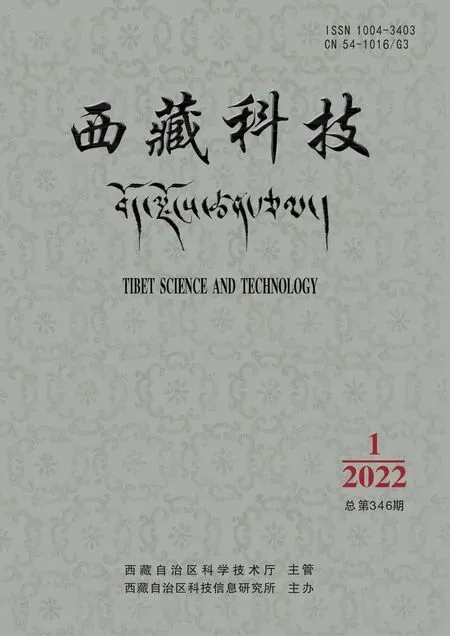胎盤研究在成人慢性疾病和惡性腫瘤研究中的潛在價值*
次旺拉姆 次旦卓嘎
(西藏大學醫學院,西藏 拉薩 850000)
胎盤是一個對妊娠期母親和胎兒的健康乃至對母親和子女終生健康起到重要作用的器官,以至于學者提出了一個概念即“胎盤起源的成人慢性疾病”[1-3]。由于胎盤結構和功能的復雜性以及無創性研究技術的不成熟,目前對于胎盤的研究方法多是類似“驗尸”即胎盤娩出后分子生物學和組織學的研究[1]。另外,物種之間胎盤結構和功能存在較大的差異以至于模型動物的胎盤不能很好地反映人類胎盤整體的情況,因此胎盤成了目前了解最少的一個器官[1,4]。2014 年,Guttmacher 等科學家提出人類胎盤計劃(the Human Placenta Project)以致力于實時掌握胎盤結構、功能和發育情況,探索胎盤相關的威脅母親和胎兒生命健康的疾病以及心血管系統疾病等胎兒成年后的慢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的新方法[1]。本綜述對胎盤形態、胎盤形成過程和胎盤功能進行簡要的介紹并對胎盤研究在預防成人慢性疾病和探索惡性腫瘤治療靶點上的潛在價值進行簡要的分析。
1 正常足月妊娠胎盤形態
1.1 大體形態(gross morphology)
一個正常足月妊娠娩出的胎盤形狀一般描述成圓形,但是在群體研究中發現胎盤的形狀往往偏向于橢圓形[2,5]且胎盤長度和胎盤寬度(胎盤母體面上測量的最長的直徑定為胎盤長與之垂直的直徑定為胎盤寬[6])相差大約2.6cm[2]。研究發現胎盤寬度越短,產婦患子癇前期(preeclampsia,PE)的危險越高或已患PE的產婦癥狀越嚴重[6]。另外,胎盤寬度還與新生兒的出生體重呈正相關[7]。因此,認為胎盤寬的長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胎兒在宮內的營養狀況。對于胎盤重量,文獻報道較重的胎盤意味著較重的新生兒出生體重,但是有學者認為僅測量胎盤重量來評估新生兒生長情況可能有些過于粗淺,因為這樣不能反映胎盤表面積和胎盤厚度各自所起到的作用[7]。此外,胎盤重量與新生兒重量的比值過高和過低都與后期罹患高血壓等心血管系統疾病相關[8]。相對于出生體重,較重的胎盤可能說明胎盤需要代償性增大來彌補運輸功能的不足而相對較小的胎盤則可能表示運輸能力受損從而導致胎兒某些營養素的供應不足[8]。胎盤厚度則反應的是絨毛外滋養層(extravillous tro?phoblasts,EVTs)細胞侵襲母體子宮內膜螺旋動脈的程度[3]。
1.2 組織形態(histomorphology)
胎盤作為一個由母體和胎兒部分共同構成的器官,可分為三層結構,即連接著從臍帶的面由上而下分別為羊膜(amnion)、絨毛膜(chorion)和底蛻膜(de?cidua),其中羊膜和絨毛膜為胎兒部分,而底蛻膜則為母體部分[9]。羊膜是一種半透明的薄膜,分別由與羊水直接接觸的羊膜內皮層、基膜、致密層、成纖維細胞層以及中間層(又稱為海綿層)五層結構構成。絨毛膜由絨毛膜板(chorionic plate)以及由此分支而來的絨毛干(stem villous)、游離絨毛(free villus)和固定絨毛(anchoring villus)構成[2]。靠近底蛻膜的基板(basal plate)形成朝向絨毛膜板的隔膜將胎盤分成多個葉,而一個葉可含有一個或多個小葉[2]。終末妊娠胎盤的功能性單位由游離絨毛外層合體滋養層細胞、絨毛間質和絨毛內胎兒-胎盤毛細血管(fetoplacental capil?lary)內皮構成并且該結構是充滿于絨毛間隙(inter?villous space)的母體血液和游離絨毛內胎兒-胎盤毛細血管內的胎兒血液之間的重要屏障,同時也是母親與胎兒之間進行物質交換的場所[10]。胎兒靜脈血通過兩條臍動脈隨著絨毛逐級分支到了終末絨毛中的胎兒-胎盤毛細血管中,并且在此與絨毛間隙中的母體動脈血進行物質交換之后通過逐級匯合的絨毛膜靜脈,最終到達臍靜脈供應胎兒的生長,而絨毛間隙里的已經進行過物質交換的血液又通過子宮內膜靜脈回到了母體血液循環[9]。正是因為人類胎盤的這個特點即胎盤絨毛合體滋養層直接暴露于絨毛間隙的母體血液中人類胎盤又叫做血性絨毛膜型胎盤(he?mochorial placenta)[8-9]。固定絨毛由細胞滋養層細胞柱以及其周邊的合體滋養層構成而固定絨毛底蛻膜一側無合體滋養層覆蓋,這些具有侵襲能力細胞滋養層細胞侵襲底蛻膜,從而使胎盤固定于母體子宮[8,11]。
2 胎盤的形成
長入母體子宮底蛻膜的固定絨毛頂端即靠近底蛻膜一側是由細胞滋養層細胞分化而來的EVTs 形成[11]。這些具有侵襲性的EVTs 細胞侵襲母體子宮內膜螺旋動脈血管并且取代原有的動脈血管內皮層從而改建母體血管[11]使胎盤組織固定于母體子宮的同時母體子宮血管與胎盤組織的胎兒-胎盤毛細血管建立了聯系。在妊娠早期,游離絨毛具有兩層滋養層結構即外層的合體滋養層和里層的細胞滋養層[11]。盡管存在于絨毛間質的胎兒-胎盤毛細血管在受精卵植入一周后已經開始形成[10,12]并且在妊娠第18~20天在形態學上可以證明血管的形成[13],但是此時母體子宮動脈血管被一群EVTs 細胞堵塞[9,11],因此此時流入胎盤組織的母體血液是非常有限的。妊娠早期母體子宮動脈血管被EVTs 細胞阻塞起到兩方面的保護作用:一方面,這個時期是胚胎形成(embryogenesis)和器官形成(organogenesis)的關鍵時期,因此是胎兒最易受到致畸因素影響的一個時期[10]。這樣的機制有效地限制了經母體血液進入胎兒循環的有害物質從而對胎兒起到保護作用。另一方面,妊娠早期固定絨毛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胎盤與母體子宮內膜的連接較為松動,此時若有母體動脈血液流入可能會引起固定絨毛的脫落。妊娠中期子宮動脈血管已開始改建,母體動脈血液流入絨毛間隙。此時具有屏障功能的合體滋養層開始起到母親和胎兒之間物質交換膜的作用,但是子宮內膜血管的侵襲與改建直到妊娠晚期才完成[10]。在妊娠中期的開始階段,母體血液和胎兒血液之間隔著四層結構,即最外層與母體血液直接接觸的合體滋養層、合體滋養層下面的細胞滋養層、絨毛結締組織以及絨毛間質中的胎兒-胎盤毛細血管內皮[9,10]。直到妊娠第20 周左右,很多絨毛的細胞滋養層變薄甚至消失使得母體血液與胎兒血液之間只剩三層結構[9]。有些絨毛中的胎兒-胎盤毛細血管直接與合體滋養層接觸即形成血管合體膜(vasculo-syncytial membrane,VSM)使局部胎盤屏障厚度只有3μm 左右[9]。在妊娠晚期的開始,具有VSM 的終末絨毛以指數方式增加以增大終末絨毛母-胎之間物質交換的面積直至妊娠終末此區域面積可達13m2[10,14]。
3 胎盤功能
3.1 運輸功能
母體與胎兒之間物質交換的結構基礎是母體血液與胎兒血液之間的胎盤屏障,而這個屏障并非是一個簡單的物理性屏障。對于胎兒生長所需要的營養物質、免疫球蛋白以及對于胎兒的代謝廢物這個屏障具有物質運輸的功能,而對于胎兒生長不利甚至有害的物質則在一定范圍內起到屏障的作用。大范圍內的物質可以通過彌散的方式以及修飾過的彌散方式在母-胎之間進行交換[15]。彌散方式又可分為親脂途徑和親水途徑[15]。胎盤組織具有足夠大的物質交換面積,因此脂溶性物質運輸主要取決于該物質在母-胎血液之間的濃度差或電化學梯度差[15]而親水性物質則受到更多因素的影響,如葡萄糖的運輸還需要葡萄糖轉運蛋白(GLUT,glucose transporter)。
3.2 屏障功能
早在1749 年,Watson 等畸形學家開始研究胎盤對天花的屏障作用[16]。然而,當時的研究主要是在低等動物上開展并且其研究結果主要以描述性而不是以分析性的形式呈現,以至于未能引起當時主流醫學雜志的關注[17]。當時的共識就是胎盤是一個能夠阻擋環境中所有有害物質的完美屏障,因此直到20世紀60 年代對孕婦的處方并沒有做出特殊的限制[17]。隨著“薩力多胺事件”的報道以及對胎盤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員發現胎盤的屏障功能是相對的并且胎盤本身也是某些藥物作用的潛在靶標,如合體滋養層和絨毛間質的胎兒-胎盤毛細血管內皮都有藥物轉運蛋白的表達[18]。轉運蛋白既可以使細胞內一些藥物的濃度升高也可降低細胞內另外一些藥物的濃度,主要取決于轉運蛋白的類型即流出性轉運蛋白(efflux transport?er)和攝取性轉運蛋白(uptake transporter)以及轉運蛋白所在的位置[18-20]。如最早在乳腺癌細胞中分離出來的由ABCG2 基因表達的BCRP(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蛋白是主要表達于合體滋養層頂端膜上的流出性轉運蛋白能有效地限制母血中的藥物向胎兒循環的轉運[18,21]。目前已有報道大量的在胎盤組織上特異性或高度表達的藥物轉運蛋白[22],而探索這些轉運蛋白的功能及其調節機制以研發孕期安全有效的新藥任重而道遠。
3.3 內分泌功能
胎盤除了具有運輸和屏障功能之外,同時也是一個內分泌器官。胎盤缺少神經組織而被學者認為是胎盤的內分泌功能起到母體與胎盤以及胎盤與胎兒之間傳遞信息的作用[9],使母體的生理適應妊娠期胎兒的生長。胎盤能夠分泌100 多個肽類和甾類激素,如合體滋養層細胞合成的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胎盤生長激素(pla?cental growth hormone,PGH)和人胎盤生乳素(human placental lactogen,HPL)等[9]。妊娠早期就有hCG 的合成,在妊娠第8 周左右hCG 的合成達到高峰。hCG 作為黃體生成激素(luteotropin hormone,LH)的超激動劑使月經黃體轉變為妊娠黃體,從而延長黃體的促孕功能[23]。自妊娠第12周至第20周左右在母體血液循環中PGH 水平升高直至妊娠終末完全取代垂體生長激素[23]。研究發現胎兒生長受限的母血中PGH 水平是下降的,認為PGH能通過調節母體代謝來保證胎兒的營養[23]。HPL 由合體滋養層合成并釋放到母血和胎兒血中[9]并且自妊娠第6周母血中可以檢測到HPL[24]直至妊娠第30 周左右母血HPL 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遠超過其他蛋白類激素的分泌量[24-25]。HPL 主要通過調節中間代謝和刺激胰島素樣生長因子、胰島素和肺泡表面活性物質等的產生來調節胚胎發育[9,25]。
3.4 免疫調節功能
盡管胎兒作為一個“半同種異體移植物”并且胎兒來源的合體滋養層直接與絨毛間隙中的母體血液接觸,但母體并不會對胎兒產生免疫排斥反應。一般來說,母體對胎兒的免疫耐受主要是以保證母體整個免疫系統不受抑制的前提下通過對母體和胎兒之間物質交換場所處的免疫細胞的限制和調節等途徑來實現的,其可能的途徑有:(1)母體來源的底蛻膜免疫細胞中自然殺傷細胞大約占70%而胎盤EVTs上表達的人類白細胞抗原G(human leukocyte antigen-G,HLA-G)通過與自然殺傷細胞的抑制性受體結合使胎兒來源的滋養層細胞免受母體自然殺傷細胞介導的細胞溶解作用[26-28]。(2)底蛻膜處沒有淋巴系統并且表觀修飾抑制了底蛻膜的T 細胞的化學引誘物[11,29];(3)研究發現合體滋養層分泌物表達TRAIL(TNF-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和Fas 從而能介導白細胞的凋亡[30]。(4)文獻報道其他抑制T 細胞的途徑如B7蛋白途徑、Galectin1途徑和IDO酶途徑等[11,31]。
4 胎盤研究在預防成人慢性疾病中的潛在價值
胎盤是一個可塑性較強的器官,具有相當大的結構和功能的適應能力,能夠自行減輕營養不良、毒素或低氧等不利因素對胎兒造成的不良影響。然而,當這些不利因素的作用超過胎盤的適應能力時,胎兒在宮內生長的環境受到干擾從而影響胎兒重要器官的結構和功能[2]。從受精卵植入到胎兒分娩過程中尤其在胎兒各器官和各系統形成的關鍵階段,基因表達、細胞分裂和細胞分化若是受到不利因素的干擾就會影響關鍵器官的形成對胎兒造成終身性的損傷,因此學者將這個過程稱之為“發育性編程(developmental programming)”[2]。這種改變使胎兒容易患上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甚至成年以后才表現出明顯癥狀和體征的各種疾病,如心源性猝死可能是由于EVTs 細胞侵襲母體子宮內膜螺旋動脈的深度不足而引起胎兒營養不良從而使胎兒在宮內自主神經系統發育受限所致[3]。目前研究發現的與宮內生長相關的成人慢性疾病有高血壓、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2]以及二型糖尿病和胰島素抵抗等內分泌疾病[32]。這種宮內“發育性編程”對成人健康的影響最先由David Barker 提出[33]。David Barker 對胎兒宮內生長情況與成年后慢性疾病相關的開創性研究成果為全面認識成人慢性疾病提供了新思路。因此,積極探索孕期胎盤功能檢測技術以實時監測胎兒宮內生長情況以及研發安全有效的應對措施將在預防成人高血壓等心血管系統疾病和糖尿病等內分泌系統疾病,減少慢性疾病家庭和社會負擔具有重要的作用。
5 胎盤的類惡性腫瘤特征及其在惡性腫瘤研究中的潛在價值
胎盤滋養層細胞和惡性腫瘤細胞在細胞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上存在某些相似性,如侵襲正常的組織和逃逸宿主免疫反應等[34-36]。另外,一些特異性表達于胎盤組織的基因在某些惡性腫瘤組織中表達,如胎盤組織特異性表達的PLAC1基因在前列腺癌、卵巢癌和乳腺癌等惡性腫瘤組織中表達且認為該基因是前列腺癌免疫療法的潛在靶點[37-38]。在物種之間比較發現,孕期形成胎盤的哺乳動物尤其是形成血性絨毛膜型胎盤的哺乳動物具有最高的惡性腫瘤發病率且孕期不形成胎盤的哺乳動物中目前并沒有發現轉移性實性腫瘤(metastatic solid tumor)[34-36]。基于以上發現學者甚至提出了“惡性腫瘤的轉移性是胎盤在進化過程中獲得侵襲子宮壁能力的代價”的觀點[34-36]。研究胎盤組織EVTs 細胞侵襲母體子宮內膜螺旋動脈、合體滋養層細胞逃逸母體免疫反應等類惡性腫瘤組織特征及其分子機制將會為進一步揭示惡性腫瘤發生機制以及為研發惡性腫瘤精準治療藥物提供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