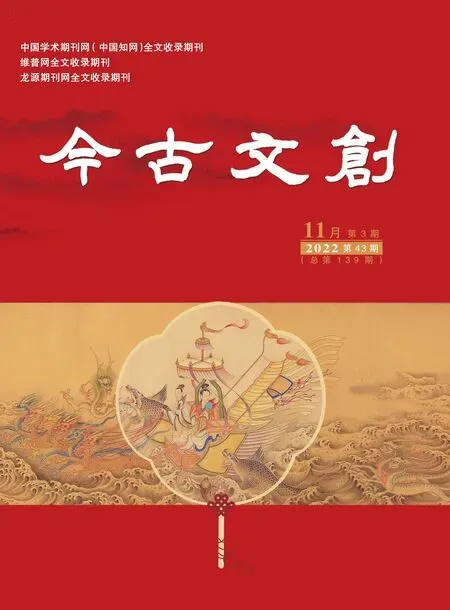索爾·貝婁對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反文化”的態度
——以《賽姆勒先生的行星》為例
◎沈袁煦 方澤曦 孔易安
(蘇州科技大學 江蘇 蘇州 215000)
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反文化”有其存在的獨特的文化價值。其中諸種過激反傳統文化行為的背后,蘊含著一定的文化解放的積極意義,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至今還揮之不去的消極影響[1]。在《賽姆勒先生的行星》一書中,作者索爾·貝婁以賽姆勒先生為傳聲筒,表達了對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的多重態度和思考。而目前國內外同類課題研究仍舊有一些急待豐富的空間,基于此,本項目組通過研讀《賽姆勒先生的行星》以及大量的相關權威資料、研究索爾·貝婁本人和他的其他作品,最終得出系列理論成果。
一、社會失范與信仰瓦解的“反文化”
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在美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20世紀六十年代上半期,黑人平權運動高漲,在20世紀五十年代消亡的個人主義重新膨脹[2]。憤世嫉俗的青年人,以其獨特的方式,或激進、或曲折地,向社會表達他們的不滿與希求。這股瘋狂的“反文化”浪潮席卷當時整個美國社會,為當時的世界帶來了新鮮的思想和主張,同時也沖擊著傳統價值體系,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失范與信仰瓦解問題。在這場“反文化運動”中,涌現出一群乖僻的嬉皮士,他們將消極頹廢的批判指向整個傳統社會。嬉皮士們試圖以“感官滿足、人性回歸和無政府生活方式”等極端方式反抗主流價值觀,實現自我解放和個性自由[3]。嬉皮士們所倡導的“性解放”運動在整個西方社會引起強烈反響;與之相伴而來的,還有毒品泛濫與物質享樂。過度的自由瓦解了人們的道德底線,暴力犯罪變得司空見慣,法律制度在這場“暴風雨”中茍延殘喘。
《賽姆勒先生的行星》正是以此為背景,通過敘述主人公阿特·賽姆勒在三天之內經歷的光怪陸離的事件,體現了這位波蘭籍猶太人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洞察與哲思。經歷二戰大屠殺、痛失愛妻、從洞穴和死人堆里僥幸逃生,這位獨眼老人突然掉落到一個崇尚“自由、博愛、平等、通奸”的“原始世界”。老賽姆勒被隔離在這個“嶄新的”世界之外,試圖以正常的理智重建崩壞的信念,尋找修復這顆星球的可能。全書以賽姆勒先生目睹黑人扒手行竊為開端,開篇便呈現出紐約市一副“腐化墮落”“野蠻粗鄙”的危機畫面。而后賽姆勒更是經歷了一系列瘋狂病態的秩序瓦解:遭到黑人扒手展露生殖器的威脅;參加演講時受到青年學生諷刺攻擊;女兒蘇拉偷走博士手稿;侄子格魯納病逝。老賽姆勒既是瘋狂事件的目擊者,也是這些瘋狂因子的容器,怪癖的人類不避諱向賽姆勒袒露自己的瘋狂行徑:嘮叨的老頭布魯克迷戀上了女人臂膀,哭訴自己的癖好;侄孫華萊斯為了挖掘其父親所謂的財產,致使水管破裂、房屋被淹,又向賽姆勒坦言自己“闖出爸爸為他安排好的未來”的“革命想法”[4]。除了記錄當下困境和悲劇,賽姆勒深刻關切著人類的命運,對歷史與未來懷有獨到的見解,同時也強烈呼喚道德秩序的回歸。
盡管在賽姆勒先生和索爾·貝婁身上都可以看到共有的猶太性與戰爭經歷,但將兩者簡單地畫上等號是不負責任的,同樣,也不能忽略隱含書籍作者與作家索爾·貝婁之間的差異。不過事實上,作家和隱含作者很難剝離開來。文論家申丹提出,“隱含作者”是相對的概念,來自于文本,讀者在作品表達本身中建構作者形象[5]。一定程度上,賽姆勒是一個“可靠的敘述者”,即敘述者的思想意識和價值判斷與隱含作者相差無幾。因此,貝婁筆下的賽姆勒先生暫且可以視作是其觀點的傳聲筒。作為“反文化運動”的親歷者與旁觀者,貝婁多重而獨特的態度,具有深刻的探究意義與啟發性。
二、索爾·貝婁的多重態度
以賽姆勒先生為傳聲筒,《賽姆勒先生的行星》體現了索爾·貝婁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思考和對命運出路的探索,而人們因此也從某種程度上得以窺見貝婁對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反文化”現象的多重態度,即深切關懷、疏遠、不贊成和批判抨擊以及仍懷希望。
(一)深切關懷
誠然,索爾·貝婁以嚴肅冷峻的筆調批判了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社會充斥著的暴力、物欲縱橫、性瘋狂和道德瓦解,他的內心深處仍抱有對人類社會、人類文明的期冀與深沉的愛。貝婁在展示混亂不堪的美國圖景的同時,通過主人公的所思所言表達了重構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愿望以及不離不棄的深切人文關懷[6]。他筆下的賽姆勒冷眼旁觀著這席卷西方世界的瘋狂和“如今被視為是正當的懶散、愚蠢、淺薄、混亂、貪欲與無秩序”[7],卻并沒有倒向虛無主義,也從未放棄對解決當下人類精神困境的出路的探索。貝婁對當時道德瓦解的混亂現象的抨擊是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式的,寄痛惜與熱忱于批判中。換而言之,批判的目的絕非批判本身,而是為了謀求修復地球與重建人類文明的可能。他對這個地球,對生存在這個行星上的人類并未絕望。逃離地球,飛往月球并不是他的選擇[8]。在談論人類命運現狀與未來的時候,他堅定地相信人性的力量、文明的力量和傳統價值的力量,而這也正是構成賽姆勒選擇“留在地球上”的理由。貝婁對人類整體生存狀態和命運的關注以及對精神困境的探討充分體現了他深切的人文關懷和對重塑西方文明的期冀。
(二)疏遠、不贊成和批判抨擊
1.疏遠、不贊成
在主觀方面,索爾·貝婁對于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反文化”的不贊成主要因為他的傳統道德認知與當時社會現狀相去甚遠。在賽姆勒先生的視角下,他對社會傳統道德長期以來的認識與認可導致他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反文化”對其思想的“入侵”。由于其態度定式,賽姆勒先生對于新事物、新思想的出現,持慣有的閉鎖與排斥心理。而他所秉持的一些傳統道德觀念與價值觀念,與20世紀六十年代在青年群體中所流行的開放觀念并不協調同步,甚至可以說是背道而馳,而這種差異與相悖也引起了他對于“反文化”態度的發展變化。
在客觀事實中,不贊成的態度主要是因為傳統文化與“反文化”之間差異之大與變化之迅猛令貝婁始料不及,也只有青年群體能夠跟得上這次“反文化”席卷而來的浪潮并成為引領浪潮的主力軍。而以賽姆勒先生為傳聲筒的貝婁本人,既無法及時對新出現的文化作出及時的了解與反應,同時,他的固有認知與傳統價值觀念也讓他對于這場浪潮的到來感到無所適從,甚至容易從了解之初就產生先入為主的排斥心理。
綜上所述主客觀兩方面原因,賽姆勒先生的個人經歷與其所處的文化環境變化之快、之大都對其多重態度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2.批判抨擊
貝婁對于伴隨著“反文化”一齊到來的一些其他社會現象抱有批判的態度,甚至對其進行猛烈抨擊。具體表現在《賽姆勒先生的行星》一書中的三個方面,分別是泛濫的暴力、物質貪欲與性解放運動。
泛濫的暴力首先集中表現在黑人扒手這一形象上。穿著高貴的黑人扒手在公車上偷竊,被賽姆勒先生發現之后將賽姆勒先生逼至角落,向他展示自己的生殖器,這對此時身殘體弱且年歲已大的賽姆勒先生來說,無疑是一種居高臨下的炫耀甚至一種較為粗暴的挑釁與直接示威。黑人的一舉一動均帶有高出賽姆勒一等的權力感和優越于賽姆勒的陽性力量感,他在賽姆勒面前由被凝視到主動展示陽具的轉變正如黑人由被歧視、被剝奪話語權,到打破種族隔離制、通過民權運動發出自己的聲音。在這種沉默卻令人窒息的示威之下,賽姆勒先生不僅受到了視覺上的刺激,伴隨而來的更是一改往日形象的黑人扒手反凝視的抗爭行為在觀念層面上對賽姆勒先生產生的巨大沖擊[9]。書中同時也有關于對街頭暴力熟視無睹甚至推動矛盾激化的警察和對賽姆勒先生惡語相向的青年們的描寫,他們以不同方式對賽姆勒先生施加了暴力,使賽姆勒先生對于“反文化”的態度逐漸變得明晰,其批判的立場逐漸變得堅定。
物質貪欲主要體現在賽姆勒先生的親屬身上。他的侄孫華萊士在與他的談話中提出了對父親格魯納的不滿以及對得到父親存款來發展事業的渴望,他甚至想通過打破水管來獲得那筆錢;而他的女兒蘇拉更是兩次偷走了拉爾博士的論文手稿并將其藏匿起來。對他們行為的評價,用原文的話來形容,“這也是當代的特點——無法無天”。貪欲和庸俗被視為正當——把往日受到人們尊敬的東西翻了個個兒[10]。
至于性的解放,則可從青年一代的代表蘇拉與華萊士平日的社交生活中窺見一斑。小說中,在談到新一代女性的放蕩不羈時,賽姆勒先生直言“在她們厭惡權威之際,她們對誰都不愿意尊敬,甚至連她們自己都不尊敬”[11]。在賽姆勒先生與華萊士父親的交談中,賽姆勒先生提到蘇拉“看到一個女人以過多的方式與過多的男人胡搞……她的雙眼全顯得房事過度”,華萊士更是在家中支持的事務所上班時玩弄速記員的乳房。
在面對充斥著暴力、貪欲與性的時代環境中,貝婁的傳統價值觀念受到了身邊人的這些行為的沖擊,他對“反文化”的認知與情感在不斷更新,逐漸蒙上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
(三)仍懷希望
那是一個“你打開一扇嵌著寶石的大門,出去就置身在腐化墮落之中,從高度文明的拜占庭的奢侈豪華,一下子就落盡了未開化的狀態,落進了從地底下噴發出來的光怪陸離的蠻夷世界”[12],當時社會面臨精神墮落和人道主義危機,印度科學家拉爾博士已經對這個人類僅有的家園失去了信心,“厭惡透了地球”,將希望寄托于月球,主張“向外出發,乘坐人類的飛行器向月球方面駛去”;而賽姆勒先生雖然對這充滿暴力、混亂、腐敗的世界進行批評諷刺,但是他并沒有對此懷有消極態度,他認為人類還有挽救的余地,地球還有修復的可能。索爾·貝婁借助賽姆勒表達了對重建人類文明的希冀、對拯救失范社會的希望[13]。
賽姆勒先生對拉爾博士所說的“人類正在把自己吃掉”的“實際情況”提出質疑,認為“人有一種本能,不愿跳進死的王國里去”,人類擁有更多的還是生的欲望而不是死,并且“除非采取一種普遍的自我毀滅的行動,人類是不能了結自己的”。由此可見,貝婁對地球上的人類還是抱有希望的,認為他們本著“一種生存意志的道德觀念”不會等待接受“死的王國”的“最后一次爆炸”,深信他們不會摧毀自己;并且即使處失范和狂熱之中,仍有那么一群人,“他們乘坐公共汽車到工廠去;他們開設店鋪;他們打掃;他們包扎;他們洗滌;他們安裝;他們照料;他們計算;他們操作著計算機。每一天、每一晚都是這樣。而且,不論內心多么激動反抗,多么驚恐絕望或是疲憊不堪,他們總前去工作,乘電梯上上下下,在辦公桌前面坐定,坐在方向盤后面,操作機器”[14]。在混亂中,他們出來尋找工作,他們承擔責任,他們尊重秩序,他們是重建人類文明的希望所在。人類還有救,我們這個星球還有修復的可能[15]。
這或許也是賽姆勒先生不愿意逃離地球、去往月球的原因,制約人類發展的不是星球,而是人類本身,他只是在等一個時機,“當我們有了一個住滿了圣人的地球,而我們又一心想著月球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登上航天機器,飛上天去了……”[16]他在等地球上“住滿了圣人”,這意味著當人類不再瘋狂、不再極端,當社會的“天花板”重建時,“月球計劃”便可實施了。這也是貝婁的希望,他希望狂熱愚蠢的人類可以醒悟,希望混亂失范的社會可以被拯救。
三、結語
本文以美國作家索爾·貝婁的作品《賽姆勒先生的行星》為典型文本,通過文本中呈現的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特征與社會特征,研究索爾·貝婁對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反文化”的多重態度,并結合《賽姆勒先生的行星》對20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作出客觀、創新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