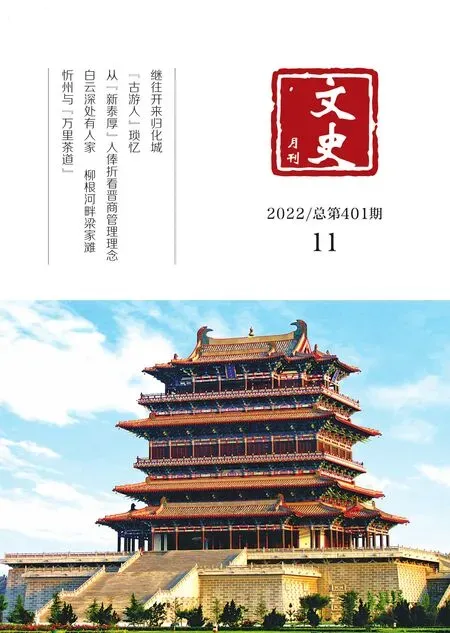“古游人”瑣憶
◇ 張小榮
2017年1月18日,家父張頷離我們而去,至今已五年多了。回想過往,記憶之零星散葉,每每念及,堪堪如畫,心底充滿敬佩與溫存。茲將部分回憶摘錄如下,與親友共同緬懷。
一、不愁工作
家父說:“兩千年前,在戰國時期,我也能找到一份工作,因為認識戰國文字。”也因此,人稱家父“古游人”。
二、樂趣多多
家父曾對我講:“我的工作研究是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天文學及古音韻學。對寫毛筆字、作詩、刻章,只是樂趣而已。”實際上他的愛好還有許多,比如打乒乓球、踢毽子,但最喜歡的還是音樂。我小的時候,家父因工作調動,全家由省委遷至文廟,住在大成殿右側偏后的四合院內。夏天,全家人在院中老榆樹蔭下乘涼,擺起方桌,倒上茶水,家父則彈起月琴教幾個子女唱歌,記得有《漁翁樂陶然》《三弄》等幾首。
三、不失禮數
家父心善、慈祥,但也有嚴肅的一面,若說錯話辦錯事,他的批評很是嚴厲。一次我接了個電話,不客氣地掛了,他問是誰打來的,我說:“有人要你給他寫字,可連你的名字都說錯了。”他呵斥道:“不論他是誰,都是找我的,你不應對人家失禮,好像咱家不懂禮數似的。你若不答應人家可婉言謝絕。再不可這樣!”
四、儉以養德
家父一生勤儉,而且要求子女們生活上要“儉”,行為上要“檢”,即要勤儉,檢點。能吃的不挑,能用的不扔。還用猜燈謎的方式講“儉”字:“一人站立一人臥,兩個小人地下坐。家中還有一兩口,你說日子怎么過?”寓教于樂。
五、喜贈聯語
我兒子結婚時,家父將小夫妻叫到身旁,送給他們一副對聯作為結婚紀念物:“天地和而后雨澤降,夫婦和而后家道昌。”小夫妻有了一對雙胞胎女孩,過“百天”時家父又寫了一副對聯:“重孫百日家庭旺,曾祖耄年福壽長。”

張頷寫給孫兒孫媳的對聯
六、寓教于典
2015年4月18日,全家人搬進萬水瀾庭小區新家,看到自己的臥室與舊家陳設相差無幾,家父自言自語:“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七、書不離身
家父終生手不釋卷,有躺著看書的習慣,一手捧書,一手執筆,邊看邊批注,眼困了點滴眼藥水,休息養神后再繼續。每遇不識之字或不解之詞,當即查閱典籍,從不輕易放過,由此也教我查閱《中文大辭典》。
八、樂見“雪花”
九十大壽后,家父思維顯衰,行動緩慢,早晚穿衣脫衣困難,行動依靠助步車,或依墻扶柜。我每天端水喂飯,早晚幫他更衣解帶,十分了解他的心思。那年一冬未雪,天干氣燥,為調節家父情緒,我買了紙雪花貼于窗戶,家父臉上頓時洋溢起開心的笑容。
九、二十五孝
家父平時坐藤椅,頭靠墻,我便買了個氈質汽車腳踏墊掛在墻上,以解決冷硬問題,家父說可在“二十四孝”中補一孝。
十、仁義胡同

張頷的書法作品
家父生前經常說起介休城“jia ban de nao huo huo”,實際上是“夾扁腦袋巷巷”,是一條兩家蓋房子留下的窄巷,在廟底街郭家巷附近,東西向,只能走一個人,二人對走就得側身而過。他童年上學天天經過此巷,后來此巷叫成了仁義胡同。這里面有個緣由,說的是關于“張尚書回信”的故事,兩戶人家為蓋房發生爭執,一方給在朝廷任職的尚書寫信,希能壓制對方。尚書回信:“千里家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見信后感觸頗深,造墻時讓出一線,對方因此也讓出一線,從此這條小巷叫成了仁義胡同。
十一、兩個地下
家父說:“解放前我是搞地下工作的,解放后我還是搞地下工作的。”我十分不解:“解放后怎么還在‘地下’?”他哈哈一笑:“考古挖掘古墓不就是搞地下的工作嘛。”
十二、公私分明
很多年前去四川出差,回來后有人問家父:“你也不去峨眉山玩一趟,多好的機會。”他說:“空余時間是有的,但此行沒有安排上峨眉山的工作,我不能去,如去了那不是占國家的便宜嘛。”
十三、險成竊賊
家父在文廟大成殿掃地,看見自家的自行車支在門口,便順手推回家中。一進門就喊:“誰騎了車子,放在大成殿也不騎回來!”家母見不是自家的,趕緊讓哪兒推的放到哪兒去。當時家父是被監督勞動改造對象,隨時都有人監視,防止他搞破壞活動。因為他不會騎自行車,推車的動作就讓人產生了懷疑,幸虧能說得清,否則便成了竊賊。
十四、超強記憶
2016年,柯文輝先生來家,家父問他多大年齡,他說83 歲。家父隨口說了段童謠:“一個老漢八十三,每天吃飯把門關;蒼蠅含走一顆米,一追追到紅樓山;紅樓山上有座廟,搗動鐘鼓問老道;老道說你該破財,氣得老漢嗨嗨嗨。”家父時年96 歲,還能記得兒時的歌謠,但口齒已有些含混不清。
十五、內外有別
姚國瑾先生到家中探望,正好趕上高增德先生要走,家父相送。高說:“不送了,又不是外人。”家父順口說:“你不是‘外人’,但也不是‘內人’。”
十六、天天向上
家父身體不好,不常出門,但是常有朋友們前來探望聊天,內容多是文字、書刊、書法方面的事,有人說近期有某某書法展,有錯字、錯筆,老爺子說:“(這些人)只想天天向上,卻不知好好學習。”
十七、英雄氣短
2011年某一天,韓石山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來看望家父,聽到家父喘氣緊迫,順口問:“您氣短嗎?”家父說:“我是英雄。”“怎么是英雄呢?”家父說:“英雄氣短嘛,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十八、豬肉蓋章
20世紀90年代末,文廟南墻外照壁下形成了收藏品市場,每到周末擺地攤買賣各種古董玩器的人很多。家父常出去看看,只是欣賞,看到好的他也買不起。一次看到地攤上擺的一幅古畫,真品贗品不說,只見畫面上蓋了很多印章。隨口說了一句:“怎么在畫上亂蓋章,可惜了畫。”擺地攤的說:“你不懂。”家父說:“那也不能拿畫當檢疫過的豬肉吧。”
十九、張頷高壽
“文化大革命”時期上行下效,文管會貼出“打倒劉靜山張頷高壽田”的標語。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風吹雨淋,十個字先被風刮掉三個,剩下了“打倒張頷高壽田”,再后來大風又把“打倒”和“田”字也刮掉了,僅留下“張頷高壽”。不知道確有其事,還是家父冷幽默,但確是家父親口所講。
鏈 接:
張頷,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自幼家境貧寒,但因酷愛文史學科,博聞強記,苦學成才,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兼考古研究所所長。其研究領域廣涉古文字學、考古學、晉國史及錢幣等,先后出版了《侯馬盟書》《古幣文編》《張頷學術文集》等著作,其作品把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融為一體,在中國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張頷先生在詩文、書法、篆刻方面也頗有造詣,在國內外都享有極高的聲譽。(來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