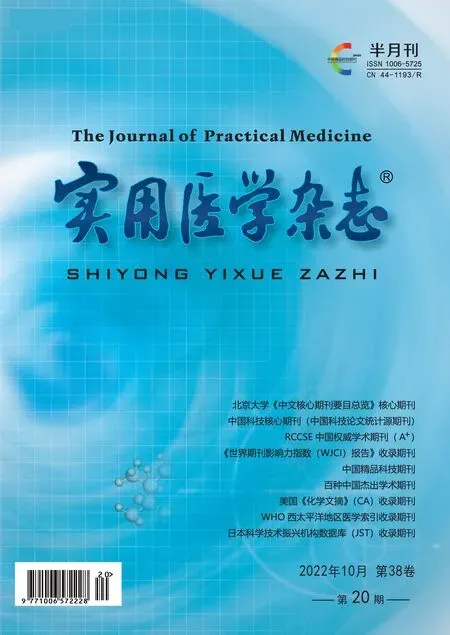乳腺癌疫苗的現狀與展望
史福軍
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普通外科中心乳腺外科(廣州 510280)
目前臨床上化療、靶向治療、內分泌治療三者已經構成了乳腺癌非手術治療的基石,其總體治愈率也有了顯著提高。但是目前的治療手段對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治療效果不佳。腫瘤疫苗療法的出現有望解決這個臨床難題。本文旨在結合目前乳腺癌疫苗的臨床研究結果,對其發展前景進行評述并為開發治療或者預防效果更好的乳腺癌疫苗提供參考。
乳腺癌是一種起源于乳腺導管上皮的惡性腫瘤。根據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報道,自2020年以來乳腺癌已經成為全球發病率第一位的癌癥。在美國,2022年估計新增乳腺癌病例290 560例,其中女性患者287 850例,占女性新增癌癥總數的31%,在女性新增癌癥中排第一;2022年預估乳腺癌死亡病例43 250例,占女性新增癌癥相關死亡病例的15%,在女性新增癌癥相關死亡病例中排第二,僅次于肺癌[1]。根據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體(progesterone receptor,PR)、Ki67和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這四種因子的表達水平,乳腺癌可以分為luminal A型、luminal B型、HER2過表達型以及三陰型乳腺癌(TNBC)。HER2受體屬于EGFR家族受體,在肺癌、乳腺癌、卵巢癌和腎癌等多種癌癥的發病機制中發揮關鍵作用。EGFR家族包括4種受體:HER1(EGFR)、HER2、HER3和HER4。有研究發現,HER2受體在大約20%~30%的乳腺癌患者中過度表達。因此,基于HER2的靶向治療,研究人員開發出了具有抗腫瘤特性的單抗。曲妥珠單抗是FDA批準的第一個推薦用于治療HER2陽性轉移性乳腺癌的單抗。它通過多種機制發揮抗腫瘤作用,如誘導細胞凋亡、誘導細胞周期停滯、抗體依賴的細胞介導的細胞毒作用(ADCC)、抑制HER2胞外區的脫落以及抑制下游信號轉導通路等。單抗治療乳腺癌是一種有效的治療策略[2],但它有其自身的缺點,如費用、治療持續時間和頻率、耐藥性和耐受性等。此外,一旦腫瘤在治療過程中發生基因突變,便更加容易轉移并產生耐藥性[3-4],從而影響患者預后。
腫瘤疫苗療法可以利用癌細胞的特異性抗原,使免疫系統長期激活,特別是由于機體存在長時間的免疫記憶,可以降低癌癥復發的幾率。由于腫瘤疫苗獨特的作用機制,其有望解決晚期轉移性乳腺癌這一臨床治療難題。另一方面,疫苗不需要頻繁接種,而且從歷史上看,疫苗比化療相對安全。在乳腺癌類型中,HER2陽性和三陰型乳腺癌(TNBC)亞型免疫原性最強[5],對于這些類型的患者,研究人員認為可以通過制備相應的疫苗來激活患者的免疫系統。盡管目前總體進展緩慢,這一領域的臨床轉化面臨挑戰,但臨床前研究為癌癥疫苗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因此,開發適用于臨床的乳腺癌疫苗對于乳腺癌的預防和治療都有重大意義。
1 乳腺癌相關多肽疫苗
多肽疫苗的作用機制主要有:首先,在疫苗注射后相關多肽與抗原提呈細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的Ⅰ類和Ⅱ類人類白細胞抗原(HLA)結合,形成多肽-HLA復合體;其次,CD8+T細胞能夠識別多肽-HLA復合體并產生特異性細胞毒性淋巴細胞(CTL);最后,CTL特異性識別表達抗原的腫瘤細胞,然后釋放穿孔素和細胞因子來溶解腫瘤細胞[6]。與其他類型的疫苗相比,多肽疫苗有其獨特的優勢,如合成容易,可以應用生物信息學等方法來篩選具有腫瘤相關抗原(tumor-associated antigens,TAAs)的MHCⅠ類限制性多肽表位的候選氨基酸序列,并且可以對這些候選抗原表位進行抗原特異性免疫反應的實驗篩選。到目前為止,在乳腺癌多肽疫苗研究中的大多數多肽抗原來源于HER2蛋白和其他HER2衍生多肽[7]。與腫瘤特異性抗原不同,TAAs為在腫瘤和正常組織中普遍表達的自身蛋白,但是它們在腫瘤細胞中異常表達[8]。由于HER2在人正常組織也有表達,因此機體已經對其產生了免疫耐受。但是,由于HER2具有高免疫原性,部分乳腺癌患者仍能對HER2產生免疫反應。除了選擇合適的抗原以外,多肽疫苗的效果還與佐劑的選擇有關,佐劑的主要作用是確保啟動T細胞的APC有足夠的共刺激作用[9]。
目前針對HER2的多肽疫苗主要有E75(p369-377)、GP2(p654-662)和AE37(p776-790)。E75是一種來源于HER2受體的9個氨基酸的多肽,氨基酸序列為KIFGSLAFL,它能與HLA-A2結合,從而激活CTL。目前已經有臨床研究證實了E75的有效性和安全性[10-11]。在一項涉及187例淋巴結陽性和高危淋巴結陰性(≥T2,3級,HR-,IHC或FISH擴增>2.0的HER2 3+)乳腺癌患者的Ⅰ/Ⅱ期臨床試驗中,通過聯合使用E75和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結果表明使用E75的患者5年無病生存率(DFS)為89.7%,使用安慰劑的患者的5年無病生存率(DFS)為80.2%[12]。隨后在一項Ⅲ期臨床試驗中,使用佐劑GM-CSF與E75對758例HER2低表達(IHC 1+/2+)淋巴結陽性的乳腺癌患者進行了評估,結果表明在觀察組和對照組之間DFS沒有差異[11]。
GP2是一種來源于HER2(654-662)跨膜區片段的免疫原肽,是一種9個氨基酸的多肽疫苗,其序列為IISAVVGIL,它已被證明能與HLA-A2結合并激活CTL[13]。一項Ⅰ期臨床試驗表明聯合GMCSF的GP2對淋巴結陰性的乳腺癌患者有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14]。Ⅱ期臨床試驗在180例淋巴結陽性和淋巴結陰性乳腺癌患者(HER2 IHC 1+~3+)中進行。該研究表明觀察組與對照組的DFS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該研究證實了GP2疫苗的安全性[15]。
AE37是一種由15個氨基酸殘基組成的多肽,來源于HER2的細胞內結構域。與E75和GP2不同,AE37主要誘導CD4+T細胞活化[16]。一項Ⅰ期臨床試驗證明AE37和GM-CSF聯合給藥的安全性,同時可以成功引發HER-2/neu的特異性免疫應答[17]。在一項涉及到298例淋巴結陽性和高風險淋巴結陰性乳腺癌患者的Ⅱ期臨床試驗中,對觀察組和對照組的處理措施分別為AE37聯合GM-CSF以及GM-CSF單獨給藥[18]。其研究結果表明在總體患者中觀察組5年DFS為86.8%,對照組為82.0%,結果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1)。但是在TNBC患者(HER2 IHC 1+/2+、激素受體陰性)中,觀察組DFS為77.7%,而對照組為49.0%(P=0.12),這表明AE37疫苗可能對低HER2表達腫瘤患者具有臨床療效。
人端粒酶逆轉錄酶(hTERT)在人類癌癥中幾乎普遍存在過表達,對腫瘤發生發展有關鍵作用[19]。一項研究[20]對19例轉移性乳腺癌患者接種了hTERT肽疫苗,其中9例出現hTERT誘導的特異性CD8+T細胞免疫應答,且9例免疫學高應答者的中位OS更長。
2 乳腺癌相關蛋白質疫苗
與多肽疫苗相比,以完整蛋白(HER2胞內或胞外區域)作為疫苗可以避免特定的HLA限制,因為其同時包含HLAⅠ類和Ⅱ類表位。已有研究證明蛋白質疫苗可以引發特異性免疫。在一項涉及29例HER2過表達乳腺癌或卵巢癌患者的Ⅰ期臨床試驗中,給患者接種了HER2胞內結構域(ICD)蛋白疫苗(p676-1255)以及GM-CSF[21]。研究結果表明HER-2/neu ICD蛋白疫苗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同時分別有89%和82%的患者可以產生特異性T細胞和抗體免疫。重組HER2蛋白疫苗(dHER2)是由HER2胞外區(ECD)和胞內區(ICD)片段與佐劑AS15結合而成的重組蛋白。
在另外一項Ⅰ期臨床試驗中,61例未使用過曲妥珠單抗的Ⅱ-Ⅲ期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在手術切除和輔助治療后接受了dHER2治療。結果顯示dHER2劑量與dHER2相關的特異性體液免疫的發生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在接受最高dHER2劑量的8例患者中,有6例患者在接種后5年都能保持其dHER2特異性體液免疫[22]。
3 乳腺癌相關DNA疫苗
DNA疫苗是指將編碼某種蛋白質抗原的重組真核表達載體直接注射到體內,使外源基因在活體內表達,其產生的抗原能夠激活機體的免疫系統,從而誘導特異性的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應答。一項小型Ⅰ期臨床試驗對8例轉移性HER2+乳腺癌患者接種了編碼HER-2/neu的質粒DNA疫苗以及佐劑GM-CSF和IL-2[23]。8例患者中有6例完成了3個周期的疫苗接種,且都接受了曲妥珠單抗治療。在研究中沒有觀察到與疫苗接種相關的副作用或毒性。研究結果顯示在接種疫苗后沒有立即觀察到HER2特異性的T細胞免疫應答,但在長期隨訪中檢測到MHCⅡ類限制性T細胞對HER2的反應顯著增加。
乳腺珠蛋白-A(mammaglobin-A,Mam-A)是一種分子量10 kDa的分泌蛋白,在80%的原發性和轉移性人類乳腺癌中過表達。在一項Ⅰ期臨床試驗中,15例Mam-A+的乳腺癌患者接種了Mammaglobin-AcDNA疫苗6個月后,在外周血檢測到參加研究的前7例患者顯示CD4+ICOS(hi)T細胞數量增加,CD4+FoxP3+T細胞數量減少[24]。Mam-A cDNA疫苗的接種與CD4+ICOS(hi)T細胞的特異性擴增和活化有關,并且這些活化的CD4+ICOS(hi)T細胞可以誘導表達Mam-A蛋白的人乳腺癌細胞的優先裂解[25]。
4 乳腺癌相關樹突細胞疫苗
樹突細胞(DC)是一種APC,它能夠將外源性和內源性抗原分別呈遞給CD4+T細胞和CD8+T細胞。目前可以通過從腫瘤患者的外周血中分離得到未活化或未成熟的樹突狀細胞(immature dendritic cells,imDCs),并向其直接添加TAAs或者編碼TAAs的載體轉染DC,從而得到攜帶TAAs的IDCs。接著使用特定的細胞因子刺激使其活化成熟,然后將成熟的樹突狀細胞注入患者體內,TAAs將被呈遞給CD4+/CD8+T細胞,從而啟動強大的特異性免疫應答[26]。在一項小型臨床研究中,7例Ⅱ-Ⅳ期HER2過表達乳腺癌患者在術后且完成4周輔助治療后接種了HER2胞內結構域(ICD)刺激的自體DC疫苗。在平均5年的隨訪后,有6例患者可以檢測到抗ICD抗體,且7例患者全部存活[27]。
5 各類乳腺癌疫苗的優缺點以及可能的應用前景
以上介紹的幾種乳腺癌相關多肽疫苗在各項臨床研究中都顯現出一定的優點,包括可耐受的副作用和安全性、易于合成等優點。但是多肽疫苗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為了確保APC對T細胞的共刺激作用,多肽疫苗需要相應的免疫佐劑才能發揮一定的療效。同時由于通用型疫苗只能針對有限的幾個表位發揮作用,當腫瘤相關抗原發生突變時便容易出現免疫逃逸。此外還有包括半衰期短、體內清除率高等其他缺點[28]。而與多肽疫苗相比,蛋白質疫苗在合成難度、疫苗副作用及安全性、結構穩定性方面沒有顯著優勢。但是在另一方面,蛋白質疫苗可以避免特定的HLA表位限制,同時可顯著激活T細胞,提高機體免疫應答水平[29]。前文介紹的乳腺癌DNA疫苗的Ⅰ期臨床試驗結果雖然表明了相關疫苗可以在受試人體內成功誘導相關免疫應答,但是其安全性和免疫原性還需要進一步研究驗證。同時,由于DNA疫苗也是通過不同的TAAs設計的,因此也不可避免要面對TAAs突變后的免疫逃逸問題。并且與其他類型的疫苗相比,DNA疫苗的療效還受到質粒載體及相關遞送系統的影響。而與上面幾種類型疫苗相比,使用患者自體血分離生產的DC疫苗的副作用更小。但是,從全血或白細胞中分離單個核細胞、在外周刺激產生成熟的DC細胞等程序也與DC疫苗的療效相關[30]。
目前由于我國不僅乳腺癌發病率高,還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因此乳腺癌已經給我國的醫療衛生建設事業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此,目前除了開發治療性疫苗以外,研發針對乳腺癌的預防性疫苗也同等重要。與治療性疫苗相比,預防性疫苗的應用人群更廣。因此,考慮到成本控制,生產工序、安全性等問題,多肽疫苗適用于開發預防性疫苗。同時針對因TAAs突變而造成免疫逃逸的問題,目前可以考慮選擇覆蓋多種腫瘤相關抗原,或者選擇相對穩定不易突變的TAAs作為靶點。另外,由于蛋白質疫苗可以避免特定的HLA表位限制,因此其也適合用于開發預防性疫苗。由于治療性疫苗需要保證其臨床療效,因此,在開發通用型治療疫苗的過程中,上述幾種疫苗同樣可以選擇復數或者不易突變的TAAs。此外,為了追求更好的治療效果,也可以針對每個患者制作個體化新抗原疫苗。通過生物信息技術,從來源于患者的病理標本中篩選出免疫原性強、誘導生成的CTL殺傷力強的多個特異性表位,并將其制作成相應的個體化新抗原疫苗。同時,也可以嘗試將疫苗療法與現有的化療、內分泌治療、靶向治療等手段相結合。
6 結論與展望
與化療、激素治療、被動免疫治療、放療等方式相比,乳腺癌疫苗具有以下理論優勢:耐受性較好、毒性更低、給藥時間短以及可以產生特異性抗腫瘤作用的持久免疫反應。但是,乳腺癌相關疫苗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1)由于大多數疫苗為MCH-Ⅱ類限制,這可能使能從接種乳腺癌相關疫苗獲益的患者人群減少;(2)多數疫苗需要和佐劑聯合應用才可取得一定的療效,因此可以通過開發更有效的佐劑、改變疫苗劑型等方式來嘗試提高疫苗療效;(3)上述疫苗針對的是一個或少數幾個通用表位,這可能無法克服腫瘤的免疫逃逸機制,導致疫苗的療效降低,研究表明在腫瘤免疫微環境中CTL識別TAAs并破壞腫瘤細胞這一過程會受到抑制[31]。近年還有報道其他機制參與免疫抑制,包括髓系抑制細胞(MDSCs)的擴增[32]、機體代謝變化[33]、樹突狀細胞(DC)的抑制[34]等。因此,針對這一點,可以通過選擇更具特異性且穩定不突變的TAAs以及增加通用表位數量來提高疫苗的療效。另外,隨著測序技術的進步,通過全外顯子測序以及RNA測序來識別個體化新抗原并制作的新抗原疫苗已經針對黑色素瘤取得了良好的長期療效[35]。因此,為了減少免疫逃逸,可以通過針對乳腺癌患者的特異性新抗原制作個體化新抗原疫苗。同時除了上述幾點以外,還可以通過優化疫苗成分、更改給藥方式、選擇加強接種加強針等方式來嘗試改善疫苗療效,也可以探索疫苗療法與手術、放療、化療、內分泌治療和單抗等其他治療方法結合后的治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