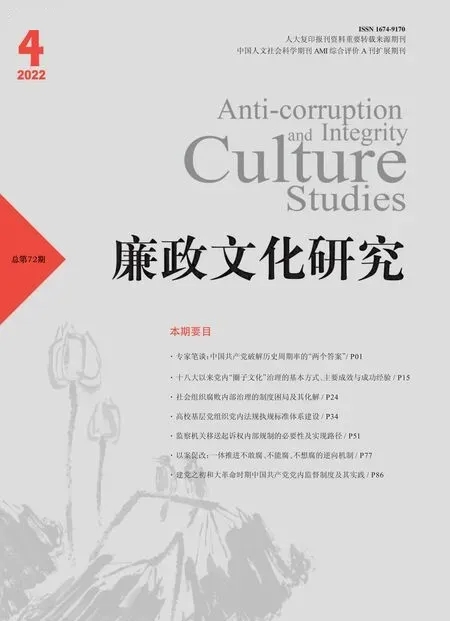人民監督:中國共產黨破解歷史周期率的“第一個答案”
羅永寬,王文浩
(武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歷史這么長、規模這么大、執政這么久,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一論述不僅肯定了毛澤東對于破解歷史周期率的艱辛探索,而且揭示了人民監督之于破解歷史周期率的重大意義。
歷史周期率這一重大命題源于20 世紀40 年代中期毛澤東對革命勝利后的憂慮。1944 年,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評述了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因勝而驕、旋而失敗的悲劇性歷史事件。此文得到毛澤東的重視,被列為整風學習文件。1945 年,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在與毛澤東的長談中,明確表達對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歷史周期率支配的隱憂。實際上在此之前,毛澤東對黨內曾發生過因驕致敗事例多有反思,并預見將來可能繼續發生“驕兵”之害。他強調全黨要以李自成為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因此,毛澤東對于黃炎培的疑問當即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找到跳出這一治亂循環周期率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即讓人民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依靠人民監督的民主方式,極大克服了舊式農民起義與封建統治勢力的局限性,其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寶貴經驗延續發展至今,是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陷阱的重要抓手和著力點。
一、人民監督有助于恪守人民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主體作用
瑞金時期,毛澤東曾領導建立工農代表大會和工農檢查委員會等組織,頒布法令,推行全民監察,從法律和制度層面保證人民群眾的監督權利,培養和鍛煉其參政能力,提升群眾對蘇維埃政權的了解與信任,強化工農群眾的責任感和自豪感,增強其參政意識和主體意識,這些已然關切到實行人民監督與人民群眾主體意識覺醒之間的密切關聯。對此,當時有新聞報道指出,在“‘匪禍’前,農民不知國家為何物”,但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后,蘇區群眾已經在思想上認識到其固有的參政權利,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更是可以直接選舉委員,甚至能夠出任政府官員,佐證了蘇區人民監督助力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的實際效果。
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制定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等法律法規,大力推動“三三制”“普選制”等民主制度在邊區落地生根,要求黨政干部必須接受人民的檢查和監督,向人民代表報告工作,傾聽和虛心接受人民群眾的意見,保證人民群眾監督、控告、檢舉揭發,乃至罷免政府官員的權利。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政治報告,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1949 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強調要“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體現出秉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繼續貫徹讓人民監督政府的主張。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罵群眾,壓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鼓勵人民群眾積極監督和檢舉,防止黨內出現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要求黨政干部革除特權思想,端正為人民服務的態度。
鄧小平從黨的性質和宗旨出發,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先進,恰是因其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組織和領導人民群眾為自身利益而斗爭外,完全沒有超乎人民群眾之上的權力和特殊利益,強調要拓寬黨政事務的公開形式,把所有能公開的,一律公開,以便更好地接受人民監督,解決群眾關心的問題,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高興不高興和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堅持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檢驗黨的工作好壞的最高標準。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和發揚了黨重視人民監督的優良傳統,要求各級黨員干部放下架子、俯下身子,主動到群眾意見多、矛盾尖銳和困難比較多的地方去,聽取群眾意見,接受人民監督,解決群眾關心的問題,真正做到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和問計于民。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明確提出“讓人民監督權力”。此后,人民監督的方式與方法不斷豐富,除改進和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信訪制度的監督職能外,依靠互聯網信息技術發展起來的政務公開渠道、民意反饋渠道和網絡監督渠道等新式監督網絡也在持續健全并產生影響,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彰顯。
二、人民監督有助于正確把握所處發展環境,作出并貫徹符合實際的決策部署
戰爭年代,毛澤東領導建立的群眾檢查監督組織,已顯現出督促各項工作順利開展的實際效果。比如,在蘇區的擴紅工作中曾出現強迫命令和紅軍家屬優待不到位的情況,造成新招募紅軍開小差現象多發,工農檢察委員會即對此進行調查和處理。可見,人民群眾的監督工作與黨的中心工作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其監督實踐就能夠促成黨的中心任務得到正確執行。另外,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等一系列文章中,詳細闡發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觀點,強調聽取群眾意見,了解中國具體實際對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極端重要性。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鄧小平多是從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的角度來論述黨為什么要接受人民監督。1957 年,鄧小平在西安干部會議上作報告,談到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議題,認為位居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威信很高、權力又大,一旦犯錯誤,波及面和消極作用會很大,為了盡可能不犯錯誤,就必須接受人民群眾及社會各方面的監督;因為社會面反映的問題多,黨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才會更加全面,即使發生了一些意外情況,也容易及時糾正。反之,如果一味地憑老資格,鬧宗派主義的小團體,脫離群眾,以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方式思考問題制定政策,排斥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意見,閉目塞聽,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就極易產生片面性,非犯錯誤不可。此外,鄧小平在思考如何盤活機關單位積極性時,有過擴大民主生活的主張,如在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召開職工會議商討企業重大問題,領導干部要接受職工的監督和批評,在學校要暢通教職工、學生會的意見表達渠道,單位領導需結合現實情況與群眾意見修正前進方向、調整相關政策。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非常重視群眾監督制度的構建,為人民群眾行使監督權提供保障,提高黨政決策與群眾利益的契合度。面對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挫折的嚴峻局面,江澤民十分重視保持黨同人民群眾之間的緊密關系。江澤民認為蘇共亡黨亡國的重要誘因,就在于蘇聯共產黨所施行的方針路線嚴重脫離了群眾的實際,不能滿足人民需要,最終失去人民群眾的擁護,走向衰亡。由此,江澤民得出結論:人心向背是關乎政黨、政權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因素。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就是決不能脫離群眾和凌駕于社會之上,要虛心聽取群眾意見,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推進人民監督制度化和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建設向縱深發展,整合監督資源。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將人民民主和監督事業推向前進。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要求黨員干部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2021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又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系統闡釋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涵特征與發展路徑,指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要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本依托,進一步落實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確保來自人民的聲音能夠傳達進黨和國家決策、執行、監督落實的各個環節。依此程序制定并實施的國家政策更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能反映群眾要求,即使在局部出現張力,各級黨政部門也能快速作出反應,動態調整策略,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三、人民監督有助于發揚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關注到人民監督對于整頓干部隊伍和正風肅紀的積極意義。在蘇區主要機關單位和街道路口,都會放置由中央各級工農檢察部為收集群眾意見而設的控告箱,并規定蘇維埃的公民都有權利向控告局檢舉政府和經濟機關中的貪污、浪費和官僚腐化現象,另有突擊隊、工農通訊員、輕騎隊和群眾法庭等群眾性組織厲行監督責任,《紅色中華》等期刊雜志亦開辟專欄為人民監督搭建平臺。諸如此類的若干舉措,有力打擊和震懾了蘇區黨政干部中的貪污腐敗分子,維護了蘇區干部的良好作風。1934 年中央審計委員會在公布節省運動成績時,曾得出“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之結論。
延安時期,毛澤東先后撰寫《新民主主義論》《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論聯合政府》等文章,闡述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強群眾監督以懲治腐敗和破除官僚主義的理論構思,并領導建立司法制度,完備民主監督機制,保障人民監督檢舉權利的實現。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前瞻性地指出黨內可能生長驕傲情緒和以功臣自居貪圖享樂、畏縮不前的心理狀態,要求各級黨組織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發揚“兩個務必”的作風,接受人民監督。1951 年末至1952 年10 月間,毛澤東親自領導發動旨在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群眾監督的作用得以較好發揮,增強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指出,推進人民監督制度化、法律化建設,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的黨政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人民有權依法進行彈劾、控告以及罷免和撤換。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推動下,《關于黨和國家機關必須保持廉潔的通知》《關于加強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條例》等黨紀國法陸續出臺,各級監督機構相繼恢復,職權得到加強,建構起較為嚴密的監督體系,依法受理群眾舉報線索,查處腐敗案件,嚴肅黨風黨紀。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人民群眾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的積極作用,認為黨員干部身上存在的問題,人民群眾看得最清楚,最有發言權,人民更是無所不在的監督力量。因此,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各級黨政部門加大黨務政務公開力度,提升領導干部接受群眾監督的自覺性,為群眾進行監督和評議暢通渠道,決不能以“批評”抵制批評。在實踐層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續提高群眾監督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將群眾力量深度嵌入權力監督的制度設計中,推動群眾監督制度與巡視制度的融合共進,出臺《關于創新群眾工作方法解決信訪突出問題的意見》《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則》等政策文件,完善和強化信訪監督、網絡監督、輿論監督等制度體系,凝聚監督合力,推動了人民監督落到實處,凈化了黨內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