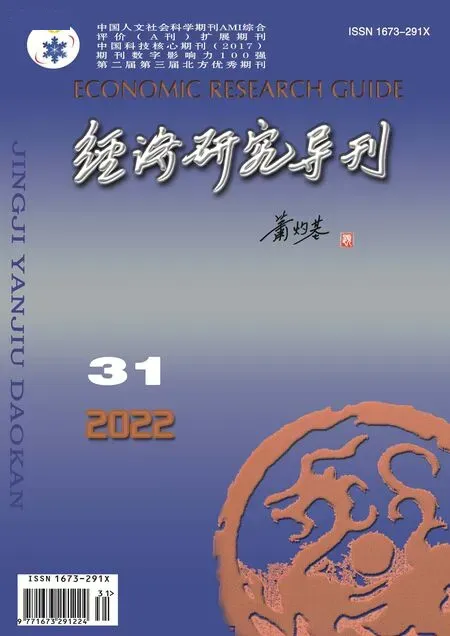互助養老模式:外文文獻綜述
劉小蝶
(南通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南通 226001)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高達18.7%,65歲及以上人口已達13.5%。可以看出,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形勢越發嚴重。2018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助養老”的概念,互助式養老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方面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國外對互助養老模式的探索時間比較早,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我國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還處于探索階段。對外文文獻進行綜述,對我國的互助養老模式的實踐具有現實意義。
一、概念界定
互助養老模式是指居住在同一社區或同一區域范圍內的老年人,本著自愿參與、友愛互助、相互扶持的原則,在生活、情感以及精神等方面互相提供服務,以滿足老年人的各種養老需求,從而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質量的一種互助式的養老模式。
二、互助養老模式的價值研究
(一)公民價值
影響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因素主要有兩部分,一是歸屬感,二是在社會中的價值感。互助式養老有利于實現參與者的社會價值,幫助人們提升自身的認同感,也有助于改善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態。
(二)社區價值
互助養老一般以社區為依托,Crisp等(2013)對互助養老服務在減少老年人的患病幾率以及能否降低其住院治療方面進行研究,認為互助養老模式可以使社區內養老資源得到有效整合配置。Gill Seyfany(2013)和Judith Lasker(2011)研究的共同結論是互助養老可以加強社區鄰里之間的交流互動,消除鄰里之間的防備心理,建立一種良好的鄰里關系,同時增強參與者的社區意識與社區歸屬感,使社區居民的相處更為融洽,繼而促進社區建設的可持續性發展。
(三)社會價值
互助養老模式的社會價值也不容忽視。Man Wai Alice Lun(2011)& Ozawa & Howell(1994)在研究中發現,互助養老模式以及老年人自發組織的志愿者服務可以明顯緩解社會的養老壓力。Lukas(2013)指出,互助養老模式可以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是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有效策略。西方學者們側重研究互助養老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耶魯大學教授Edgar S.Cahn(2004)認為,這種模式可以使參與者建立一種“核心”經濟,而這個核心經濟并非指向金錢或財富,而是一種產生在親人、家庭、鄰里以及社區之間的無形經濟。Gill Seyfang(2006)也指出,互助養老是對社會經濟的創新,它通過獎勵那些參與社區活動或去幫助鄰居的人,來培養人們之間的社會資本和互惠網絡。
三、互助養老模式的國外實踐經驗
經過不斷的實踐與探索,西方發達國家比較典型的互助養老模式包括美國的“村莊”模式、日本的“鄰里互助網絡”模式、德國的“多代居”模式以及英國的“時間銀行”模式等。
(一)美國的“村莊”模式
美國的“村莊”模式中的“村莊”和屬于我國地區劃分中的“村莊”是不同的,其本質是一種非營利會員制志愿者互助組織,最初由波士頓的基層社會組織Beacon Hill Village(BHV)建立。在美國的“村莊”模式中,參與者主要由65歲及以上老年人組成,成員不僅要進行組織的日常管理活動,同時也是志愿者的身份,成員之間通過開展志愿性的互助式服務來滿足基本的養老需求,包括社會、身體、情感和智力方面的需求。村莊也會為成員提供多種支持性服務,開展各種村莊建設活動,拓展服務形式來提高會員的整體生活質量。此外,還有專業的服務機構為其提供不同類型的專業養老服務,以此來滿足會員多樣化的養老需求,提高老年人長久居住在熟悉的環境中的能力。“村莊”模式尤其注重鼓勵非營利組織參與捐款、捐助實物等,資金主要來源于參與成員繳納的會費與慈善組織的捐款。
(二)德國的“多代居”模式
德國是一個典型的老齡化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提出“高齡友善型城市”與歐盟提出“激活老齡化”政策的背景之下,德國積極響應并推出了多代互助的項目,“多代屋”互助養老模式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德國的“多代屋”項目為服務對象提供免費無償的服務,是一種非盈利性的項目,由德國聯邦政府自上而下推進建立,政府每年為各地“多代屋”項目提供運營資金,德國政府還積極鼓勵慈善組織、基金會和地方企業參與,以保證“多代屋”項目的多元資金來源,社區負責多代屋的日常運營和管理,兼具開放、互助、志愿、福利的性質。德國的代際居住模式主要包括三種形式:第一,大學生與老年人合住,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大學生難以支付高額的房租費用。同時,城市中的獨居老人大多擁有空閑的房屋,老人把空余房間給學生免費居住,讓大學生與老人共同生活,互幫互助。第二,單親家庭與老年人合住,這是“多代屋”比較突出的一種形式,獨居的老人因為缺少社交活動,往往會產生孤獨無聊的情感,而單親家庭最難的問題就是平衡工作和照顧孩子,常常由于工作原因沒有辦法照顧孩子,因此單親家庭與獨居老人之間互相幫助,一方面是老人可以幫助單親家長看管照顧孩子,另一方面是單親家庭也可以陪伴和照顧老年人,給予其心理上的安慰,以此來解決老年人養老問題和單親家庭照顧孩子難的雙重困境。第三,老年人與老年人的合住,大多數老年人都不愿意去養老機構度過晚年,因此在同一個社區生活的老年人可以與其他老人一起抱團生活,在熟悉的環境里通過互幫互助來滿足彼此的養老需求。可以說,“多代屋”互助養老模式打破了家庭與代際之間的界限,這種互助關系,打造了不一樣的鄰里關系,是一種值得借鑒的獨特養老模式。
(三)日本的“鄰里互助網絡”模式
在日本具有突出代表性意義的互助養老模式是“鄰里互助網絡”,該網絡由政府提供政策、資金支持,由社區志愿者團體提供幫助,構建互助協會,主要由社區內的老年人通過互助的方式提供服務。另外,社會組織在提供社區養老服務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組織會經常舉辦各種鄰里聚會活動,為社區中的獨居老人提供互動交流的機會,并籌劃各種社區活動來豐富他們的老年生活。老年協會等組織會記錄活動中老人聊到的各自的問題和困境,并在以后的服務中采取有效措施,不斷改進滿足老年人多層次需求的養老服務。此外,在活動過程中,鄰里之間能夠互相了解、增進感情,可以加強獨居老年人的社會交往以及對鄰里的信任和依戀感,研究發現對鄰里的依戀感可以顯著提高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提高社區生活質量。可以看出,日本這種互助養老模式的產生,讓現代陌生的鄰里關系變得熟悉,對養老模式的改革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使傳統養老模式向新型養老模式轉變,有效緩解了老齡化的社會養老服務的壓力。
(四)英國的“時間銀行”模式
英國的“時間銀行”發展規模較大,已經較為成熟。英國最具代表性的“時間銀行”是共享石屋(Stonehouse Fair Shares)和萊西格林時間銀行(Rushey Green Time bank)。共享石屋于1999年成立,是英國第一家時間銀行,它最初是一個面向老年人以及殘障人士提供護理服務的慈善機構,后來逐漸成為以退休職工為主體的社區互助養老組織,以滿足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養老需求。為了推動“時間銀行”的全面發展壯大,英國政府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支持性政策體系,在資金上給予“時間銀行”大力資助,構建了比較完備的保障機制。英國政府還引導各種公益組織、慈善團體等參與以確保資金的多元化來源,并推動社會志愿服務積極發揮帶動作用,同時對志愿者進行醫療方面的相關培訓。除此之外,針對不同群體的各種需求積極組織開展個性化的服務項目也是值得借鑒的做法。
四、國外互助養老模式的啟示
(一)給予政策支持,發揮政府主導作用
從國外的互助養老實踐來看,政府是社會服務的組織者和管理者,互助養老服務的發展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Emily A.Greenfield等(2013)指出,政府資金對于“村莊”模式的發展很重要;沒有政府的資金扶持,日本的“鄰里互助網絡”很難建立起來;德國“多代屋”和英國“時間銀行”的發展也離不開政府對其提供運行資金的支持。但是互助養老模式的可持續發展不僅需要穩定的資金來源,更需要政府制定完善的政策體系,并對養老服務的質量進行監督和評估。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并完善互助養老方面的相關法律政策,大力宣傳互助理念、保障組織條例的執行和督促互助活動和條約的落實。同時,政府可以在政策上鼓勵互助養老模式和其他行業資源的結合,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為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政策環境。
(二)以需求為導向,改善互助養老服務
從國外的互助養老實踐來看,老人不僅僅是提供互助服務的主體,也是服務的對象,互助養老的最終目標是滿足老年人的多樣化養老需求。美國“村莊”模式中,成員擁有管理者和志愿者的雙重身份,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進行互助服務,對于無法通過互助方式提供的服務則由專業機構來滿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日本“鄰里互助網絡”模式根據老年人的具體問題提供所需服務;英國時間銀行鼓勵根據當地特色和老年人需求,組織開展有針對性的服務和活動。因此,在互助養老實踐中,應把老年人對于養老服務需求的差異性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改善互助養老服務,不斷滿足老年人多樣化、多層次的養老需求,提高老年人對養老服務的滿意度。
(三)重視社會力量,引入多元主體參與
從國外的互助養老實踐來看,社會當中的一些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服務同樣在互助養老模式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推動多元責任主體共同參與,才能更好地實現互助養老體系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非營利組織大多是官辦的,工作效率不高,在養老服務中的作用不明顯。另一方面,我國民辦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受到一定限制,很難為互助養老提供有效的幫助。因此,在互助養老的實踐中,要為社會組織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支持和引導互助養老團體組織的建設,發揮互助養老組織的引導功能,幫助團體中的個人實現互助。此外,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緩解政府在老齡事業中的壓力,政府應將一部分公共服務提供職能轉為監督和規范職能,為社會組織提供更大的發揮空間。比如,社會組織可以協助政府拓寬互助養老資金的來源渠道,還可以更加貼近老年人的實際養老需求,為老年人提供多樣化、多層次的老年服務。
(四)注重鄰里互助,構建新型社區關系
從國外的互助養老實踐來看,“就地養老”(Aging-In-Place)是國外養老服務發展的大趨勢,即老年人的普遍意愿是留在社區養老,在熟悉的社區環境和人際關系中度過晚年生活。西方大多數研究者把社區養老服務的資源分為“正式資源”和“非正式資源”,“正式資源”包括政府、市場化組織、養老機構等提供的服務,親屬、鄰里和志愿者服務等則屬于“非正式資源”。日本“鄰里互助網絡”模式十分重視鄰里互助的功能,完善社區互助養老模式的社會支持系統。在我國,城市的生活節奏很快,人際關系相對冷漠。因此,應該致力于加強社區居民的社區歸屬感,從而形成鄰里互助、平等友愛的良好社區關系。
(五)轉變養老思想,發揮老年人余熱
從國外的互助養老實踐來看,老年人之間的互助對解決老齡化的問題和發揮老年人自身價值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我國,因為長期受到“血緣”和“宗親”觀念和傳統養老觀念的束縛,多數老年人很難脫離“家庭”,無法正確理解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及意義。老人應轉變傳統思想,正確面對身體機能老化帶來的影響,以積極的心態面對和適應老年生活,主動貢獻力量幫助他人,發揮自身余熱的同時也豐富了老年生活。同時,年輕人應該消除對老年人的偏見,站在更加長遠積極的角度來審視老年人在社會中的貢獻,這對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總之,通過上述的文獻研究可以看出,為了更好地推動我國互助養老模式的發展,我們要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給予政策、法律、資金等方面的支持;第二,推動多元主體參與到互助養老模式的構建中;第三,重視社區內的鄰里互助功能;第四,轉變高齡人口的傳統養老思想,發揮老年人的余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