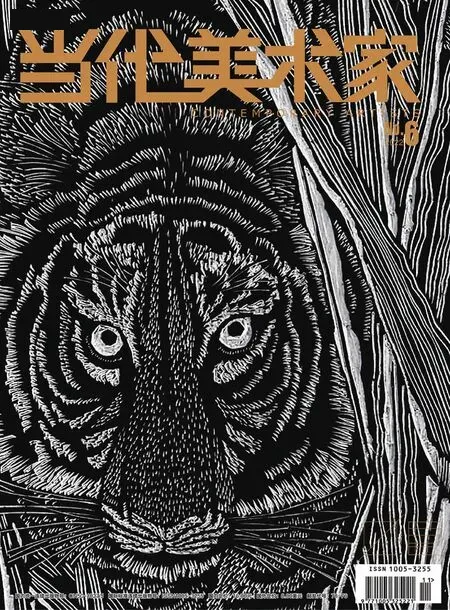論社會文化心理對早期裝飾紋樣的審美指向性影響
——以連續植物紋的肇始為例
郭昕 Guo Xin
社會文化心理是社會群體在社會實踐中自發形成的一種具有普遍性、穩定性、階段性特征的共同社會意識,它支配和約束著社會成員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價值判斷等社會行為,也不可避免地影響著社會群體的審美指向。[1]審美指向是主體對審美對象的選擇和導向。在一個時代或地區廣為流傳的審美對象,體現出相對穩定的審美指向性,是特定歷史時空中社會文化心理的必然產物。連續植物紋就是這樣一種審美對象。
連續植物紋以植物的花葉、枝干、藤蔓作為紋樣主體,往復相連,構成二方或四方連續圖案,較為著名的連續植物紋包括纏枝紋、忍冬紋、卷草紋等。連續植物紋廣為流傳、變體眾多、歷史古早、傳承至今的屬性,使之如同一本無字的史書,能真實折射出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社會文化心理特征,成為裝飾紋樣中的“活化石”。多年來不少學者從裝飾藝術發展史的角度,對富有代表性的連續植物紋的紋樣流變、圖式特征進行了梳理與研究。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經明確連續植物紋的構成特點包括:以植物的花葉枝蔓為內容要素,以連續、反復、曲線為形式要素;同時連續植物紋并非我國所獨有的傳統紋樣,跨越廣闊的時空可以發現各種既滿足連續植物紋基本構成要素但又各具特色的圖式,如古埃及的蓮花紋、古希臘的莨苕紋、古印度的忍冬紋、阿拉伯的蔓草紋等,這些紋樣在今天的裝飾藝術中依然被大量運用。在這些研究中,對連續植物紋本體的形式特征研究已經較為豐富,但它為什么會產生、為什么會廣為流傳、為什么會變體眾多,這些問題在過去的研究中尚未被闡明。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原始文化心理的角度剖析連續植物紋樣產生之前及產生之初,決定其表層圖式特征產生、傳播的內在因素,從各民族早期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連續植物紋變體豐富的原因,既可揭示社會文化心理對早期裝飾紋樣的審美指向性具有的深層次影響作用,也對更好地理解、傳承、創新連續植物紋樣有著積極意義。
原始時期,在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類的器物上就有了各種或抽象或寫實的紋樣,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這些紋樣在產生之初多具有象征或敘事的意義卻未必具有審美意義[2],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些紋樣孕育了人類最初的審美意識和后世裝飾紋樣的構成要素。
一、原始文化心理對連續植物紋樣形式要素的審美指向性影響
南非布隆伯斯洞穴中出土的75000年前的赭石石刻上已經有了連續折線型抽象幾何紋樣(圖1),東歐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指揮棒”上同樣有布滿棒體的波狀紋和螺旋紋,我國新石器時代也有各種折線紋網格紋,甚至到近現代的原始部落里,也能看到類似紋樣。更有意思的是,將這些紋樣并置在一起,這些跨越了數萬年的時間線和縱橫亞非歐各大洲的紋樣,并沒有明顯的區分度。這種現象提醒我們,原始紋樣的產生和具體的地域、時間幾乎沒有關系,決定它們形態高度相似的是一些共同的內在因素。這種因素就是原始社會特定的文化心理。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低下、生產關系簡單、認知水平低下等共同特征,形成相似的社會文化心理,這種相似的文化心理決定了原始紋樣的構成特征,導致世界各地原始紋樣的高度趨同性。

1.赭石石刻,出土于南非布隆伯斯洞窟(約75000年前)
原始社會的人類在以采集、漁獵為主的長期的勞動實踐中,對晝夜的更替、四季的往復和生命的始終有了初步感知,這種感性認知已經模糊地感覺到了自然世界中秩序、節律、循環、綿延等規律的普遍存在,而原始人類改造自然的力量微乎其微,他們的生產、生活只有與自然的規律相吻合才可能獲得相對順利穩定的生存繁衍。在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遵循自然的節律、群落的秩序、生命的循環、種族的綿延,不僅是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也成為他們的精神信仰。而節律、秩序、循環、綿延等特征也漸漸抽象出來,在原始文化心理中形成了一種強烈而持久的結構樣式。同時,從原始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來看,水波蕩漾的江河湖海、連綿起伏的山脈丘陵、動物植物的花紋肌理這些自然對象都包蘊著連綿、反復而富于韻律的曲線,這與原始文化心理的“力的樣式”是趨于一致的。
按照格式塔心理學的觀點,當客體對象與主體心理產生這種結構上的同一時即為異質同構,審美就產生于異質同構。也就是說,自然對象具備的連續性、曲線性、重復性等特征與原始人類的文化心理中的相關結構特征契合時,便形成同構對應的格式塔,使原始人類對具備這樣形式特征的外部樣式產生心理上的接受與認同;同時,由于人的主觀能動性,原始人類也會根據其文化心理特征有意識地去尋找與之對應的客體對象,來表達自己的審美指向,而對于不符合格式塔的形式特征的對象,要么無視其存在,要么通過整體變形或者提取某一局部進行再加工的方式,使其滿足原始文化心理的需求。格羅塞曾在《藝術的起源》中提到“裝飾藝術完全不是從幻想構成的”,“原始民族的裝飾,大多數都取材于自然界;它們是自然形態的模擬。”[3]通過上文分析可知,這里格羅塞所說的模擬并非目之所及的隨意模擬,而是在原始文化心理的主導下,在自然世界中有指向性地尋覓、摹仿、提煉、加工格式塔所需要的力的樣式。在這一過程中,被選擇的對象逐漸脫離自然形態呈現出人工形式。這些人工形式由于符合原始文化心理的特征,被廣泛地創造出來并反復地使用、長久地傳承成為一種必然。這就不難解釋為何世界各地的原始紋樣中都隱含著秩序、節奏等高度相似的形式美的基本規律,也包含了連續、曲線、重復等連續植物紋樣形態的造型要素了。
二、原始文化心理對連續植物紋樣內容要素的審美指向性影響
受文化心理的影響,在早期原始紋樣中,已經有了指向連續性、重復性、曲線性的特征,從形式要素上為連續植物紋的出現做好了鋪墊,但還需要一個重要的內容元素,那就是以植物作為紋樣表現的主題。格羅塞在《藝術的起源》中認為所有的植物圖形裝飾在原始藝術中都沒有萌芽,他還說:“文明民族的裝飾藝術喜歡取材于植物,而原始的裝飾藝術卻專門取材于人類和動物的形態。”[4]我們在原始紋樣中確實可以看到大量寫實的動物和人物圖樣,也可以看到大量的抽象紋樣,而且很多抽象紋樣還能清晰地找到從動物紋樣逐步簡化、抽象化的過程,如鳥紋、蛙紋等。但動物類紋樣的廣泛存在并不能說明原始時期就沒有以植物為主體的紋樣。問題的關鍵在于,植物在什么條件下才有機會成為原始紋樣的表現對象。
目前學術界的普遍認知是:人類從漁獵經濟過渡到農業經濟才會有從動物紋樣到植物紋樣的轉變。也就是說當新石器時代原始農耕出現,植物成為人類重要的食物來源的時候,原始人類的生產、生活與農作物發生了密切的聯系。隨著社會生活的改變,使社會心理也發生了改變,原始人類對植物有了更多的親近和關注,于是原始紋樣開始選擇以植物為塑造對象。這個認知看似有理,從目前已知的出土文物來看,的確在新石器時代出現了大量的植物紋樣。但是這里仍有存疑:如果是農耕的出現導致了人類對植物的依賴與興趣,那么早期出現的植物紋樣必然應該以農作物,尤其是農作物可供食用的果實部分為表現的主要對象。但在已知的原始紋樣中除了不多的稻穗紋和種子類紋樣,還有數量和變體都遠多于此的各類花瓣紋和葉形紋。花和葉作為自然界中最常見的對象,是否真的在農耕時代才被人們所關注呢?在此之前,它們對人類意味著什么?是否真的如有些研究者所說:“植物(包括花朵)剛開始不僅不是美的,而且可能還是恐怖的,因為這些植物之中可能隱藏著兇狠的動物”,認為進入農耕時代之前植物對人類來說是恐怖的,所以植物沒能進入人類的紋樣世界。[5]分析到這里,我們需要注意兩個事實:第一,在原始時期,令人可怖的對象往往使人產生敬畏之心,進而成為原始人類崇拜或者圖騰的對象,并加以圖示化用于宗教、祭祀等活動中,既然“兇狠的動物”可以成為紋樣的主題,那么“恐怖的”植物也理應相同。第二,在進入農耕時代之前,并不是植物遠離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漁獵時代以及之前的漫長歷史時期中,采集一直是原始人類非常重要的生產方式之一,也是原始人類最重要的生活來源之一。可以這樣說,漁獵時代因食物來源不穩定,人類出于生存的壓力,與植物的關系之密切并不亞于農耕時代。哪些植物的什么部位可以食用,哪些植物必須遠離,類似的這樣的經驗既需要數代人的積累,也需要將經驗代代傳承。因此對于植物的外形特點,尤其是具有標識性的局部特征,原始人類必定積累了大量敏銳的觀察、深刻的記憶。同時,我們也知道,植物的花葉枝蔓從紋理到造型都非常豐富,其中有很多是契合前文所提到的原始文化心理的“力的樣式”的。既然如此,植物也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早期原始紋樣的重要內容要素之一。這就不難理解出土于我國河北興隆縣13000多年前的刻紋鹿角上為什么不僅有水波紋、8字紋等曲線紋樣,還有連續葉紋了(圖2)。而新石器時代的植物紋樣更加豐富了,包括花形紋樣、葉形紋樣、樹形紋樣等。作為原始人類長期觀察、識別植物的必然結果,與我們上文的分析相吻合。這些植物紋樣大多選取和提煉植物富有特征的局部加以構形。這一時期常見的植物紋樣有卷花紋、勾葉紋等,以花瓣或葉片為表現主題,每一種紋樣又有不同的組織方式和各種變體,形成種類繁多的植物紋樣,并逐漸定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帶有連續、弧線、重復特征的植物紋樣,比如我國廟底溝的花葉紋(圖3)。

2.刻紋鹿角,出土于河北興隆(舊石器時代晚期)

3.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出土于河南省三門峽市陜縣廟底溝村(約前4400-前3500)
至此,已經清楚地看到,在原始文化心理的推動下連續植物紋的形式要素和內容要素均已具備,雖然我們永遠無法確切考證連續植物紋樣在何時何地最早出現,但可以推斷連續植物紋樣的出現是原始文化心理發展演進過程中的必然,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化中都有可考的連續植物紋。
三、各民族早期文化心理與連續植物紋樣的審美特征分化
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各地域的文化特征不再具有原始時期的高度相似性,文化特質的分化導致文化心理的分化,這就直接導致了不同文化區域的連續植物紋出現了各自不同的審美特征。
古埃及是植物紋樣較早的發源地之一。古埃及藝術的重要特征是為他們的宗教信仰服務。古埃及人相信靈魂是不死的,人死后只要保存好身體,靈魂有歸宿,就可以到達另一個永恒的世界去獲得永生。不管是他們具有標志性的金字塔還是正側面的人物構圖,都是在為他們追求永生的信仰服務。從古埃及時代留下的壁畫和其他物品上,可以看到在古埃及早期的藝術中由花、葉、梗構成的圖案就已經較為常見,其較為常見的連續植物紋樣是蓮花紋。古埃及的蓮花不是荷花而是埃及睡蓮,這種睡蓮當時分布于北非的水域中,包括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羅河。睡蓮隨著太陽的升降而盛開、閉合,因此古埃及人認為,太陽從蓮花中升起,又落入蓮花中;蓮花成為重生和復活的象征,被放置在木乃伊里。蓮花生于綿延的水波中,其根莖又在水面下綿延相連,其裝飾的對象——壁畫、亡靈書等也具有橫向延展的尺幅特征,因此古埃及的工匠們提取出波狀與曲線的線性幾何形狀聯結蓮花單體植株,使蓮花紋從形式要素上呈現出二方連續特征[6](圖4)。這些蓮花紋對稱均衡綿延反復無限延長,表達了對生命重生與綿延的信仰與渴望,呈現出一種莊嚴感和神圣感,其形式要素和內容要素相互平衡相互結合滿足了古埃及社會文化心理的需求。

4.古埃及的蓮花紋
如前所述,古埃及以其對蓮花的崇拜以及裝飾的需要為裝飾史貢獻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連續“花”紋,而與之鄰近的兩河流域則為裝飾史創造出了同樣影響巨大的連續“葉”紋。兩河流域文明與古埃及文明關系密切,其連續植物紋樣不論從植物的單體造型還是將單體植物聯結在一起的方式都與古埃及蓮花紋有著較多的相似。但兩河流域受巴別神系的影響有信仰“生命之樹”的社會文化特征,棕櫚、無花果等樹木以其強健的生命力、多汁的特征成為當時人們所崇拜的“圣樹”,是生殖、生命甚至光明、繁盛的象征。在亞述時期的尼姆魯德的浮雕中可以看到棕櫚圣樹的典型造型就是以肥厚豐茂的棕櫚葉由藤蔓狀的枝干彼此連接環蓋樹身(圖5)。對棕櫚樹的崇拜使得扇形棕櫚葉成為兩河流域古文明廣泛使用的裝飾紋,與埃及的蓮花紋一樣,出于裝飾的需要不斷優化,由象征性走向裝飾性,形成了程式化的的連續棕櫚紋。棕櫚紋和蓮花紋為連續植物紋樣貢獻了葉和花的內容要素和連續反復的形式要素,直接影響了后來的古希臘植物紋樣。

5.兩河流域亞述時期的棕櫚紋式樣
作為典型海洋文明代表的古希臘民族,其文化心理具有自由勇敢、浪漫熱烈、兼容并蓄、求真求美、追求現世生命的價值等特征。古希臘的連續植物紋樣受蓮花紋與棕櫚紋的影響,并創造發展出了莨苕紋。莨苕是一種生產于地中海沿岸的植物,其旺盛的生命力、強盛的繁殖力、勇于生長的生物特性與古希臘的社會文化心理的“力的樣式”相契合,使之在希臘裝飾中與蓮花紋、棕櫚紋相結合,被大量應用。莨苕紋在形式上花葉交錯、反轉往復,呈現出自由活潑、舒展繁盛之態(圖6),尤其是作為連接部分的卷須式樣充滿流暢自由的律動,徹底改變了過去連續植物紋樣的單調呆板僵化,強烈表現出了古希臘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從世界裝飾史的角度來看,連續植物紋樣在其發展傳播過程中,受經濟政治交流以及戰爭等因素的影響,使各地區各民族的紋樣特征呈現出相互影響交融的態勢,但差異性依然明顯,印度、西亞、中國、日本等地區和國家的連續植物紋樣各有其特色化的形式要素與內容要素[7],這種差異性正是社會文化心理對裝飾紋樣審美指向性的影響造成的。

6.古希臘時期莨苕紋飾裝飾的建筑柱頭
結語
從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對連續植物紋樣的源起進行研究,有利于在藝術設計中使用這一類裝飾紋樣時,既繼承又創新,既體現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符合當今世界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的人民群眾普遍的審美心理的需要;同時以此為例,舉一反三,在裝飾紋樣領域的研究與實踐中,以社會文化心理為深層次的考量因素,推動對紋樣的深入研究。本文從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對肇始階段連續植物紋樣的形式特征和內容特征的趨同與分化進行了分析,指出了連續植物紋樣的出現是原始文化心理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結果;最后以古埃及、兩河流域、古希臘等為例指出該紋樣之所以在不同的民族、地區發展演變出不同的表現內容與形式特征,其內在深層次原因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差異性。
注釋:
[1]張玉能:《深層審美心理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24頁。
[2]倪建林:《論原始裝飾藝術的涵義》,《山東工藝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第4-7頁。
[3][德]格羅塞:《藝術起源》,譯者:蔡慕暉,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90-91頁。
[4]同[3]。
[5]陸軍、吳清芳:《淺議原始彩陶裝飾方面的研究》,《景德鎮陶瓷》,2016年第5期,第25-26頁。
[6]劉蕊:《忍冬紋樣造型的源流探析》,西安:西安工程大學,2014年,第17頁。
[7]倪建林:《從忍冬到卷草紋》,《裝飾》,2004年第12期,第61頁。
圖片來源
圖1 [美]帕特里克·弗蘭克:《藝術形式》(第11版),譯者:俞鷹、張妗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39頁。
圖2 《中國美術史圖庫》https://m.douban.com/note/334049371/
圖3 張道一:《中國圖案大系1》(上冊),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3年,第31頁。
圖4 邱鳳香:《古埃及傳統裝飾圖案創意應用研究》,《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第153頁。
圖5 劉蕊:《忍冬紋樣造型的源流探析》,西安:西安工程大學,2014年,第23頁。
圖6 倪建林:《中西設計藝術比較》,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