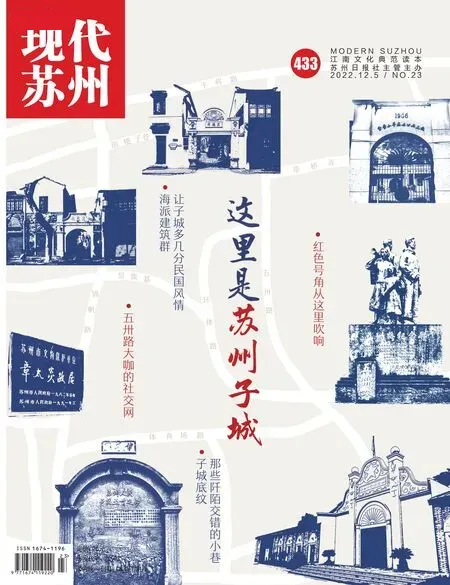姑蘇,一個城市的歷史影像
記者 丁云

垂入古井的西瓜,吸引了孩子們的目光(攝影/李淵)
一個城市的歷史遺跡、文化古跡、人文底蘊,是一座城市歷史、文化、藝術的具象載體,也是城市的歷史記憶和符號。
2022年是蘇州獲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40周年,由蘇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區管理委員會、蘇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區古保委、區文聯承辦的“姑蘇印記”古城保護40周年攝影展,近期在蘇州華貿中心姑蘇里·LAVIE展出,100多張從全市征集而來的姑蘇古城新、舊照片,從光影里展現了40年間的古城保護足跡。
這100多張攝于古城各個時期的攝影作品,由全市50多位攝影家帶來,分為古城遺存、百園之城、古今相融、市井人家、古城新貌等五個主題,從古城的硬件、軟件等多方面展示40年間的發展變化,以及古城保護的成果。1963年矗立在一片農田之間的雙塔、2005年搖櫓聲陣陣的平江路、40年前人聲鼎沸的觀前夜市……大量關于姑蘇古城遺存、市井生活的老照片都是第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借以流動著愛與美的影像作品對話城市、連接古今。
老照片上的生活滋味
茶館到底是哪一家?巷子到底是哪一條?拍攝角度到底在哪里?當時的場景在做什么……幾乎每一撥來參觀的觀眾,都是三三兩兩組團而來,有滋有味地談論照片里的內容。有些照片,可能就連拍攝的人也混淆了拍攝細節,但觀眾卻根據照片上的情景和記憶里的蛛絲馬跡,不斷地推演、拼湊出照片包含的大部分信息。有些圖片的說明,本身就顯得很懷舊了,比如“原工業品商場”,不知還有多少老蘇州人記得工業品商場就是美羅百貨,而它還有個更古老的名字“五化交商場”。
從一張時間標記為“20世紀30年代的盤門”的黑白照片來看,瑞光塔仍舊保持著原本“清瘦”的樣貌,至少到20世紀80年代,那里周圍的房子也依舊如照片中所示。至于背景的瑞光塔,估計還是眾所周知的1978年被幾個小學生發現國寶文物時的瑞光塔,因為如今挺立在盤門的瑞光塔,修復后“元氣滿滿”。但一些巷子里弄是不是在盤門?出版過《一水一盤門》的人文攝影記者于祥也犯起了嘀咕,相比之下,他覺得更像是在百花洲一弄、二弄。
即便是在20世紀初的老照片里,吳門橋也依舊太好認了,“江蘇省現存最高的單孔古石拱橋”的特征過于凸顯。吳門橋加上一旁的興隆橋、附近的裕棠橋,共三座橋是拍攝吳門橋最常用的鏡頭語言。“現在有了新裕棠橋,實際可以拍出四座橋來了。”于祥說。附近,幸福村集體洗滌的場面是于祥拍攝盤門的一張經典照片。照片里既有男人,又有女人,喏,說明蘇州男人是做家務的,還有人腳蹬回力鞋,當時很時髦。
另一位攝影家李淵拍攝的一口雙眼井照片里,有人將西瓜垂入古井,拍照的人用鏡頭對準了井下“作業”,而五個孩子出于好奇,或許是想看看西瓜怎么樣了,或許是想看看叔叔到底在拍什么,從另一眼井口中探頭探腦,正好被鏡頭捕捉到,兩個井眼,不同目的的三組人,全部被“機警”的相機咔嚓了下來。
回憶里的古城百轉千回
攝影家李孝祥、孫以樑從不同角度拍攝下了占魚墩吊橋下南碼頭、南新路一帶的昔日場景。照片上船只的密集度,就真實展現了當年金閶門、銀胥門的繁盛等級。這些船只既是在水上長途跋涉的交通工具、吃飯家伙,更是船上人的家。放大的照片上可以仔細觀察船上附帶的灶臺等生活設施。
過去從橋上下來,都是走到橋堍打一個彎兒轉回頭,再從臺階下到沿河岸,用蘇州話說,就是沒有直沖頭。街上一派悠閑。一些老房子的雕花木窗與陽臺很美,樓下的門臉上還吊掛著鳥籠,有人抱著飯碗頭吃飯,推測拍攝時間是午后了。
賣菜的船只停靠岸邊。堤岸就是天然的工作臺,運來的白菜一溜擺開就可以直接出樣,而若是街上人流量不夠大,生意不夠好時,船上人就會用船頭的那種菜筐子挑上岸走出去賣。
小時候在裕棠橋、朱公橋附近也看過人家這樣賣西瓜。那些買菜的人,有時嫌撂在外頭的菜不夠好,膽子大的還會順著木踏板跑到船上挑。你看那個傾斜角度和寬度,加上船泊在水面上有時要晃兩晃的,這種人的膽子真是很大的,身段也很靈活。
這樣的黑白老照片,都有鮮活的生活場景,多看兩眼就能回到往昔,模糊的記憶也會變得有棱有角。于祥說,當年他們拍攝時,也沒有料到照片里會包含多少內容,不同的人不同的視角,但能夠拍下這么多這樣的照片,是非常可貴的。當年當時,這樣的紀實性照片是不可能獲獎的,“俗語評價就是‘破破爛爛’的,但到今天,誰人不說這兩張護城河邊的照片拍得真是好?”

上圖:閶門外北碼頭曾是當時重要的水運中心(攝影/李孝祥)

下圖:舊時護城河邊(攝影/孫以樑)
看到照片,常叫人想起往事。“姑蘇印記”古城保護40周年攝影展上的照片質量都很高,于祥感嘆,很多攝影人都是他的拍友們。當年,他們有機會拍攝下更多彌足珍貴的古城場景,但“熟”視無睹,舍近求遠,錯失了機會。這或許是他們年少時追求的“標新立異”,卻未意識到姑蘇古城的處處獨異于世,好在有人補上了其中的部分“缺位”。于未來而言,姑蘇古城還年輕,古城保護是未竟的事業,當下的記錄也是留給未來的珍貴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