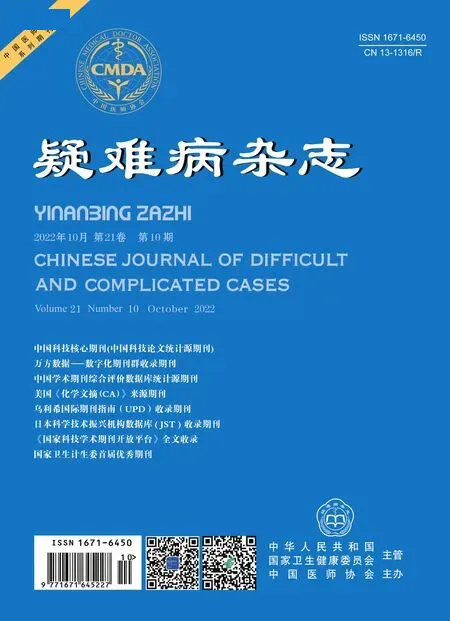二肽基肽酶-4抑制劑與感染SARS-CoV-2糖尿病患者的相關性研究進展
楊海珍,何鑫綜述 胡克審校
研究發現,合并糖尿病尤其是2型糖尿病(T2DM)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病情加重的重要危險因素之一[1],因此,對于不同降糖藥物在機體感染SARS-CoV-2后不同臨床結局的影響已越來越受到關注,有研究分析了二甲雙胍及鈉—葡萄糖共轉運體2抑制劑對這些患者預后的影響、可能的利與弊等[2]。近來發現二肽基肽酶-4(DPP-4)在SARS-CoV-2病毒進入體細胞內的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而二肽基肽酶-4抑制劑(DPP-4is)廣泛應用于T2DM的治療中,且安全性良好,因此對于DPP-4is與COVID-19預后的相關性同樣受到高度重視[3]。本文旨在介紹有關DPP-4is對COVID-19臨床結局影響的研究進展,尤其是與T2DM患者合并COVID-19的相關性。
1 DDP-4及DDP-4is概述
1.1 DPP-4及DPP-4is對免疫的作用 DPP-4最初被稱為“T細胞抗原CD26”,是一種能與宿主細胞相結合的多功能、可溶性絲氨酸蛋白酶,已發現在淋巴細胞、脂肪細胞及其他多種細胞有大量表達,包括肺血管內皮細胞和肺泡上皮細胞;同時,廣泛表達于多種類型的免疫細胞,包括CD4+和CD8+T細胞、B細胞、自然殺傷細胞、樹突狀細胞、巨噬細胞等,并參與其功能的調節。研究表明,除具有催化活性外,DPP-4/CD26也與T細胞信號轉導過程有關,通過與腺苷脫氨酶(ADA)、小凹蛋白-1(caveolin-1)、CD45、甘糖-6磷酸/胰島素生長因子-Ⅱ受體(M6P/IGFⅡ-R)等細胞蛋白相互作用聯合刺激參與T細胞活化,產生控制免疫應答的細胞內信號[4]。同時,研究結果也表明,CD26在與其他因素共激活T細胞的作用中,DPP-4的催化活性不是必需的[5]。DPP-4也可以可溶性形式存在于血漿和體液中[6]。研究發現,可溶性DPP-4可增加促炎細胞因子如IL-6、IL-8的分泌,2種細胞因子在肺損傷中發揮關鍵作用[7]。DPP-4is主要通過影響活化B細胞核因子-κ輕鏈增強子(NF-κB)信號通路來減輕炎性反應程度,有研究證實,該類藥物在T2DM患者中具有快速強效的抗炎作用[8]。因此,DPP-4不僅在維持機體葡萄糖的穩態中起關鍵作用,而且在炎性反應和免疫反應中也起重要作用。基于此,推測DPP-4/CD26參與了多種免疫性/炎性疾病,而DPP-4is通過修飾多種免疫調節底物的生物活性而穩定內環境或治療疾病[5]。
1.2 DPP-4及DPP-4is對炎性反應的作用 由于DPP-4/CD26參與調節T細胞活性,曾認為DPP-4is可能因損害細胞免疫功能而增加發生呼吸道感染的風險[5]。然而,在臨床實踐中常規使用DPP-4is并不影響機體的固有免疫及適應性免疫。不過有研究顯示,與其他降糖藥物使用者相比,DPP-4is使用者報道的感染數量增加,特別是上呼吸道感染病例[9];但另一項大型前瞻性研究并沒有發現DPP-4is存在感染風險增加的證據[10]。有研究表明,DPP-4is可增加鼻炎、咽炎及尿路感染的風險,但不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風險[11]。在COVID-19大流行前夕發表的2項觀察性研究和對41項隨機對照性研究進行的薈萃分析顯示,DPP-4is并不增加發生肺炎的風險性[12]。總之,就普通細菌性肺炎的風險性而言,常規使用DPP-4is是安全的。
在2013年,DPP-4被歐洲人類冠狀病毒伊拉斯姆斯醫學中心確定為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冠狀病毒的功能性受體,其基因型與SARS-CoV-2相類似。研究發現,DPP-4的自然突變并不利于MERS-CoV進入宿主細胞,反之可能有助于改善MERS感染患者的病情發展[13]。為進一步評價DPP-4與MERS臨床經過的相關性,研究者通過免疫學方法研究了DPP-4在機體內的分布,結果發現,在人體呼吸道DPP-4的免疫反應性定位于免疫細胞、內皮細胞、肺泡細胞、胸膜間皮和淋巴管[14]。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項有關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小鼠模型的研究中,DPP-4is可通過抑制促炎細胞因子白介素-1b、腫瘤壞死因子-α和白介素-6,而減輕肺損傷等組織學變化,但這種來自動物實驗的發現尚未在人體中得到證實[15]。
2 DDP-4及DDP-4is與糖尿病的關系和作用
葡萄糖穩態依賴于多種激素的相互作用,包括胰島素、胰高血糖素和腸促胰島素激素等。小腸內存在營養物質時,腸內分泌細胞會釋放腸促胰島素激素,主要是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和葡萄糖依賴性胰島素性多肽(GIP)。這些激素以葡萄糖依賴的方式刺激胰島素分泌,同時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從而促進血糖調節。DDP-4廣泛表達于多種組織中,其功能雖尚未完全了解,但其在葡萄糖和胰島素代謝中有重要作用。GLP-1和GIP被循環中的DPP-4快速代謝并失活[16],最終導致胰島素分泌減少。DDP-4is可快速特異性抑制DPP-4活性,從而阻斷GLP-1和GIP的分解,增加活性腸促胰島素的水平,最終使胰島素分泌增加和血糖水平降低。由于這種特性,DDP-4is被用于治療T2DM,這也是臨床上控制血糖的良好選擇,在許多國家逐漸取代磺脲類藥物[17]。這一趨勢的原因是,DDP-4is除了對餐后血糖控制有積極作用外,對T2DM患者的體質量、血壓、餐后血脂、氧化應激和內皮功能也有積極作用[18],且血糖變化幅度小,發生低血糖的風險性低,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尤其是住院患者。
3 SARS-CoV-2對糖代謝的影響機制
COVID-19與糖尿病之間存在雙向關系。一方面,糖尿病與嚴重的COVID-19風險增加有關;另一方面,COVID-19本身會擾亂葡萄糖穩態,并可能發展為糖尿病[19]。長期以來病毒感染被認為是引發糖尿病的潛在環境因素。研究表明,SARS-CoV-1與β細胞破壞和1型糖尿病的觸發有關[20]。來自德國和我國的病毒學數據揭示了SARS-CoV-2和SARS-CoV-1感染之間的重要共性,并證明SARS-CoV-2與SARS-CoV-1均通過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CE2)進入宿主細胞[21]。一方面,ACE2可裂解血管緊張素Ⅱ(Ang-Ⅱ),當SARS-CoV-2與ACE2結合后,ACE2與病毒復合物一起被內吞,降低了ACE2在細胞表面的表達,導致Ang-Ⅱ積累和局部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激活;另一方面,Ang-Ⅱ不僅可通過Ang-Ⅰ型受體促進血管收縮,還可促進炎性反應的發生,甚至可能導致急性肺損傷、細胞因子風暴。目前尚不清楚COVID-19引發的糖尿病表型是典型的1型還是2型,其糖代謝改變是短暫的還是持續的[19]。一些暴露于SARS-CoV-2的新發糖尿病患者,可能由于細胞因子風暴及SARS-CoV-2向胰腺β細胞的趨向性而增加胰島素抵抗和胰島素分泌減少,進而引起了血糖升高[22]。這可能由于RAS的激活和宿主對COVID-19的炎性反應所致。
4 DDP-4及DDP-4is與SARS-CoV-2及COVID-19的關系和作用
4.1 來自生物信息學的研究發現 研究者利用生物信息學方法來預測人體細胞與病毒蛋白相互作用及基于晶體結構蛋白對接的結果顯示,人類DPP-4與SARS-CoV-2的刺突受體結合區域具有高度的親和力,并據此提出假設,即SARS-CoV-2能通過DPP-4酶作為功能性受體進入宿主細胞[23]。將SARS-CoV-2主要蛋白酶的三維結構與包括DPP-4在內的多種蛋白酶的三維結構進行對比,發現盡管預測結果需要進一步評估,但仍提示DPP-4is具有抗病毒作用,并可用來治療合并COVID-19的糖尿病患者。然而,另一項研究并未證明SARS-CoV-2能與DPP-4結合,而是發現β冠狀病毒除與公認的ACE2結合外,還能夠通過一種未知的受體進入人體細胞[24]。目前大部分研究認為,相對于DPP-4,膜結合ACE2是COVID-19進入宿主免疫細胞的主要結合位點,而COVID-19患者血液中可溶性DPP-4水平下降這一現象,提示ACE2和DPP-4酶在COVID-19發病過程中起著調節作用[25]。另有研究者進一步提出假設:由于DPP-4is能靶向作用于宿主細胞與病毒的結合位點,因此使用DPP-4is或許可降低機體在暴露病毒后的COVID-19嚴重程度[3]。但對這一假設尚存在一定爭議。
4.2 DPP-4is對COVID-19作用的相關機制 具有抗炎特性的抗糖尿病藥物一直被認為是COVID-19時期“充滿希望的藥物”,已知DPP-4is因其較強的抗炎作用而對心血管系統和腎臟功能具有保護作用[26]。對16項研究進行的薈萃分析結果發現,與安慰劑相比,DPP-4is治療可顯著降低炎性生物標志物C反應蛋白(CRP)的水平[27]。Solerte等[28]分析了DPP-4is對因COVID-19而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生化結果,結果提示DPP-4is治療組患者的IL-6、降鈣素原和CRP等炎性參數較基線降低。由于炎性反應過程在COVID-19患者異常活躍,加重疾病嚴重程度,促進SARS-CoV-2感染患者發生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凝血功能障礙,因此,DPP-4is可能有利于阻斷導致細胞因子風暴的通路。
另一方面,由于DPP-4是一種作用范圍廣泛的多功能蛋白,不僅僅限于作為蛋白水解酶的作用,因此當其受到抑制后對機體的影響可能也是多方面的。應當指出的是,當前對于COVID-19的致病過程已有較好的了解,確定了多種危險因素和保護性因素[29],但對DPP-4is在感染SARS-CoV-2的2型糖尿病患者臨床結局有何影響方面尚未完全闡明[3],尚待隨機對照性研究獲得可靠結果之后,方能進一步明確其地位。
4.3 COVID-19期間有關DPP-4is的觀察性研究 分布于人體呼吸道的DPP-4可能會促進病毒進入呼吸系統,并導致機體發生COVID-19,促進細胞因子風暴和免疫病理的進展,乃至發生ARDS。因此,至少在理論上,將DPP-4is應用于感染SARS-CoV-2的2型糖尿病患者,可能減少進入呼吸道的病毒及其復制量,并減輕患者在發生COVID-19后的肺部細胞因子風暴和炎性反應程度[30]。基于這一假設,已經報道了多項回顧性臨床觀察研究[28,31-32],分析了DPP-4is對因COVID-19而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臨床結局的影響,但不同的研究結果之間差異較大,患者需要入住ICU的風險比(HR)為0.36~1.81。同樣,這些研究也分析了DPP-4is對住院患者病死率的影響,不同結果之間的異質性也很明顯,風險比為0.13~1.48。事實上,對于這些研究之間存在較大異質性的原因并沒有進行較好的解釋;而且,大多數研究并不是專門針對假設而設計的。如在法國進行的冠狀病毒SARS-CoV-2和糖尿病終點研究即CORONADO研究[32],接受DPP-4is治療的糖尿病患者數量很有限,因此,這也降低了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因為樣本量小的研究結果使統計效能下降。而另一項招募的患者數量更大、旨在專門評估DPP-4is對預后影響的病例對照性研究[28],所獲得結果則更具有說服力。與未使用者相比較,DPP-4is使用者需要入住ICU的風險比及發生死亡的風險比均更低,前者HR為 0.51(95%置信區間 0.27~0.95,P=0.03),后者HR為0.44(95%置信區間0.29~0.66,P=0.000 1)。
應當指出的是,現有的研究資料均存在較大的局限性。首先,選擇性偏倚和多種混雜因素影響了所得結果。因為現有的關于感染SARS-CoV-2的T2DM患者的預后大多來自回顧性觀察性研究,這種回顧性研究有其本身固有的缺陷;此外,在無隨機化的情況下,無法避免選擇性偏差;不同種類降糖藥物的適應證和禁忌證不同也影響所得結果;而且,DPP-4is使用者與未使用者的臨床特征可能存在差異,包括年齡、腎功能、已確定的心血管疾病等,甚至這些因素帶來的影響可能獨立于DPP-4is本身帶來的影響進而影響預后[30]。其次,患者住院期間血糖控制水平可能影響合并COVID-19的T2DM患者的預后[1];但迄今已發表的有關DPP-4is與預后相關性的研究中,并沒有對住院期間血糖控制水平進行分析和排除;甚至對于入院前使用的DPP-4is是否在住院期間仍然維持使用也不清楚。最后,由于這些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國外已經有學者對此進行了討論和點評[33],并認為當前客觀的看法是使用DPP-4is僅可能在理論上降低COVID-19相關病死率,現有的證據并不足以證實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西格列汀等DPP-4is對發生COVID-19的T2DM患者有著潛在的益處,需要得到良好設計、高質量的前瞻、隨機、對照性研究的證實。
5 當前臨床實踐推薦
為證實DPP-4is治療可能影響T2DM患者發生COVID-19后的病情變化這一假設,一項在意大利完成、包括3 818例重癥COVID-19患者的研究發現,盡管意大利不同地區使用DPP-4is存在明顯的差異,但這種差異與糖尿病患者感染COVID-19后的病死率并不相關[34]。因此,這一發現并不支持DPP-4is對COVID-19的發生和病情進展可能產生影響。由于COVID-19是一種有著諸多未知和不確定因素的新型病毒導致的感染,至今對其研究的深度仍然有限,因此,專家建議對病情嚴重的COVID-19糖尿病患者應遵循經典的糖尿病治療策略[35]。而且,在大流行期間強調對COVID-19患者進行良好控制血糖的重要性,甚至有學者提出優化血糖控制可能減輕病情和降低感染COVID-19的風險性[1]。此外,在一般情況下,對于有著T2DM的SARS-CoV-2無癥狀感染者或非重癥COVID-19患者,不建議預防性停用降糖藥物。另一方面,即使與胰島素聯合使用,DPP-4is也不增加發生低血糖的風險性,而且對腎功能的影響也不大。在當前,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建議輕、中度COVID-19住院患者應停用DPP-4is,也即建議非重癥患者應繼續使用。
6 小結
盡管近來有報道認為,DPP-4is有益于降低COVID-19合并糖尿病患者的病死率[28],但在總體上支持DPP-4is能夠改善暴露SARS-CoV-2的T2DM患者預后的證據仍不充足。對于DPP-4is在這些新發糖尿病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未得到充分的證實。此外,DPP-4is對病情危重的COVID-19患者的治療作用可能有限,不少需要入住ICU的重癥患者無法繼續使用這類藥物,且即使有必要使用降糖藥物也應首先采用胰島素替代治療。
總之,鑒于DPP-4參與免疫和炎性反應等諸多生物學過程,因此有理由認為DPP-4is可能改善感染SARS-CoV-2糖尿病患者的預后,但現有的研究尚不足于確切地回答DPP-4is對COVID-19糖尿病患者預后的影響。此外,除危重患者外,無證據表明COVID-19糖尿病患者需要停用DPP-4is。當然,這些結論仍有待于前瞻、隨機、對照性研究所得結果的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