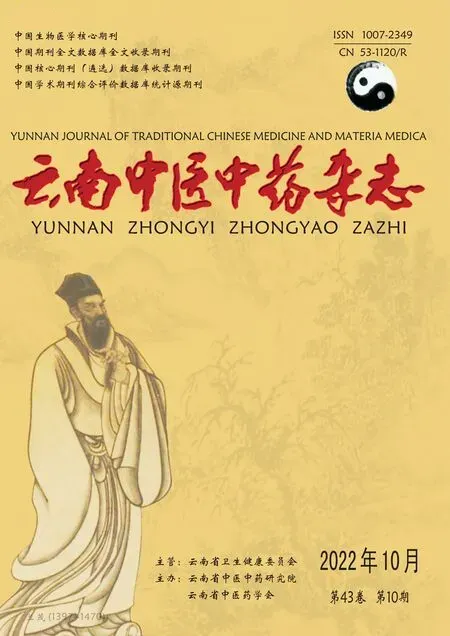李德隆教授運(yùn)用滋養(yǎng)心陰法治療肝腎虧虛型中風(fēng)經(jīng)驗(yàn)
譚振貴,譚 華,王 平△
(1.湖北中醫(yī)藥大學(xué)第一臨床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34;2.湖北中醫(yī)藥大學(xué)附屬武漢市第一醫(yī)院,湖北 武漢 430034)
腦梗死(cerebral infarction)又稱缺血性腦卒中,是由各類原因引起以局部腦組織血液供應(yīng)障礙、缺血缺氧性病變?yōu)樘攸c(diǎn)的腦部病變。目前在全球范圍內(nèi)所有致死疾病中排名第二,與缺血性心臟病合計(jì)約占所有心腦血管疾病死亡人數(shù)的85.1%以上,其致殘率以及復(fù)發(fā)率普遍高于其他系統(tǒng)疾病,已成為全球重大公共衛(wèi)生問題之一[1-3]。在中醫(yī)學(xué)中,本病屬于“中風(fēng)病”范疇,以猝然昏仆、口舌歪斜、半身不遂、語言不利為主要癥狀特點(diǎn),根據(jù)有無神智昏蒙可診斷為中經(jīng)絡(luò)和中臟腑,其中中經(jīng)絡(luò)包括風(fēng)痰阻絡(luò)證、風(fēng)火上擾證、氣虛血瘀證、陰虛風(fēng)動(dòng)證、肝腎虧虛證五大證型,中臟腑可分為痰濕蒙神證、痰熱內(nèi)閉證、元?dú)鈹∶撟C三大主要證型[4]。歷代醫(yī)家對于肝腎陰虛型中風(fēng)的治療,多以益氣活血祛瘀、補(bǔ)肝益腎為主。李德隆教授從事教學(xué)、臨床六十余載,熟讀《黃帝內(nèi)經(jīng)》,精通醫(yī)理,勤于臨床,認(rèn)為心為一身之本,統(tǒng)領(lǐng)全身血液循環(huán),主血液的運(yùn)行以及生成,通過運(yùn)用滋養(yǎng)心陰法,調(diào)和心臟陰陽,加強(qiáng)心主血脈功能,對于治療肝腎虧虛型中風(fēng)療效顯著。筆者有幸跟診,受益良多,現(xiàn)將其治療經(jīng)驗(yàn)介紹如下,以饗同道。
1 病因病機(jī)
1.1 年老體衰是基礎(chǔ) 李老認(rèn)為,年老體衰是中風(fēng)的發(fā)病基礎(chǔ),正如《內(nèi)經(jīng)》云:“女子六七,三陽脈衰于上……,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男子五八,腎氣衰……,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dòng),天癸竭。”首先,年到古稀,精虧神少,元?dú)獠怀洌X竅失養(yǎng),致腦部供血障礙,引發(fā)中風(fēng);其次,五臟六腑隨年齡的增長,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衰退,伴隨著現(xiàn)今人類壓力的劇增,或飲食無度、或勞逸失調(diào)、或?yàn)E用藥物,致使其功能失調(diào),藏泄失司,氣血逆亂,終致中風(fēng)的發(fā)生。
1.2 肝腎虧虛是關(guān)鍵 中風(fēng)主要病機(jī)為陰陽失調(diào)、氣血逆亂,病因主要為肝腎陰虛、氣血耗損[5-6]。李老認(rèn)為,肝臟陰虛,肝失調(diào)達(dá),陰陽失調(diào),或統(tǒng)血無力,血不循經(jīng),或藏血失衡,血不養(yǎng)經(jīng),致精血無法充養(yǎng)腦竅及四肢血脈;另一方面,腎臟為“先天之本”,儲(chǔ)藏機(jī)體一生之精,腎精亦是血液生成的來源之一,腎臟虧虛,腎精失養(yǎng),后天之精生成受阻,出現(xiàn)氣血匱乏,成為本病發(fā)生與發(fā)展的重要原因。
2 治法治則
2.1 補(bǔ)肝益腎為先 腎藏先天之精,寓真陰、涵真陽,主骨生髓育于腦;肝為罷極之本,主疏泄,通暢氣機(jī),協(xié)調(diào)出入升降,統(tǒng)帥血液運(yùn)行[7]。李老認(rèn)為,中風(fēng)患者多為年老體衰,肝腎乏源,精不養(yǎng)血,髓海不充,以半身不遂,四肢乏力,言語不利,舌淡紅,脈沉細(xì)等一派“陰虛”之癥為主。在臨床上常用左歸丸加減,以滋肝腎陰,填精益髓。方中重用地黃為君,滋陰填精,大補(bǔ)肝腎之陰;山茱萸滋肝腎之陰,山藥補(bǔ)脾益腎固精,烏梅酸甘化陰、固澀陰津,石斛滋陰益胃,取“陰中求陽”之義,四者共為臣;佐以枸杞、菟絲子、川牛膝補(bǔ)肝益腎填精,適當(dāng)加用葛根、伸筋草、桑枝等通經(jīng)活絡(luò)之藥以攜藥流通上下,諸藥合用,使腦竅得養(yǎng),髓海得充,達(dá)到治療目的。
2.2 滋養(yǎng)心陰為要 《黃帝內(nèi)經(jīng)》云:“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首先,心主行血,統(tǒng)領(lǐng)全身氣血運(yùn)行,使食物水谷之精微輸至五臟六腑、四肢及腦竅,維持機(jī)體正常生命活動(dòng);再者,心主生血,和五谷之精微“奉心化赤”生成血液,《靈樞·邪客》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為血”,以此充分濡養(yǎng)五臟六腑以及四肢。李老認(rèn)為,肝腎虧虛型中風(fēng)所表現(xiàn)的癥狀主要以陰虛為主,臨床上單以補(bǔ)肝益腎往往收效欠佳,在此前提下,通過應(yīng)用生脈散,以味甘之人參大補(bǔ)心氣,以入心肺胃經(jīng)之麥冬滋陰生津養(yǎng)心,以味酸之五味子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心陰的補(bǔ)充,3藥共用,使心臟陰陽得和,也加強(qiáng)心的生血以及行血的功能,并進(jìn)一步補(bǔ)充肝腎之陰,達(dá)到氣血而和,腦竅為之而通,疾病因之則愈。
3 典型病案
李某,男,74歲,2018年7月31日初診。主訴:雙下肢乏力8年。患者自述8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xiàn)雙下肢乏力,無頭暈頭痛,無口角流涎,無視物旋轉(zhuǎn),予以湖南省中醫(yī)附一就診,CT提示:腔隙性腦梗死,予以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效果欠佳。慕名求助李老,刻診:患者形體消瘦,面色少華,雙下肢肢體乏力,行走欠穩(wěn),視物模糊,納寐欠佳,二便可。舌紅苔薄白,舌上可見裂紋,伴瘀點(diǎn)。脈細(xì)。西醫(yī)診斷:腦梗死后遺癥期,中醫(yī)診斷:中風(fēng)病。辨證:肝腎陰虛型。治療予以補(bǔ)肝益腎,配合滋養(yǎng)心陰法等對癥支持治療。藥用:西洋參、茯苓、麥冬、五味子、桑枝、石斛、天花粉、生地黃、北沙參、葛根、烏梅各10 g,黃芪15 g,甘草5 g,7劑,日1劑,分早晚2次水煎溫服,囑其補(bǔ)充睡眠,飲食清淡,少食辛辣刺激油膩之品。
二診(2018年8月7日):患者述雙下肢乏力感較前好轉(zhuǎn),感麻木,余未見明顯不適,于上方加僵蠶、木瓜、川牛膝各10 g以加強(qiáng)通經(jīng)活絡(luò)之效。繼續(xù)7劑水煎溫服。
三診(2018年8月14日):患者述雙下肢乏力感較前明顯減輕,行走可,納寐可,二便調(diào)。舌紅,苔薄白,舌上裂紋變淡,瘀點(diǎn)減少,脈細(xì)。繼續(xù)予以上方加減調(diào)理。
按:本案中,患者雙下肢乏力8年,CT示:腔隙性腦梗死,屬于中風(fēng)后遺癥期范疇。患者年老體衰,肝腎功能衰退,以致陰精不能充分滋潤腦竅,氣血得不到充分的補(bǔ)充,出現(xiàn)腦部神經(jīng)功能受損,從而引起雙下肢肢體不能得到充分的濡養(yǎng),呈現(xiàn)出雙下肢乏力,行走欠穩(wěn)等癥狀;另體陰陽失調(diào),陰液的相對匱乏,面部血管以及肌肉失于滋養(yǎng),以致面色少華及全身消瘦;舌紅苔薄、裂紋舌、脈細(xì)亦是肝腎虧虛之癥。多數(shù)醫(yī)家遇此常投以滋補(bǔ)肝腎之品,然收效欠佳,李老創(chuàng)新性認(rèn)為,心是人體的一身根本所在,對待肝腎陰虛型中風(fēng)患者單從肝腎入手難以取得滿意療效,在此基礎(chǔ)上極力加強(qiáng)心陰的補(bǔ)充,可以取得事半功倍。方中以生地黃、北沙參、烏梅大量滋陰藥補(bǔ)充肝腎虧損之陰,輔之以石斛、天花粉以益脾胃之陰,黃芪、茯苓健脾胃之氣,補(bǔ)后天以助先天,收效更佳;配合生脈散之西洋參、麥冬、五味子三味滋養(yǎng)心陰,既補(bǔ)充虧損之陰液又加強(qiáng)心臟之功能;以桑枝、葛根舒經(jīng)活絡(luò),使藥效上至頭顱,下達(dá)下肢;最后佐以甘草調(diào)和諸藥。諸藥共用,使陰液得補(bǔ),陰陽平和,腦竅得通,下肢得養(yǎng)。二診患者自述雙下肢乏力癥狀較前好轉(zhuǎn),伴有麻木,表明此方療效可觀,然病程日久,下肢頑疾,藥力難以速下,遂加強(qiáng)通經(jīng)活絡(luò)之效,加用僵蠶、木瓜通經(jīng)活絡(luò),且加川牛膝補(bǔ)肝腎,引藥下行。三診時(shí)患者癥狀較前明顯好轉(zhuǎn),未訴行走欠穩(wěn),舌上瘀點(diǎn)逐漸減退,故繼續(xù)以上方鞏固治療。
4 小結(jié)
現(xiàn)代醫(yī)學(xué)將腦梗死按照發(fā)病時(shí)間分為腦梗死急性期、腦梗死恢復(fù)期、腦梗死后遺癥期三個(gè)階段,對于腦梗死治療上主要以抗凝、抗血小板聚集、護(hù)腦等為主,以改善腦循環(huán)、腦缺血損害,恢復(fù)腦神經(jīng)功能、防止復(fù)發(fā)以及減少并發(fā)癥。在中醫(yī)方面,從古至今困擾無數(shù)醫(yī)家,李老推陳出新,提出滋養(yǎng)心陰法的應(yīng)用,將心與腦融為一體,護(hù)腦的同時(shí)不忘強(qiáng)心,強(qiáng)心的同時(shí)鞏固護(hù)腦,以共奏治療之效。李老認(rèn)為,中風(fēng)所出現(xiàn)的舌強(qiáng)不語、半身不遂甚至昏撲等癥狀,中醫(yī)可歸納為神機(jī)失用的表現(xiàn),心主神明,《靈樞。·本神》:“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問·靈蘭秘典論》云:“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思謂之意……”,充分表明心臟統(tǒng)領(lǐng)五臟六腑;腦主精神意識(shí),調(diào)控全身的意識(shí)活動(dòng),為“元神之府”,張錫純所著《醫(yī)學(xué)衷中參西錄》中開創(chuàng)性提出“神明之體藏于腦,神明之用發(fā)于心”之說,即“心腦共主神明”[8]。心統(tǒng)領(lǐng)一身之氣血運(yùn)行,腦指導(dǎo)五臟六腑的意志表現(xiàn),心腦共用,心腦共治。以補(bǔ)肝益腎法為主,常加西洋參、麥冬、五味子為主的生脈散[9],共奏滋陰養(yǎng)血、護(hù)腦養(yǎng)心之效。若頭暈甚者,加天麻、鉤藤止眩;若失眠多夢者,加百合、夜交藤、合歡花清心安神;若病程日久,肢體偏癱更甚者,常用僵蠶、蜈蚣、水蛭等蟲類藥搜風(fēng)通絡(luò)。另李老尤其強(qiáng)調(diào)養(yǎng)生之法,倡導(dǎo)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合一,叮囑患者加強(qiáng)太極拳、八段錦、易筋經(jīng)等中國傳統(tǒng)功法的使用,現(xiàn)代多項(xiàng)研究[10-11]證明,健身功法能有效緩解患者的神經(jīng)及心血管系統(tǒng)的調(diào)節(jié)功能,也利于血液循環(huán)以及組織肌肉的恢復(fù)。但李老強(qiáng)調(diào)在練習(xí)功法之時(shí)需調(diào)息平心,配合呼吸,否則難以達(dá)到成效。
中風(fēng)病機(jī)繁多,病癥諸多。對于肝腎虧虛型中風(fēng),李老遵循詢證論治,謹(jǐn)遵病因病機(jī)治療原則,在補(bǔ)肝益腎的前提下通過運(yùn)用滋養(yǎng)心陰法,既加強(qiáng)心臟功能,使之主血行血功能得到充分的發(fā)揮,也有效的補(bǔ)充了肝腎虧虛之陰,達(dá)到治療疾病的目的,這也符合中醫(yī)陰陽理論。不過目前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研究人群較為局限,臨床樣本數(shù)量不多,后期會(huì)進(jìn)行多樣本臨床數(shù)據(jù)分析以及動(dòng)物模型試驗(yàn),以進(jìn)一步明確其作用機(jī)制,為臨床辨證論治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