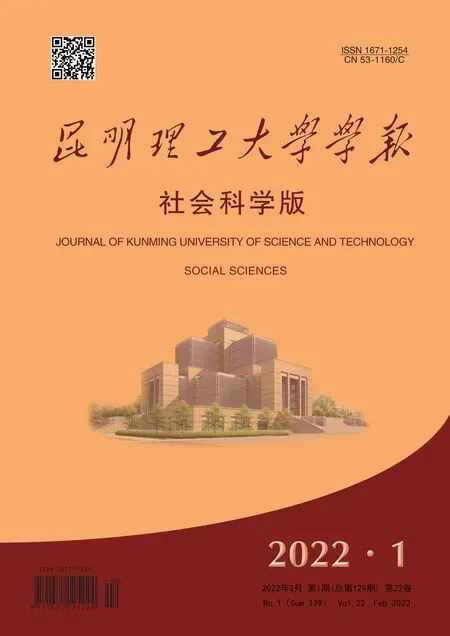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自然犯化研究
盧義穎
(昆明理工大學 法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生態環境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1]。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等重要理念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刑法作為規制生態環境資源犯罪這一最嚴重的生態環境資源違法行為的后盾法,毋庸置疑地涵蓋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之中。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從單純法定犯向“自然犯化”的轉變,將成為新時代生態環境刑事立法與司法的必然發展方向。結合一起公益性公墓非法占用農用地案,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展開實證剖析,筆者發現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的誤解會導致司法實踐陷入邏輯怪圈,故有必要予以澄清。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的準確定性關乎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法益保護和社會危害性確定的精準性,對生態環境資源違法行為在罪與非罪的界定上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也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立法體例完善提出了時代性的迫切需求。
一、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的立法與司法現狀
在“五位一體”社會主義建設總布局不斷向縱深發展的進程中,不少地區仍不可避免地面臨著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或資源匱乏之間的客觀矛盾。如何在生態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找準平衡點,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的現實考驗。這一考驗延伸至法治領域,則體現在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的立法理念、執法水平和司法智慧等具體方面。以生態環境資源犯罪中較為常見的非法占用農用地為例,實踐中常出現為盡快實現城市化建設等目的而未批先建、未批先占情形,這些情形是否構成犯罪的實踐之爭亦此起彼伏。例如,某市某城市中心公園建設非法占用林地、某縣某公益性公墓建設非法占用林地等案件,均是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管理機制與發展需求錯位而引發的法律問題。從形式上看,這些案件中的行為均已構成犯罪。但是,從實質上看,如果簡單機械地進行歸罪則可能會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并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也不利于良法善治的健全與完善。這些爭議的產生與生態環境資源犯罪被作為法定犯規定在《刑法》分則“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的立法現狀關系甚密,且多圍繞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屬性問題展開。
(一)立法現狀
犯罪屬性分為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源自“本質惡”“自體惡”,是違反社會倫理道德的犯罪,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成為刑事處罰的對象,如殺人、強奸、搶劫、盜竊等。法定犯,又稱行政犯,源自“禁止惡”“他禁惡”,是根據某一時期刑事政策需要,由特定法律將某一類行為納入刑事處罰對象的犯罪[2]76-93。法定犯與自然犯并非非此即彼的劃分。就我國現行刑法規定來看,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兼具法定犯和自然犯屬性,但因其規定在《刑法》“破壞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從立法體例上更強調其法定犯屬性。首先,“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一節16個罪名中有12個都以“違反國家規定”“違反XX法規”“未經XX許可”等空白罪狀開頭,均為法定犯的罪狀描述特點。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向縱深發展,在“國家規定”“XX法規”的援引上,有關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的法律,如《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等,以及有關保護、治理和合理開發自然資源的法律,如《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礦產資源法》《漁業法》等,組成了獨立的法律部門——環境資源法[3]。這些環境資源法在“法律責任”的相關條文中會出現“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的表述。該條文并不因此成為附屬刑法,而是對有關生態環境資源違法行為進一步追究刑事責任的宣示性、指引性條款,即我國現行生態環境資源刑法立法體系中并不包括附屬刑法。這些條款需要指引到刑法分則中生態環境資源刑法對應的條款,符合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構成要件時,才能追究刑事責任。其次,從各罪的具體罪狀看,一般都加入了“污染環境”“破壞野生動物資源”“農用地大量毀壞”“礦產資源大量毀壞”等直指生態環境資源實質法益的特別罪狀,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自然犯屬性得以彰顯。需特別指出的是,多個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罪名中規定的“情節嚴重”這一特別罪狀,是指環境被污染或資源破壞等危害后果的情節嚴重,而非違反某個環境行政管理秩序的情節嚴重。
(二)司法現狀
2010年以前,我國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從立法到司法均呈現出輕刑化特征,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抗制長期處于“不嚴不厲”狀態[4]。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首次在國家層面明確了生態環境刑事司法政策的從“嚴”導向。根據“寬嚴相濟”總刑事政策的內涵,這里的從“嚴”,應是“法益保護的絕對從嚴”與“行為懲罰的相對從嚴”的有機統一,即在生態環境法益得到有效救濟的情況下,可以適度放寬對行為人懲罰的門檻和幅度。近10年來,司法機關逐漸加大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從嚴懲處力度,為生態環境提供了強有力的司法保障,但也出現了一些矯枉過正的現象,即過于強調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對生態環境管理秩序的破壞,而不問生態環境法益本身是否產生實質破壞的結果,忽視了該類犯罪的自然犯屬性,導致不宜認定為犯罪的違法行為被苛以刑罰。例如,某公益性公墓非法占用林地案的實踐之爭,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認定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具有一定典型意義。2011年,根據農村殯葬改革要求,某社區居委會依上級指示選擇轄區內土地“小山包”作為公益性公墓建址上報,獲某縣民政局同意,縣規劃、國土等部門均簽章同意建設,縣林業部門簽章同意建設但要求完善相關占用林地手續。某社區居委會向縣林業部門預交50畝林地植被恢復費5萬元。隨后,該社區居委會委托他人對部分土地進行平整。2012年,該社區居委會申報擴建,某縣民政局同意再增加170畝用地。2016—2017年,該社區居委會在市、縣民政部門督促下開始建設公益性公墓主體工程,201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2018年,林地督察發現涉案公益性公墓存在違法占用林地情況,經鑒定,非法占用林地99畝,其中40畝性質為生態公益林。該案在罪與非罪的認定上存在較大爭議:有觀點認為,未批先建行為破壞了林地占用應依法審批的行政管理秩序,具有巨大的社會危害性,只要達到法定占用面積就必須追究刑事責任。也有觀點認為,殯葬改革目的就是要移風易俗,建設公益性公墓本身帶有公益性,雖然未批先建,但社會危害性較小,不宜追究刑事責任。還有觀點認為,根據刑法解釋論和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體現的立法精神,對這類案件應當采用實質解釋方法,僅屬于程序違法的,缺乏刑法上的實質社會危害性,不應以犯罪論,該案屬此情形。以上爭議的焦點主要在于對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社會危害性的認識上,本質上卻是對該罪名犯罪屬性的認識和界定不同。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認識產生的偏差可能導致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社會危害性認定的偏差,從而導致一個生態環境資源違法行為在罪與非罪間產生不必要的游弋,既浪費司法成本又不能解決實質問題。筆者將結合以上案例,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法定犯化存在的弊端和自然犯化的必然性作進一步探討。
二、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法定犯化的弊端
如前所述,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兼具法定犯和自然犯特征,但在犯罪認定中過于強調對生態環境行政管理秩序的破壞,甚至將對生態環境行政管理秩序的破壞直接等同于刑事上的社會危害性,而不問實質法益侵害性或實質社會危害性,可稱之為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法定犯化,該情形會在司法實踐中帶來諸多弊端。
(一)有違刑法謙抑之原則
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法定犯化會將非犯罪行為輕易納入刑事司法程序,從而陷入多個司法邏輯怪圈。某公益性公墓案中,正是基于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法定犯化的認識,將“未經報批”所破壞的行政管理秩序認定為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的社會危害性,導致偵查機關把對犯罪主體的偵查方向鎖定在是誰導致未能報批的問題上,而忽略了是什么法益受到侵害、誰是施害人等至關重要的犯罪本質問題。偵查機關一方面認為報批義務人某社區居委會、某街道辦事處、報批經手人縣林業局以及督促推進公墓建設的市、縣民政局、縣政府都有犯罪嫌疑;另一方面又認為將多個主體都確定為犯罪主體似有不妥,僅選擇其一也有不妥,但不妥在何處又說不清、道不明,故在整個偵查階段遲遲不能確定犯罪主體,陷入了無法解開的偵查邏輯怪圈。在此基礎上,林業主管部門還提出該案只有在追究了刑事責任后,用地單位才能以該林地“必須占用”為由,重新報批以獲得審核同意,即以刑事非難性評價作為“非法用地”合法化的前提。該做法必然導致刑法適用陷入“后盾前移”的邏輯怪圈。這些邏輯怪圈既有違刑法謙抑性原則,又會造成刑事司法資源的浪費。
(二)有違依法行政之內涵
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法定犯化可能導致行政機關履職方向的偏頗,將應積極正向履行的管理職責轉化為可消極反向施行的懲罰職責,并可能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某公益性公墓案中,對“必須占用”的林地進行審批時,專業的行政主管機關負有指導并督促相對人規范報件的職責,而不是在行政相對人開始未批先建之初不監督、不指導,而在建筑完工后苛以懲罰。“報件不規范”用地就得不到審批,得不到審批用地就處于違法狀態,也就使得“必須占用”的土地無法被“合法占用”,導致土地資源被合情合理利用甚至推動文明進步的社會功能無法合法實現,從而把“報件不規范”的瑕疵行為逼入“用地違法”的行政違法范疇,進而逼入刑事犯罪的邊緣,阻卻了社會資源的合理利用與配置,也阻卻了社會文明的進步,還會導致林地等自然資源的合理化利用在良性運行的軌道上發生逆轉,使建設好的公益性建筑或設施投入使用后又面臨被拆除的風險,造成社會的資源浪費。此非依法行政應有之內涵。對此情形,行政機關并不需要移送刑事偵查,而是可以參照國土資源部《關于完善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審查報批工作的意見》第10條規定,在依最高限額收繳“植被恢復費”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行政罰款,既體現對行政管理秩序的維護,又符合責罰相當的行政處罰原則,亦回應了人民群眾一般認識上的樸素正義觀。
三、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自然犯化的必然性
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從法定犯向自然犯化的轉變,是當代生態環境資源刑事立法與司法的必然發展方向,既符合新時代生態環境倫理的內在需求,又符合刑法實質解釋的必然要求。
(一)生態環境倫理的內在需求
倫理是以善惡為表現形式的價值知識,為人們提供行為評價導向,向人們指出他們同現實世界的價值關系的方向,并提出要求解決的問題[5]。生態環境倫理以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目的,并為其提供評價導向。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治理系以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終極目標,故其倫理基礎應當遵循與人類社會進步程度相匹配的生態環境倫理。我國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產生的最根本原因是“恰當的環境倫理的缺失”[6],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打擊與預防的總體成效不佳的原因亦在于此。生態環境倫理涵蓋了自然法與人為法的共同倫理基礎,既要揭示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又要展現國家、集體、個人等主體所應遵守的與生態環境相關的倫理規范和行為準則。從“天人合一”“ 以中致和”等傳統生態文明思想到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重要理念的發展演變,正是我國樸素生態環境倫理觀歷經千年的回歸。正如陳興良教授指出的,伴隨社會倫理道德的演變,“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等法定犯越來越具有自然犯色彩”,此為法定犯的自然犯化[7]173。生態環境資源犯罪作為兼具法定犯和自然犯屬性的混合犯,其法定犯屬性日漸削弱,自然犯屬性則在日益增強[8]。
一方面,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自然犯化是人們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倫理認識演變在立法實踐中的必然產物,是生態環境倫理“人類中心主義”向“人類-生態中心主義”轉變的結果,亦是環境正義的應有內涵。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單純的利用者與被利用者的關系,而是一個復雜的生命共同體之間共生共存的關系。這種關系亙古存在,并不以某一特定時期形勢政策的需要而改變。立法者賦予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法定犯屬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我國社會發展進程中一度出現的“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理念影響的產物,是以人類對環境資源的利用、環境資源對人類的服務為前提的,故欲通過行政手段來調整人類利用環境資源的合理限度。當人對環境的利用行為超過必要限度以致打破生態平衡時,就可能被科以行政的甚至刑事的懲戒。這一認識必將伴隨 “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 新時代生態文明理念的轉變而轉變。另一方面,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由法定犯向自然犯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由單純滿足工業文明的發展轉向到滿足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歷史選擇,是一個雖然緩慢但必然發展的自覺過程,這一過程貫穿著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長期宣傳教化和人們經受環境污染、資源匱乏痛苦之后的覺醒,越來越多的人們逐漸形成一種返璞歸真的現代生活倫理——保護自然、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己;反之,破壞生態環境就是毀滅人類自身。“勿以惡小而為之”的倫理古訓,必然逐漸包含“勿以污染環境而為之”“勿以破壞環境資源而為之”的內容。相應地,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資源的行為將被大眾認為是一種惡行,一種應當自禁的惡。換言之,社會公眾不會繼續認為污染或者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具有合理性;相反,其會自覺意識到是一種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從而自覺遵守國家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信奉司法機關查處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判決結果。
(二)刑法實質解釋的必然要求
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由法定犯向自然犯轉化,并不意味著一切污染環境或者破壞環境資源的行為都應當以犯罪論處,在刑法解釋論上,還面臨著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的考量。形式解釋論提倡從刑法條文語義入手,強調犯罪構成的形式要件;實質解釋論則提倡從犯罪的本質即社會危害性入手,強調刑法的法益保護目的。在我國生態環境資源刑法體例保持現狀的情況下,更應當注重實質解釋在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司法適用中的必要性,從而推動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向著自然犯化良性發展。
實質解釋論中的“實質”是指犯罪的本質,即法益侵害性或社會危害性。在制定法與自然法(實質的正義觀念)發生沖突的時候,實質解釋論堅持優先選擇自然法(實質的正義觀念)。實質解釋只將值得科處刑罰的行為解釋為犯罪行為[9]。實質解釋不贊成單純以行為方式或者手段本身來考慮犯罪構成,而是基于特定背景下行為與法益侵害的關系來明確行為的意義,從而確定對其進行刑事非難的必要性。如果“將特定的行為手段本身作為禁止對象”,就意味著無論侵害結果發生與否該行為都不得實施,“這顯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自由”[10]。從這一角度出發,一個生態環境資源違法行為的法益侵害性界定關乎該行為應否確定為犯罪的法律后果。對生態環境資源違法進行行政制裁或刑事制裁所要保護的核心法益是相同的,即生態環境法益,但二者對法益保護的傾向又各有側重,行政制裁中的法益侵害性側重于行為人對環境管理秩序的違反,即形式的違法性。而刑事制裁中的法益侵害性強調的是對生態環境法益本身的侵害,即實質的危害性。切薩雷·貝卡里亞早在250多年前就一語中的地指出:“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尺,是犯罪對社會的危害。”[11]陳興良教授進而提出的犯罪本質二元論以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作為犯罪的本質特征,如果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或者社會危害性沒有達到一定程度,就根本不存在刑事違法性與應受懲罰性的問題[7]155-159。從生態環境行政違法向犯罪轉化的唯一條件,就是“社會危害性加劇到足夠嚴重之程度”[2]76-93。因此,生態環境行政違法與生態環境資源犯罪中的社會危害性應屬同質,僅是在程度上有所區別,可統稱為生態環境資源違法的社會危害性,其核心就體現在生態平衡的破壞上,即本質上是一種自然秩序的破壞。
傳統刑法理論視域中刑事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被越來越多的人解讀為法益侵害性。生態環境資源犯罪之所以具有社會危害性,其實質在于生態環境法益的侵害性,有的學者表述為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本質,認為生態環境資源犯罪不僅侵害以人為主體的環境權益,而且侵害全體公民生存發展環境權[12];也有學者認為,生態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結合,使環境要素法益與環境管理秩序法益共同構成環境法益,這是一種可以獨立的法益類型,生態環境資源刑法保護的不再是如生命、健康、財產等具體的個人法益,而是社會主體共同享有的一種利益[13]。正是這種法益觀的發展深化,不僅推進了生態環境刑事立法的發展,使生態環境資源刑法具有了法定犯與自然犯相混合的特點,而且揭示了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由法定犯向自然犯變化的脈絡,為理論上的解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決定了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的解釋,不應繼續停留在現行刑法所強調的環境資源管理秩序上。質言之,過去那種關于生態環境資源刑法所保護的資源環境管理秩序所包含的行政審批秩序要素,在依照行政實體法的內在邏輯應當獲得審批許可時,應當被實質上的生態環境主體利益要素所取代。
具體到某公益性公墓案中,其實質社會危害性是什么呢?首先,從法條文意看,根據《刑法》第342條規定,某一非法占用林地的行為入罪,需與《森林法》第44條相銜接。該罪名中,農用地(林地)被毀壞是入罪的核心實質要件,而區分行政違法與犯罪的層次性標準則是 “大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林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規定進一步強調了該罪名構成的特別罪狀為“非法占用并毀壞”,且進一步將“毀壞”解釋為“造成林地的原有植被或林業種植條件嚴重毀壞或者嚴重污染”。根據《森林法實施條例(2018修正)》第43條的規定,如果出現未經審核同意就改變林地用途的情況,縣級以上林業主管部門將責令限期恢復原狀。“限期恢復原狀”以保持林地用途為前提,這里的“改變用途”就應當具有實質毀壞性。因此,認為只要是未批先建且占用林地面積達到法定數量就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觀點,顯然忽略了“毀壞”林地或林木這一實質性違法情節。其次,從法益保護看,生態環境資源犯罪侵犯的法益不是單純的生態環境行政管理秩序,而應是生態環境法益,即地球上一切構成物的個別利益以及他們相互關系中所體現的利益。具體到該案罪名中,就是林業資源及其與人類或其他生物相關的利益,包括林地上原有動植物的生命或土地的林業種植條件。正如另一觀點指出的,涉案土地被改變后的用途是建設公益性公墓,故為《森林法》第18條規定的“必須占用”的林地,無論是否辦理許可,最終結果是必須占用,必須鏟除原有植被、必須改變原林地用途。換言之,該案并不存在要通過行政或刑事處罰來恢復林地用途的實質必要性。因此,沒有辦理審批手續,僅具有行政違法性,而不具有刑事違法性。而《森林法》第44條規定的以開墾、采石等活動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毀壞的行為,應是指非必須占用林地的行為,即使報批也不能得到審批,其與本案中的“必須”占用行為具有本質區別,其對林業資源的毀壞才是實質性毀壞,當毀壞達到足夠嚴重的程度時,將受到刑事處罰。進言之,具備向刑事違法轉化的條件是實質性毀壞林業資源的行為,而非“必須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而未批先占的行為。再次,從社會危害性本質看,涉案公益性公墓的建設包含兩個重大的社會公共利益:一是實現森林資源的集約化管理與更加合理的利用,讓以往因私埋亂葬所損害的林業資源得以自然恢復,更好地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二是移風易俗,鼓勵人民群眾形成新的善良風俗,推動社會文明進步。公益性公墓的建設從表象上看似乎是破壞了某一特定范圍的林業資源,但在本質上,其不僅是將國家著力推行的殯葬制度改革要求落到實處,也是對更廣范圍的林地資源進行深層次保護。該利益保護與生態環境資源刑法意欲保護的法益不謀而合,不但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反而在生態資源和公序良俗的保護上具有重要而積極的社會意義。正因如此,公益性公墓用地從一開始也就具有了“必須占用性”,與“毀壞”具有本質上的區別,并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反推之,如果涉案公益性公墓的建設具有 “社會危害性”,那么,就須根據法律規定“限期恢復原狀”,須把已經建設的公益性公墓拆除,恢復林地性質。這將導致國家推行的殯葬改革制度無從落實,倒逼村民回到以往私埋亂葬的狀態,使森林資源回到粗放型利用狀態,顯然不符合生態環境資源刑法的立法本意。因本案不具有實質社會危害性,亦就不存在刑事違法性與應受刑事懲罰性,故不構成犯罪。基于以上分析,能夠充分反映出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自然犯化在司法實踐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四、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自然犯化的立法完善與司法考量
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自然犯化的發展方向對生態環境資源刑事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司法領域應當更加注重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對生態環境法益的實質性危害審查和認定。故有必要在立法上較為清晰地將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法定犯屬性進行弱化,并加強其自然犯屬性的立法呈現,避免產生更多的實踐認識誤區。
(一)立法體例的完善
刑法調整因犯罪而產生的社會關系[14]。生態環境資源刑法作為刑法分則中的一項專門刑法,所調整的主要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我國生態環境資源刑法在立法體例上的位階較低,未能凸顯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的時代性變遷。生態環境資源刑法從屬于妨害社會秩序罪一章之中,忽略了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從法定犯向自然犯的逐步轉變的特征,使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在體例上停留于單純的法定犯層面。這易造成在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上過分強調對生態環境管理秩序的破壞,而未能體現對生態環境法益的實質化保護,不符合現代環境正義的內在要求以及生態環境資源刑法的發展方向。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在立法體例上應當獨立成章,一方面是要實現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從法定犯向自然犯的逐步轉變,為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本質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則是要順利實現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法益的實質化保護,將生態環境刑事政策從“嚴”的實質性體現在生態環境刑事立法與司法中。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獨立成章后,生態環境行政違法依然可以作為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構罪的客觀條件之一,作為環境或自然資源的利用行為在行政合法與行政違法上的區分界限,為生態環境行政違法向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過渡“創造”行為基礎,但不能作為確定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社會危害性的實質條件,更不宜作為生態環境資源犯罪中單獨或主要的法益給予刑事后盾保護。
(二)司法謙抑的考量
刑法的謙抑性,又被稱為刑法的經濟性或節儉性。具言之,運用刑法手段解決社會沖突,應當具備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危害行為必須具有相當嚴重程度的社會危害性;第二,作為對危害行為的反應,刑罰應當具有無可避免性[7]6-7。以此為標準,生態環境領域的刑事司法應當回歸到“生態環境法益是否受到嚴重侵害”這一實質社會危害性的必要評價上,充分考量刑罰對某一生態環境資源違法行為有無可避免性。在司法中強調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自然犯化屬性,看似提高了入罪門檻,似有從“寬”之意,實則不然。以某公益性公墓案為例:其生態環境資源違法行為所引發的社會沖突,并未達到需以刑事司法活動來解決的程度,若以犯罪論之則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在生態環境資源刑事司法中強調自然犯屬性,僅是實現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本質的回歸,并未提高入罪門檻,而是在保持原入罪門檻的基礎上,厘清法律適用的路徑,避免造成罪與非罪界限的混淆,讓生態環境資源刑法在司法實踐中更加精準地發揮制裁和預防生態環境資源犯罪、保護生態環境法益的效能。概言之,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強自然犯屬性以其看似“從寬”的表象,在根本上詮釋了生態環境資源刑事司法謙抑的重要價值以及生態環境資源刑事政策中“保護的絕對從嚴”與“懲罰的相對從嚴”的深刻內涵。
五、結論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出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體”重要論斷,從兩個層面對“生命共同體”進行了界定,既彰顯了“自然”作為“生命共同體”的本質特征,又強調了人是自然生命共同體的一員。具言之,在第一個層面上,“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構成“自然”的基本環境資源要素,它們共同孕育了動物、植物及微生物等無數鮮活的生命體,這些生命體與其賴以生存的環境資源相互依附、共生共存,因而構成了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為代表的“自然生命共同體”。在第二個層面上,人基于動物的自然屬性,本身已包含在這個自然生命共同體中,但人作為“高級”動物,具有強烈的主觀能動性,在生命活動中,具有打破自然生態平衡的巨大的現實可能性。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就是要提醒人們,人只有時刻把自己放進自然生命共同體中,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如前所述,生態環境資源犯罪的對象是生態環境資源,即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為代表,包括人類自身在內的自然生命共同體,而自然生命共同體繁衍生息、可持續發展的利益就是生態環境資源犯罪所侵犯的核心法益。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引領下,伴隨生態環境倫理的變遷與回歸,在歷經“改變自然、利用自然”的慘痛教訓之后,生態環境資源犯罪屬性的自然犯化作為一種必然的發展方向,甚至成為順應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其不僅關乎生態環境資源違法時罪與非罪的界限,也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進程中生態環境保護立法、執法、司法的諸多理論與實踐問題,更關乎人類命運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的可持續發展;既是生態環境資源保護法網的織密,也是生態文明建設及生態環境資源治理現代化的應有內涵,更是社會文明進步與生態環境治理同頻共振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