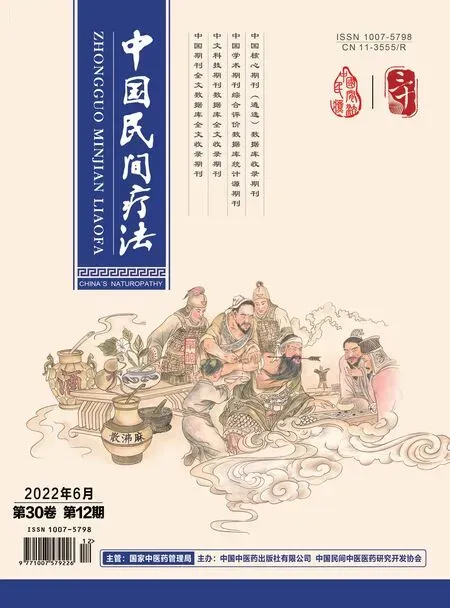感染后腸易激綜合征的機制研究與治療展望※
韓紅偉,惠鑫蓉,路霄健,指導老師:魏峰明
(1.山西中醫藥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4;2.山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D)與早期腸道感染呈正相關。大部分腸道感染患者好轉較快且無腹痛等后遺癥,但有部分患者有持續性腹部癥狀,符合IBS-D診斷標準,即為感染后腸易激綜合征(post-infectious irritabIe bowel syndrome,PI-IBS)。該病在腸易激綜合征患者中占絕大部分,且易反復,治愈難度大。本文綜合國內外有關PI-IBS的研究進展,從PI-IBS的現代研究概況、發病機制及中西醫治療等方面進行綜述。
1 PI-IBS概念及發病機制
1.1 PI-IBS概況 臨床發現部分急性胃腸道感染患者康復后仍間歇出現腹痛、排便頻次增加、糞質稀薄等IBS癥狀,即PI-IBS[1]。1950年英國學者STEWART[2]提出前期胃腸道感染與IBS的相關性,此后PI-IBS成為研究熱點。IBS發病率為11%,其中PI-IBS患者約占10%[3]。隨著該病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常見的主要健康問題之一[4]。
1.2 PI-IBS發病機制 PI-IBS的病理生理機制包括腸道持續存在的低度炎性反應、菌群失調、黏膜通透性增加、感覺運動障礙、免疫功能障礙、內臟感覺高敏性等腸道功能紊亂癥狀及腦-腸軸互動異常、心理精神因素等[5]。
(1)低度炎癥/免疫激活與腸道黏膜改變 多項前瞻性研究和Meta分析證實,胃腸道感染會直接導致功能性胃腸病的發生,研究證實,胃腸道感染與IBS呈強相關性,胃腸道炎癥參與PI-IBS的發病[6-7]。當腸黏膜存在低度炎性反應時,腸黏膜屏障受損,通透性改變,抗原進入機體激活免疫系統,免疫細胞相互作用,通過腦-腸軸使腸道敏感性增加導致腹痛、腹瀉等IBS癥狀[8-9]。WANG H等[10]通過研究旋毛蟲感染的小鼠和HALLIEZ M C等[11]關于賈第蟲感染大鼠的研究也支持腸黏膜屏障損害與內臟痛覺過敏之間的關系。
馬俊杰等[12]通過對60例中醫診斷為肝郁脾虛證、肝氣郁滯證、脾胃虛弱證,西醫診斷為PI-IBS的患者按證型分別檢測輔助型T細胞1(Th1)[γ-干擾素(INF-γ)、白細胞介素-2(IL-2)]、Th2(IL-4、IL-5)指標,發現PI-IBS患者相對健康人Th1/Th2左偏,PI-IBS證型與Th1/Th2漂移相關,如實證患者細胞免疫較強,Th1/Th2左偏,而虛證患者則偏于體液免疫,Th1/Th2右偏,該結果為臨床中該病的診治和預后提供了新的科學依據。
(2)腸道菌群失調與內臟高敏感性 腸道炎癥影響腸道內環境的穩定,腸道菌群失調可提高內臟敏感性,加重腸道病理反應。李倩等[13]研究顯示,PI-IBS患者內皮素(ET)、一氧化氮(NO)平衡破壞,導致腸道黏膜屏障功能障礙。研究表明,腸道功能障礙可影響腸腔內液體和電解質的轉運及腸道菌群,從而引起內臟痛覺過敏和排便習慣的改變[14-15]。
近年來,研究發現IBS患者有明顯的腸道菌群紊亂。張定國等[16]認為其主要原因是雙歧桿菌和乳桿菌等生理性優勢菌減少,致病性腸桿菌和腸球菌明顯增多,并且證實通過補充外源性的雙歧桿菌能有效治療IBS,攜帶IL-10基因的雙歧桿菌(BL-hIL-10)治療IBS具有雙歧桿菌和IL-10的雙重優勢,預測其可能成為治療IBS的有效方法。WANG H等[17]研究證實,在PI-IBS小鼠模型中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聯合應用可抑制促炎細胞因子IL-6和IL-17的表達,促進主要緊密連接蛋白Claudin-1和Occludin的表達,從而減輕內臟高敏感性,促進腸屏障功能恢復和炎癥的減輕。
PI-IBS患者通常為內臟高敏感性。腸嗜鉻細胞和5-羥色胺在內臟痛覺過敏的發生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腸嗜鉻細胞受Th1/Th2主導環境的影響。SHI H L等[18]證實,朝鮮薊素對三硝基苯磺酸法(TNBS)誘導的PI-IBS內臟高敏感大鼠的鎮痛活性是通過降低細胞因子水平介導的,可能為腸易激綜合征的內臟高敏感性提供有前景的治療途徑。
(3)心理精神因素 心理共病患者患PI-IBS的風險增加,可能是由于對免疫白蛋白(Ig)E的易感性增加和Th2免疫偏移[19]。長期反復的胃腸道不適會導致患者頻繁就醫,加重其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導致PI-IBS癥狀遷延不愈[20]。
2 PI-IBS的中西醫治療
中西醫治療疾病都是從“證”“癥”而治,相似而有各異。中醫辨證論治,從肝、脾、肺入手,環環相扣,調理至陰平陽秘、營衛相合、三焦通達的狀態,從而緩解腹部不適癥狀,達到治療目的。西醫對癥治療,通過藥物調節腸道菌群,恢復腸道屏障,降低內臟高敏感性,恢復腸道正常的生理狀態,以期達到治療效果。
2.1 中醫辨證論治 PI-IBS臨床癥狀多與IBS-D一致,以腹痛、腹脹、泄瀉為主,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將相關病證統稱為“泄瀉”“腹痛”[21]。《中國臨床診療術語》明確IBS病名為“腸郁”。《現代中醫臨床診斷學疾病》指出“腸郁”是“是情志不舒,氣機郁滯,使腸道運化失常,以腹痛、腹瀉或便秘為常見表現的郁病類疾病”。《醫方考》載:“瀉責之脾,痛責之肝,肝責之實,脾責之虛。脾虛肝實,故令痛瀉。”IBS的主要證型中,實證多為肝氣郁滯證,虛證多為脾胃虛弱證,虛實夾雜多為肝郁脾虛證。此外,脾虛濕蘊、脾胃濕熱、中焦虛寒也是該病常見證型。
(1)補柔兼施,疏肝健脾 《丹溪心法》提出和解劑痛瀉要方主要功效為補脾柔肝、祛濕止瀉,主治脾虛肝旺之泄瀉[22]。MA X X等[23]研究表明,痛瀉要方通過減輕行為痛覺過敏和止瀉以改善PI-IBS癥狀,其潛在機制涉及對激活黏膜肥大細胞、下調類胰蛋白酶和即刻早期基因(c-Fos)表達及降低血清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和組胺水平的抑制作用。王宏飛[24]證實痛瀉要方聯合整腸生治療PI-IBS,療效較好。田奧飛等[25]證實,白術、防風藥對對PI-IBS大鼠腸機械屏障具有不同程度的保護作用,兩藥合用起協同增效作用,其對腸機械屏障的保護機制可能是通過降低相關炎癥因子IL-6、IL-8的水平,上調黏液蛋白Mucin-1、Occludin、緊密連接蛋白Claudin-1的表達。
(2)溫胃調腸,養血護本 腸胃氣血不足和失調使胃腸道功能處于相對失活狀態,久之虛者更虛,功能趨于停滯狀態,唯有從養血護本入手,溫胃調腸,方可恢復正常的腸胃功能。楊梅等[26-27]證實,溫胃調腸顆粒(組成:柴胡、白芍各6 g,川芎10 g,白術9 g,甘草片5 g)可有效改善IBS患者癥狀,提高腸道活性,恢復其正常功能。楊梅等[28]首次證實,溫胃調腸顆粒能改善PI-IBS大鼠模型的內臟高敏感性及腸運動障礙。CHEN Y等[29]研究發現,烏雞丸能通過調節腸道微生物群和穩定腸道黏膜屏障以緩解IBS,從而改善腹痛、結腸動力異常和內臟高敏感性,其機制可能是通過增加黏蛋白的釋放、上調緊密連接蛋白Occludin和ZO-1的分布及下調結腸上皮細胞肌球蛋白輕鏈激酶(MLCK)的表達,從而促進結腸黏膜杯狀細胞的增殖。這表明應用有益生元作用的傳統中藥配方不失為治療IBS的選擇。
《醫宗金鑒》載:“名生姜瀉心湯者,其義重在散水氣之痞也。生姜、半夏散脅下之水氣,人參、大棗補中州之土虛,干姜、甘草以溫里寒,黃芩、黃連以泄痞熱。備乎虛、水、寒、熱之治,胃中不和下利之痞,未有不愈者也。”黃罡等[30]研究證明,中藥復方生姜瀉心湯顆粒(由生姜15 g,黃芩12 g,半夏、黃連、干姜、炙甘草各6 g,黨參12 g,大棗8 g等組成)可明確緩解PI-IBS效應,療效與美常安相當,可通過穩定肥大細胞,調節炎癥介質的釋放,達到治療PI-IBS的目的。
(3)理氣化濕,調運中焦 中焦氣滯濕阻,脾胃難以運化腐熟,則腸道氣機難以調達,故腹部不適癥狀明顯,臨床可通過理氣化濕,以調運中焦,恢復有序的腸道功能。劉瑤等[31]研究證實,廣藿香油可通過增強腸黏膜分泌型Ig A(SIgA)分泌,抑制細胞間黏附分子-1(ICAM-1)蛋白表達,改善腸黏膜免疫屏障功能,對PI-IBS大鼠腸黏膜機械屏障和免疫屏障具有保護和調節作用,但其藥理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機制尚待深入研究。韓棉梅等[32]認為腸黏膜屏障功能及腸敏感性的增強與炎癥、緊張情緒密切相關,并通過研究發現,結腸靈(廣東省名中醫潘錦瑤教授經驗方。由黨參片、茯苓、火炭母、糯稻根各15 g,白花蛇舌草30 g,黃連片、素馨花各10 g,白芍、枳殼各12 g,甘草片6 g組成)可能通過抗感染、免疫調節和抗焦慮作用,修復結腸黏膜屏障,從而治療PI-IBS。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結腸靈中君藥黨參的成分苯丙苷類可抗感染和抗焦慮,芍藥總苷有免疫調節作用和抗感染作用[33-35]。
2.2 中醫外治法 中醫外治法不外乎通過針灸、推拿、艾灸、貼敷等療法以調理氣機、健運脾胃,三焦疏通,則腸道不適癥狀也極大程度地得到緩解。李浩等[36]應用臍灸療法治療肝郁脾虛型腸易激綜合征肝郁脾虛證患者30例,治療4周后,臨床有效率高達93.3%,且此法無創無痛,患者依從性高。陳亮亮等[37]應用脾胃培源方穴位貼敷治療IBS-D,治療4周后治療有效率優于西藥組。裴麗霞等[38]研究發現,電針“天樞”可能通過改善結腸肥大細胞活化(MC)狀態、降低P物質(SP)表達,改善大鼠內臟高敏感狀態。另外,推拿按摩治療腹部疼痛也有明顯療效。如張國忠等[39]通過按壓患者鳩尾結合指揉氣海、建里、中脘等及摩腹、運腹分推等手法治療IBS-D取得了顯著療效。可見,中醫外治療法可舒筋通絡活血,通則不痛,榮則不痛,且此類療法操作便捷,又無明顯不良反應,患者較易接受。
2.3 西醫對癥治療 目前,臨床對感染后功能性胃腸病如PI-IBS的治療與羅馬Ⅳ診斷標準下功能性胃腸病的治療手段相同,在解痙、止瀉、抗抑郁治療等對癥治療的同時予以飲食調整[6],必要時采用心理干預療法。JIN Y等[40]研究發現,利福昔明不僅可減輕內臟高敏感性,恢復腸屏障功能,抑制腸易激綜合征小鼠模型結腸和回腸輕度炎癥,而且對該模型小鼠腸道微生物群的整體組成和多樣性影響極小。季夢辰等[41]進一步研究證明,利福昔明聯合復合乳酸菌膠囊治療PIIBS安全有效。張定國等[16]證明,口服BL-hIL-10可緩解PI-IBS小鼠炎性反應,可能是通過調節Th平衡實現的。
張玉春等[42]聯合應用槲皮素與5-氨基水楊酸(5-ASA)治療PI-IBS,證實其可降低內臟痛覺過敏和結腸運動障礙,并認為機制可能與槲皮素抑制腸道N-乙酰基轉移酶(NAT),減少5-ASA代謝有關,為解決臨床應用5-ASA時藥物有效濃度低、不良反應明顯等問題,提供了一種新型藥物組合。趙軍艷等[43]應用胃腸安丸聯合活菌制劑治療PI-IBS患者76例,發現二者聯合能在緩解腹痛的基礎上調理腸道菌群失調,療效優于單用馬來酸曲美布汀治療。肖記平[44]研究發現,匹維溴銨聯合微生態制劑治療PI-IBS的療效優于單用其中一種的療效,匹維溴銨發揮控制癥狀的作用,微生態制劑能夠增加益生菌,二者相得益彰。
4 小結
PI-IBS的西醫治療為對癥治療,可緩解患者當前不適癥狀。中醫辨證論治從多系統、多理念入手,辨證論治,隨癥加減,主張個體化診療。其中中成藥種類繁多,臨床亦可隨證施以藥物,效果更佳。但由于飲食不節、情志不暢及治療不徹底等多種因素使PI-IBS在治療上仍存在病情遷延不愈、易復發,且發病率漸趨升高等特點,如何有效地將中西醫療法相結合,在臨床上尋找患者依從性高、痛苦小且療效佳的療法仍需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