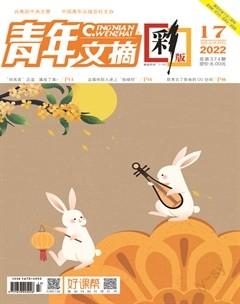讀書的四種境界
羅翔

在書籍中逃避世界
我很喜歡《納尼亞傳奇》的作者C.S.路易斯,他小時候就沉迷閱讀,自認為書中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更真實。路易斯把書籍當作這個世界上最安全、最溫暖的避難所,能夠保護自己的心智,遠離生活的種種凄苦。
但路易斯在書中搭建的美好世界,隨著母親的病逝轟然倒塌。書籍并沒有為他提供真正的庇護,當他從想象的世界中走出來,依然要面對這個令人心碎的世界。
如果書籍只是逃避世界的工具,那么,當你走出書房,會發現自己還是那個無能為力的懦弱之輩,這難道不是一種自我欺騙嗎?
在書籍中營造世界
也許對完美的追求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出廠設置,每當我們遇到不完美,就會激活這種本能,在書籍中想象和營造一種完美。可想象畢竟只是想象,在書籍中獲得的完美,在現實世界中依然不完美。
我時常反省自己,我讀很多反映戰亂、饑荒、貧困的書籍時會流淚,進而獲得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我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就自我感覺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但是我付出實實在在的幫助了嗎?
遠藤周作在《沉默》一書中有一句話很扎心:“罪,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如盜竊、說謊。所謂罪,是指一個人通過另一個人的人生,卻忘了留在那里的雪泥鴻爪。”
如果我們只是通過閱讀營造一個假想的世界,卻不愿意走入真實的世界,并關心真實世界中他人真實的苦楚,那么,這種自我欺騙式的閱讀,其實毫無意義。
在書籍中理解世界
書籍可以拓展作為個體的經驗,讓我們接軌于人類經驗的總和。每個他者都跟自己休戚相關,無論是過去的人、現在的人,還是將來的人,我們都生活在人類總體經驗的故事中,都能在他人的故事中獲得教誨。
個體雖然是獨特的,但是在人類的總經驗中,個體又并不獨特。我們經常說,每個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從個體的角度看也許是對的,但是放在人類的總經驗中,這又并不準確。
每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會讓你更多地認識自己,理解自己。
我很喜歡威廉·戈爾丁的《蠅王》,每次讀都能再次洞悉我內心深處的幽暗,覺得自己比想象中更邪惡、更幽暗、更墮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籍會讓你深刻地認識到人性的復雜;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會讓你反思科技與幸福。總之,每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是對你心靈的追問,都在幫助你反思自我、走出偏見,引發你思考那些自以為是的觀念是否真的無懈可擊。
當我們越多地理解世界,我們也就越多地理解自己。
在書籍中超越世界
如果書籍無法賦予我們對抗黑暗的力量,那么,讀書就毫無意義。小說《偷書賊》貫穿著灰色的時代調性,但依然有很多令人溫暖和感動之處。我在閱讀過程中,時常想如果換作是我,是否擁有漢斯家族的勇氣,敢于冒著生命危險去藏匿一個猶太人。
人類總體的經驗時常在拷問我們內心,這些書籍能不能幫助我們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的高光一刻。雖然這種高光一刻在有些人看來只是一種愚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癡》中的提醒:“當善良成了白癡,仁愛變得無用,狂暴顯示為力量,怯懦裝扮成理性,美注定要被踐踏和毀滅,惡卻愈加肆無忌憚、擾亂一切。”梅什金公爵并沒能撼動這張根深蒂固的網,他并不能為這個世界做什么,只能回到自己的凈土。但是這個世界真的有凈土嗎?如果沒有凈土,我們還要做白癡嗎?
這也許就是經院哲學家阿奎那所說的,我們今生活著的唯一意義,就是超越今生。
大浪淘沙//摘自《法治的細節》,云南人民出版社|果麥文化出品,本刊有刪節,攝圖網/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