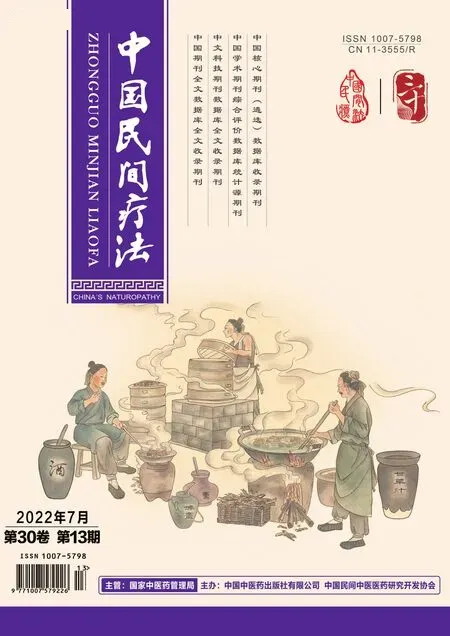中醫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的研究進展
魏琳琳,魯業東,朱紅梅,崔 麗,徐 菁
(貴州省貴陽強直醫院,貴州 貴陽 550000)
強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一種慢性進行性炎性疾病,目前其病因尚不明確。AS根據疾病類型分為中軸型和外周型兩種,臨床癥狀有髖關節受累、蠟樣指、虹膜炎或葡萄膜炎、炎性腰背痛等,嚴重者可導致殘疾。AS在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中的發病率不同,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男女患病比例為2~3∶1,且男性發病較快且病情較重[1]。AS發病主要受遺傳和環境因素影響,目前證實其發病與人類白細胞抗原-B27(HLA-B27)的陽性率密切相關。我國AS患者HLA-B27陽性率高達90%[1],具有家族聚集傾向,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發病年齡早,父母患病不僅會增加子女的患病風險,且子女患病時間要早于父母[2]。AS起病隱匿,尚無根治方法,臨床治療目標為緩解癥狀,防止關節損傷和并發癥,提高生活質量。現代醫學主要通過藥物治療AS,常用藥物有非甾體抗炎藥(NSAIDs)、糖皮質激素和生物制劑等,但不良反應明顯,需要定期檢測患者的肝腎功能,以防止肝腎功能損傷。另外,藥物治療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生物制劑價格昂貴,往往給患者的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導致患者依從性不高。中醫藥治療AS具有不良反應少、經濟效益好等優勢,在臨床中被廣泛使用。本文淺述AS的中醫病因病機及治療研究進展。
1 病因病機
AS歸屬于中醫“痹證”范疇,隨著歷代醫家對痹證的深入研究,依據本病的病因病機,又將其命名為“腎痹”“骨痹”“脊強”“竹節風”等[3]。現代醫家焦樹德教授創立“尪痹”“大僂”病名,但因《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規定“尪痹”對應現代醫學中的類風濕關節炎,AS和類風濕關節炎屬于兩個獨立的疾病,故而有醫家提出將AS命名為“大僂”或“僂痹”[4]。
中醫認為,AS的內因為肝腎虧虛,外因為風、寒、濕、熱邪侵襲。《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指出腎與本病的關系。《諸病源候論·腰痛不得俯仰候》載:“腎主腰腳,而三陰三陽、十二經、八脈,有貫腎絡于腰脊者。勞損于腎,動傷經絡,又為風冷所侵,血氣擊搏,故腰痛也。陽病者,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陰陽俱受邪氣者,故令腰痛而不能俯仰。”提出冷邪侵襲人體,傷及陰陽、經脈,進而傷腎,而陰陽受損則俯仰不能,即AS的癥狀之一。《諸病源候論·背僂候》載:“肝主筋而藏血。血為陰,氣為陽。陽氣,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陰陽和同,則氣血調適,共相榮養也,邪不能傷。若虛則受風,風寒搏于脊膂之筋,冷則攣急,故令背僂。”提到肝血對本病的影響,認為氣血陰陽調和則能抵御外邪,而風寒外邪入體會導致疾病的發生。《馬培之醫案》中提到:“督脈為陽脈之海,其為病也,腰似折,髀不可以曲,督脈與膀胱之經皆取道于脊,一著風寒濕邪,則經氣不行,腰脊板強。”指出督脈對本病的作用,以及風、寒、濕邪可導致腰脊強直。
綜上所述,AS的病因病機為人體肝腎虧虛,風、寒、濕、熱邪侵襲所致,內因、外因相互作用致使痰、瘀等病理產物生成。李彥等[3]認為因人正氣虧虛,外邪入侵,致氣血凝滯,邪入關節、脊柱,使筋脈、脊骨失養,甚至出現彎曲變形,病性為本虛標實。黃永賓等[5]認為內外合邪,陽氣不得開闔,寒氣侵襲,筋失榮養,骨失淖澤,最終導致骨損筋攣,腰、脊、髖僵痛變形,出現功能障礙。病程日久,腎虛腰腹失養,不榮則痛,外邪及痰瘀阻滯督脈,經脈不通則痛,為虛實夾雜之證。從疾病的發展分析,早期腎督虧虛、外感痹阻,中后期正氣虧虛、氣血運行失調,繼發痰、瘀等病理產物。
2 中醫藥治療AS
2.1 中藥內治 炎癥、骨破壞、新骨形成是AS的主要病理特點,導致骨破壞的關鍵因素是炎癥的產生,因此控制炎性反應是控制病情進展的關鍵環節。石金杰等[6]基于網絡藥理學方法探討馮興華教授的臨床經驗方補腎強脊顆粒治療AS的作用機制,補腎強脊顆粒由淫羊藿、熟地黃、懷牛膝、當歸、赤芍、細辛等藥物組成,分析后發現此方中的有效成分槲皮素、山奈酚、豆甾醇等可通過抑制關節滑膜增生,減少免疫細胞過度活化和增殖,抑制軟骨降解,在抗炎、抗纖維化和抑制骨破壞等方面發揮治療作用。白細胞介素-17(IL-17)信號通路和Th17細胞分化與AS的發病密切相關,補腎強脊顆粒可通過調控IL-17信號通路、Th17細胞分化等途徑降低AS的關鍵炎癥指標,從而控制炎癥進展。彭江云教授將AS辨證分為腎陽虛衰證、肝腎虧虛證和濕熱蘊結證,對肝腎虧虛證患者治以滋補肝腎、壯骨強筋,選獨活寄生湯加減,具有散寒止痛、祛風濕、補血益氣、補腎強筋等功效[7]。李偉等[8]基于網絡藥理學的方法分析獨活寄生湯的活性成分及作用機制,發現方藥中的有效活性成分有槲皮素、山奈酚、柚皮素、漢黃芩素、黃芩素等,可調節免疫功能,抑制炎癥介質產生,從而減輕炎性反應和疼痛癥狀。此外,獨活寄生湯可通過影響AS的作用靶點,發揮抗炎、調節免疫和促進骨組織修復的作用。沈家驥將AS分為寒濕侵襲證、肝腎督虧證和濕熱阻絡證,治療注重祛寒除濕、補腎強督和通絡活血,以“腰四味”(鹽杜仲、酒續斷、桑寄生、牛膝)強筋健骨、“三烏”(附子、川烏、草烏)祛寒除濕,獲得滿意療效[9]。核轉錄因子-κB(NF-κB)信號通路是AS重要的作用靶點[8]。研究發現,附子中的烏頭堿可通過調節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降低機體的炎癥因子水平,具有抗炎和中樞鎮痛作用[10],烏頭中的烏頭原堿可通過下調NF-κB信號通路以抑制破骨細胞的生成[11]。
綜上所述,中藥內治法治療AS主要通過減少炎癥因子釋放而起到抗炎作用,并且可通過中藥有效活性成分調節機體多個信號通路,抑制破骨細胞生成,達到保護骨細胞的效果。中藥內治法治療AS可有效緩解患者的臨床癥狀,體現了中醫辨證施治的優勢。
2.2 中藥外敷 中藥外敷是中醫外治法之一,常作為AS的輔助治療手段,具有操作簡便、療效好、價格低廉和不良反應小的優勢。研究顯示,中藥外敷能使藥物滲入皮膚到達病灶,可促進血液循環,改善微循環,增強組織修復能力,并能提高白細胞和網狀細胞的吞噬能力,增強機體的免疫力和抗炎、鎮痛作用,使受壓迫的神經周圍組織炎癥水腫得以吸收、消除,從而解除疼痛、腫脹等急性期癥狀[12]。郝宇鵬等[13]將68例AS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34例,對照組給予柳氮磺吡啶治療,觀察組給予中藥內服(壯督除痹湯)聯合外敷(活血化瘀膏)治療,結果顯示觀察組總有效率(94.12%)高于對照組(73.53%),患者耳屏-墻距離、頸椎旋轉、踝間距的改善情況均優于對照組,其生活質量明顯提高。唐業建[14]采用五虎散外敷配合按摩治療AS患者48例,總有效率達93.75%,患者治療后的晨僵時間、擴胸試驗、前驅試驗、指地試驗和紅細胞沉降率(ESR)等指標均明顯改善。包烏吉斯古冷等[15]將50例腎虛濕熱型AS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25例,對照組采用西藥治療,觀察組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加用補腎清熱湯聯合中藥外敷治療,結果顯示觀察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觀察組治療后晨僵時間、疼痛改善情況均優于對照組,且C反應蛋白(CRP)、ESR水平均低于對照組。
2.3 針灸 針灸通過刺激穴位改善血液循環,舒筋活絡,達到治療AS的目的。陳小波等[12]將100例AS患者分為對照組和研究組,對照組給予口服柳氮磺胺吡啶治療,研究組給予針刺華佗夾脊穴和督脈穴治療,結果顯示研究組病情活動度、β膠聯降解產物(β-CTX)和高遷移率族蛋白B1(HMGB1)水平的改善情況均優于對照組,且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孫玉娟等[16]將82例AS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41例,對照組給予柳氮磺胺吡啶治療,觀察組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運用中醫整體觀行針灸治療,結果顯示觀察組總有效率(97.57%)高于對照組(82.93%)。丁國萍等[17]采用針灸治療30例AS患者,總有效率達86.7%,患者的ESR、CRP水平均較治療前降低,且未出現肝腎功能損傷。張利紅[18]采用針灸治療60例AS患者,主穴取風池、華佗夾脊、腎俞,總有效率達96.67%。
綜上所述,針灸治療AS具有較好的臨床療效,在臨床應用過程中,需根據中醫理論辨證論治,調整針法及針刺深淺,以達到滿意的治療效果。
3 小結
綜上所述,中醫藥治療AS能有效緩解癥狀,延緩病情進程,提高生活質量,具有不良反應少、耐受性高等優勢。目前有關中醫藥治療AS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如對本病沒有統一的辨證分型標準,中醫藥治療本病的作用機制不明確,臨床研究樣本量小且無統一的療效評價標準。針對以上問題,筆者認為應聯合多地醫院,共同創建AS患者的疾病數據庫,以便于研究者進行多中心的臨床研究。此外,還應加大對AS專科醫院的建設投入,使患者得到更專業的治療。對于AS的防治,臨床應注重早發現、早治療,在積極配合醫師治療的同時,患者還應堅持功能鍛煉,以防止脊柱強直、身體畸形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