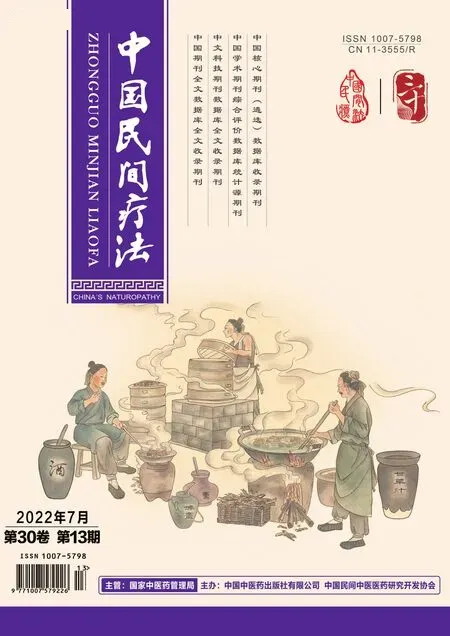強直性脊柱炎中醫(yī)辨證分型治療研究進展
李源真,周 全
(1.河南中醫(yī)藥大學,河南 鄭州 450046;2.河南中醫(y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河南 鄭州 450000)
強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以慢性炎癥為主的全身性疾病,主要累及骶髂關節(jié)、脊柱韌帶附著點等部位,癥狀以腰背部炎性疼痛,外周單發(fā)大關節(jié)炎、肌腱端炎及眼部、心血管、肺部等關節(jié)外病變?yōu)樘攸c。晚期病情嚴重者可出現(xiàn)脊柱纖維性和骨性強直[1]。目前,AS病因尚不明確,且缺乏確切有效的治療方案,西醫(yī)治療目的在于控制炎癥,延緩病程,減少藥物不良反應[2]。AS屬于中醫(yī)“痹證”范疇,在疾病發(fā)展過程中依據其不同表現(xiàn),可分為骨痹、腎痹、脊痹、頸痹、背痹、腰痹、骶痹、髖痹、大僂等[3]。本文從經絡、臟腑、營衛(wèi)不和、血瘀及毒邪等方面整理和總結AS的病因病機、辨證分型及治療情況。
1 從經絡論治
AS的病變部位主要在腰脊,屬于督脈、足太陽膀胱經循行部位。《素問·骨空論》云:“督脈為病,脊強反折。”《脈經》曰:“尺寸俱浮,直上直下,此為督脈。腰背強痛,不得俯仰。”督脈為陽脈之海,主一身之陽氣,其走行之處為后背正中線,督脈受損,感受外邪,陽氣化生的通路被阻,首當其沖的是腰脊部位。《靈樞·經脈》云:“膀胱足太陽之脈,夾脊抵腰。”太陽為巨陽,足太陽膀胱經是體表陽氣旺盛之處,并與腎經相表里,督脈與足太陽膀胱經關系密切,太陽經氣不利,督脈陽氣不能輸布于腰脊,復感外邪,則發(fā)為本病。因此,督脈陽氣的盛衰與足太陽膀胱經經氣是否通利與AS發(fā)病密切相關[4]。臨床治療AS以溫陽通督為法,并配合艾灸、針刺、中藥熏蒸等中醫(yī)外治法,常能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李月紅等[5]將120例腎虛督寒型AS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觀察組給予溫督通痹方督灸聯(lián)合針刺治療,對照組給予口服西藥治療,結果發(fā)現(xiàn)觀察組總有效率為78.6%,高于對照組的55.2%,說明溫督通痹方督灸聯(lián)合針刺治療可有效改善腎虛督寒型AS患者的臨床癥狀。姚志城等[6]對60例早中期AS患者進行分組,對照組給予口服柳氮磺吡啶治療,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配合督脈鋪灸治療,結果發(fā)現(xiàn)觀察組總有效率為90.00%,高于對照組的73.0%,說明督脈鋪灸聯(lián)合柳氮磺吡啶治療早中期AS可提高臨床療效。王新革[7]將62例AS患者隨機分組,治療組給予督脈灸聯(lián)合附子湯加味治療,對照組給予獨活寄生湯治療,結果顯示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0.3%,高于對照組的58.1%,說明督脈灸與附子湯加味聯(lián)合使用能夠取得良好的臨床療效。衣華強[8]總結近20年督脈灸治療AS的現(xiàn)狀,結果表明督脈灸治療AS臨床效果顯著。楊利華等[9]將68例腎虛督寒型AS患者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組給予溫針灸治療,對照組給予口服西藥治療,結果顯示治療組總有效率為88.2%,高于對照組的61.8%,表明溫針灸治療AS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癥狀。
2 從臟腑論治
2.1 從腎論治 AS的發(fā)病與腎緊密相關,正如《素問·脈要精微論》載“腰為腎之府”,腰背部發(fā)生的病證與腎功能失常有關。中醫(yī)認為,腎陽不足,命火虛衰,會使機體抗病能力下降,易感外邪,使氣血不通,寒濕凝滯,瘀阻經絡、筋骨,或腎精不足,骨髓失養(yǎng),則脊柱受累。因此,AS的發(fā)病之本在于腎虛,腎又與督脈密切相關,《醫(yī)學衷中參西錄》云:“腎虛者,督脈必虛,是以腰痛。”腎督虧虛,陽氣受損,或外感寒邪,或寒從內生,均使氣血運行無力,不通則痛,肌肉、筋骨失于溫煦,發(fā)為AS。張猛等[10]將90例AS患者進行分組治療,對照組給予柳氮磺吡啶治療,觀察組在此基礎上聯(lián)合補腎通痹湯(由制川烏、威靈仙、獨活、芥子、蜈蚣等藥物組成)加減治療,結果顯示觀察組總有效率為88.89%,高于對照組的71.11%,說明以補腎通絡為原則治療AS可有效提高臨床療效。秦松林等[11]從腎出發(fā),提出四大治法治療AS:一是補腎強脊、祛寒除濕,自擬強脊通痹湯,療效顯著;二是溫腎補脾、蠲痹止痛,治療時在溫補腎陽的基礎上加用黃芪、葛根、干姜等培補脾陽之品;三是滋陰養(yǎng)腎、寒溫并取,治療時需減少溫熱藥物的使用,注重藥物配伍,寒熱并取;四是益腎填精、化瘀解毒,脊柱關節(jié)強直、活動嚴重受限者治療時多用龜甲膠、鹿角膠等益腎填髓之品,適當配伍清熱解毒藥可降低炎癥活動度。尹曉霞等[12]觀察腎著湯(由干姜、茯苓、甘草、白術等藥物組成)治療AS活動期的臨床療效,結果發(fā)現(xiàn)腎著湯可有效抑制AS活動期患者的炎性反應,取得良好的臨床療效。國醫(yī)大師朱良春認為腎督虧虛是AS的基本病機,自擬培補腎陽湯,方中在使用仙茅、淫羊藿等溫補腎陽藥的同時,配合山藥、枸杞子等藥物滋補腎陰,體現(xiàn)了“陰中求陽”的理念,取得顯著療效[13]。
2.2 從肝論治 《素問·五臟生成》曰:“肝藏血,心行之……肝主血海故也。”肝藏血,肝血旺盛,濡養(yǎng)臟腑、肌肉、經筋,使其發(fā)揮正常的生理功能;肝血虧虛,失去濡養(yǎng)的功能,引發(fā)慢性損傷,可導致臟腑功能失調,發(fā)為AS。《格致余論·陽有余陰不足論》載:“司疏泄者,肝也。”肝主疏泄,調暢全身氣血,肝之氣血充足,筋脈得到滋養(yǎng),肝之疏泄功能正常,筋脈收縮弛張、柔韌有力,可保證脊柱、關節(jié)的功能正常。肝主筋,《素問·痹論》曰:“痹在于筋,則屈伸不利。”全身的筋脈由肝統(tǒng)領,筋脈強韌健壯,才能調控肌肉,增加肌肉的活動度和靈敏度。肝主藏血、主疏泄、主筋的生理功能相輔相成,同時腎為肝之母,肝腎同源,腎主骨,腎精充足,則全身骨骼強健有力,肝血能影響腎精的充盛,腎精可以化生肝血,兩者相互協(xié)作[14]。因此,從肝論治AS具有重要意義。馬建國[15]認為AS屬于中醫(yī)“筋痹”范疇,筋是脊柱活動的主動因素,治療以調肝柔筋、解痙止痛為法,急性期以濕熱瘀毒互結留滯經絡、停于骨骼筋脈為特征,治宜清濕熱,解瘀毒,柔筋止痛,用藥多為清熱利濕、活血解毒之品;緩解期以肝陰不足、肝氣不用為特征,治宜養(yǎng)肝柔筋,緩急止痛,同時輔以清熱化毒、祛瘀通絡之法,用藥多為養(yǎng)陰生津、養(yǎng)血柔肝之品。王北等[16]認為在重視補腎的同時,不能忽視肝在AS發(fā)病過程中的作用,將AS分為肝氣郁滯、肝火旺盛、肝血不足、肝陰虧虛4種證型,分別選用四逆散、龍膽瀉肝湯、四物湯、杞菊地黃丸治療。房定亞認為痙攣、強直是AS的病理特點,指出AS屬于中醫(yī)“筋痹”范疇,提出以解痙舒筋法治療AS,強調“調肝實”是治療關節(jié)疼痛、屈伸不利的根本治法,確立“酸以養(yǎng)肝體、甘以緩筋急、辛以理肝用”的用藥原則,自擬解痙舒督湯治療(由葛根、白芍、蜈蚣、山慈菇等藥物組成)AS取得顯著療效[17]。孔德敬等[18]認為AS發(fā)病以強直為特征,屬于“筋”的范疇,應從肝治,自擬補肝養(yǎng)腎湯(由淫羊藿、桑寄生、五加皮、獨活、柴胡等藥物組成)治療肝腎不足型AS療效顯著。黃儒[19]運用通督柔肝推拿法治療AS患者,結果表明該法可明顯改善患者的遠期預后,提高其生活質量。
2.3 從脾論治 古今醫(yī)家對于AS的發(fā)病多從腎督立論,認為腎虛督寒是AS的主要病機,隨著中醫(yī)基礎理論的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對于痹證病因病機的認識逐漸加深,發(fā)現(xiàn)脾虛在AS發(fā)病過程中也起到關鍵作用。《素問·痹論》有“痹聚在脾”的說法,李東垣提出:“內傷脾胃,百病叢生。”脾主運化,水谷精微能夠正常散布四肢肌肉和腠理毛竅,則外邪不易侵入。脾主四肢,脾氣健運,則肌肉豐滿有力,脊柱關節(jié)靈活。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腎為先天之本,需要脾所運化的水谷精微才能充盛,脾陽得到腎陽的溫煦才能運化正常。因此,從脾論治可為臨床治療AS提供新的思路。汪四海等[20]認為AS以正虛為本,邪實為標,呈現(xiàn)出虛實夾雜、痰瘀互結的特征,虛證以脾胃虛弱、氣血不足為主,實證以痰濕壅盛、瘀血痹阻為主,治療上注重健脾化濕、益氣養(yǎng)血。劉健教授認為AS的發(fā)病根本是脾腎虧虛,脾氣虛衰,運化功能失調,痰飲水濕內生,留滯關節(jié)、筋骨,痹阻血脈形成瘀血,同時氣血不足,營衛(wèi)不固,外濕侵入體內,困遏脾陽,流注于經絡,痰瘀交阻,發(fā)為AS,提出以健脾祛濕為治療大法,給予參苓白術散加減治療,療效顯著[21]。熊根飛等[22]根據古代文獻歸納AS從脾論治的特點,一是脾胃虛弱、氣血不足,二是脾失健運、內濕由生,三是脾氣虛弱、痰瘀留滯,并通過梳理健脾通絡法的臨床研究、實驗研究和分子免疫學研究,說明從脾論治AS具有重要意義。王瑞瑞等[23]認為AS發(fā)病病機是先天不足,后天脾胃功能失調,痰瘀內生外合風寒濕邪,自擬溫腎健脾定脊湯(由鹿角、巴戟天、防風、白術、蜈蚣等藥物組成)治療AS,結果顯示該方可有效緩解患者的癥狀,減輕炎性反應。
3 從營衛(wèi)不和論治
營衛(wèi)學說最早見于《黃帝內經》,《靈樞·營衛(wèi)生會》對營衛(wèi)之氣的概念、來源、運行、功能進行了詳細的解釋。衛(wèi)氣具有防御功能,行于脈外,抵御外邪,溫煦機體;營氣具有濡養(yǎng)功能,行于脈內,滋養(yǎng)五臟六腑、肌肉百骸。營衛(wèi)調和,腠理致密,筋脈舒暢,風、寒、濕邪難以入內。《類證治裁》曰:“諸痹……良由營衛(wèi)先虛,腠理不密,風、寒、濕乘虛內襲……久而成痹。”可以看出,痹證的發(fā)生主要是由于風、寒、濕邪入侵,而營衛(wèi)之氣在抵御外邪過程中發(fā)揮著關鍵作用。調和營衛(wèi)法首見于《傷寒論》,張仲景在繼承《黃帝內經》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身體痹不仁”的病機是營衛(wèi)不和、氣血不利,其創(chuàng)制的桂枝湯類方對后世風濕病的治療有著重大影響[24]。胡蔭奇教授運用桂枝加葛根湯治療AS效果顯著,其認為桂枝加葛根湯可以內外兼治,既調和營衛(wèi),又能升督脈陽氣,疏通氣血,緩急止痛,可用于治療AS[25]。張潔等[26]強調營衛(wèi)失和是AS發(fā)生的內因,運用桂枝湯加味以調和營衛(wèi)、祛寒化濕,臨床療效良好。戴朝壽等[27]認為AS的主要病機是營衛(wèi)不和,風、寒邪氣痹阻經絡,不通則痛,運用烏頭桂枝湯治療89例AS患者,總有效率為100%。曹浩坤[28]根據《傷寒論》中桂枝加葛根湯條文中“項背強”的描述,認為其與AS發(fā)病時出現(xiàn)腰背強直、晚期出現(xiàn)脊柱融合的癥狀相似,使用桂枝加葛根湯治療取得滿意的療效。劉朵[29]運用補中桂枝湯治療AS風寒濕痹證,以補氣養(yǎng)血、調和營衛(wèi),取得顯著的效果。
4 從血瘀、毒邪論治
4.1 從血瘀論治 中醫(yī)將血液瘀滯不通,聚于經絡、臟腑、肌肉、關節(jié)的病證稱為血瘀證。《素問》云:“痹……在于脈則血凝而不流。”《癥因脈治》云:“痹者,閉也,經絡閉塞,麻痹不仁。”《景岳全書》云:“蓋痹者,閉也,以血氣為邪所閉,不得通行而病也。”《醫(yī)林改錯》中的身痛逐瘀湯對于從血瘀論治痹證有著重要的影響,可以看出古代醫(yī)家非常重視痹證與血瘀的關系。AS的發(fā)病與血瘀證有著密切關系,多種因素都會造成血瘀證,在腎虛的基礎上,受到風、寒、濕邪侵襲,正虛不能鼓邪外出,邪氣久留經絡、骨節(jié)、肌肉,使氣血壅滯,運行不暢,導致瘀血發(fā)生。瘀血既是病理產物,也是致病原因,貫穿疾病始終。朱良春[30]認為AS的內因為腎陽虧虛,氣血凝滯,外因是風、寒、濕邪侵襲,氣血被阻,壅滯經脈,或失治、誤治,病久虧虛,氣血周流不暢,出現(xiàn)痰瘀互結,膠著難解,活血化瘀應貫穿治療始終。劉本勇等[31]認為AS發(fā)病的根本原因是腎虛,血瘀是關鍵因素,補腎活血是治療AS的基本方法之一,可改善AS患者預后,提高其生活質量。黃勝光教授認為AS的病機以腎虛為本、瘀阻為標,腎虛血瘀貫穿始終,自擬補腎活血湯(由羌活、杜仲、續(xù)斷、狗脊、川芎、雞血藤等藥物組成)治療AS,并配伍蟲類藥搜剔竄透,活血通絡,臨床療效顯著[32]。李俊枝[33]自擬導痹湯(由黃芪、當歸、人參、牛膝等藥物組成)聯(lián)合西藥治療氣滯血瘀型AS,結果發(fā)現(xiàn)可提高臨床療效,減輕不良反應。孫立明等[34]對AS活動期患者和健康志愿者進行對比研究,發(fā)現(xiàn)AS活動期患者外周血中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2(PAI-2)、血栓素A2(TXA2)等細胞因子水平明顯升高,說明AS活動期患者普遍存在血瘀證,并將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新風膠囊用于治療AS活動期患者,取得滿意的療效。
4.2 從毒邪論治 中醫(yī)“毒邪”理論最早來自《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中記載毒邪是“五行標盛暴烈之氣”。毒邪致病可分為外毒、內毒、虛毒,外毒主要是指風、寒、濕、熱之氣夾雜毒氣后侵襲人體,對人體造成傷害。《備急千金要方》曰:“夫歷節(jié)風著人……此是風之毒害者也。”內毒是指體內氣血不行,瘀滯經絡或痰濕聚集夾雜毒氣,形成瘀毒和濕毒,也可由外來邪氣轉化。虛毒致病主要是在疾病的中晚期,正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無虛不致病”,久病臟腑氣血受損,出現(xiàn)陰陽虛實偏頗[35]。楊倉良認為[36],毒邪致病是AS的基本病機,將其致病機制概括為4個方面:一是六淫邪氣等外來之毒,與內毒共同作用于人體而發(fā)病;二是外毒侵襲,又根據患者體質變化為內毒,使氣血不行,濕熱壅滯,從而致病;三是毒邪侵犯腰、髂、髖等關節(jié)韌帶部位,使局部經絡瘀滯,氣血受阻,骨質破壞,關節(jié)僵硬疼痛;四是祛毒、攻毒不及時,使五臟六腑功能受損,影響正常的生理功能而發(fā)病。在此基礎上提出“攻毒療法”治療“毒證”為核心的學術觀點,對于早期風寒濕熱毒邪,給予祛風散寒、泄?jié)窠鉄嶂?使毒邪無立足之地;中期臟腑功能受損,內生痰濕、瘀血,形成痰毒、瘀毒,在遏制和搜剔毒邪的同時調理臟腑功能;晚期則是虛與毒并存,毒邪結聚,不易祛除,病證復雜,應選好側重點,固護正氣,扶正補虛,攻毒祛毒。滕彩芳等[37]基于壯醫(yī)學毒虛致病理論,提出AS的病機以內虛為本,加之感受風、寒、濕等外來之毒,導致氣血壅滯不暢而發(fā)病,治以調氣、解毒、補虛。調氣即通過拔罐、熏蒸等療法增強人體功能,恢復氣血平衡;解毒、補虛即運用藤類藥祛除外毒,運用血肉有情之品補益精血,針藥結合,療效顯著。
5 小結
AS起病隱匿,病程漫長,急性發(fā)作期給患者帶來極大的痛苦,影響其生活質量。由于西醫(yī)治療AS療效不確切,所以中醫(yī)藥治療本病受到了更多的重視,而正確對AS進行辨證分型是取得良好療效的關鍵,應做到因人而異、病證結合、個體化治療,才能最大程度地發(fā)揮中醫(yī)的優(yōu)勢,為AS患者的康復帶來更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