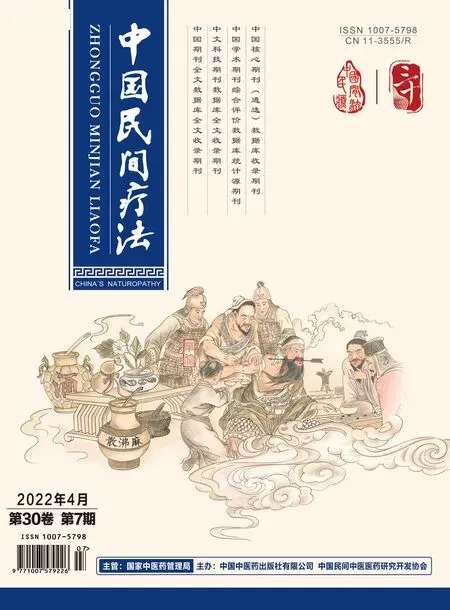針刺治療納武利尤單抗所致頑固性呃逆驗案※
陳文林,崔 玉,王锃銘,呂錦珍,張云城
[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龍崗),廣東 深圳 518712]
肝癌轉移是肝癌進展的標志。肝癌術后復發并肝內轉移或肝外轉移到重要臟器,均可導致病情加重,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納武利尤單抗作為我國首個批準上市的免疫檢查點程序性死亡受體-1(PD-1)抑制劑,在晚期肝癌的治療上兼具有效性及安全性[1]。納武利尤單抗常見的不良反應包括疲勞、皮疹、瘙癢、腹瀉、惡心、甲狀腺功能亢進、甲狀腺功能減退等,未見頑固性呃逆。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接診1例納武利尤單抗治療晚期肝癌后出現頑固性呃逆的患者,采用常規中西醫結合治療未見明顯療效。筆者采用內關透外關聯合針刺合谷、足三里、三陰交的針刺療法取得滿意療效,現將治療過程介紹如下。
1 臨床資料
患者,男,50歲,2020年7月31日就診。患者原發性肝癌術后3年,2020年5月因“腹脹乏力”在某腫瘤醫院復檢,發現肝外轉移,下腔靜脈及右心房癌栓,采取肝動脈化療栓塞術、洛鉑聯合吡柔比星動脈灌注化療,后行下腔靜脈血栓抽吸術、倫伐替尼靶向治療,7月5日行納武利尤單抗(美國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國藥準字S20180014,40 mg/4 mL)聯合倫伐替尼治療,7月23日出現輕度呃逆、腹脹、腹瀉癥狀,7月25日出院,7月26日呃逆加重,并見惡心、嘔吐、腹脹、乏力,伴雙下肢水腫,7月31日前來就診,門診擬“原發性肝癌術后復發,頑固性呃逆”收住入院。入院癥見:神疲乏力,腹脹明顯,頻發呃逆,食后加重,口干,無口苦,無胸悶、胸痛,雙下肢水腫,小便偏少,大便日行10次以上,呈稀水樣。查體:慢性病容,神志清楚,無肝掌及蜘蛛痣,皮膚、鞏膜無黃染,腹部對稱,平軟,無皮疹、靜脈曲張,無胃腸型及蠕動波;上腹部可見長約30 cm弧形手術瘢痕,愈合良好;腸鳴音正常,每分鐘約5次,移動性濁音陽性,腹部壓痛及反跳痛(+),肝脾區叩擊痛(-),墨菲征(-),肝脾肋下未觸及;雙下肢輕度水腫。舌質暗紅,苔白膩,左脈弦細,右脈濡。體質量未見明顯減輕。血常規+C-反應蛋白(CRP):CRP 81.20 mg/L,紅細胞計數3.10×1012/L,血小板計數372.00×109/L,血紅蛋白79.00 g/L;急診凝血四項:凝血酶原時間18.4 s,凝血酶原國際標準比值1.5,凝血酶原活動度53%,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58.7 s;肝功能+腎功能+電解質:丙氨酸氨基轉移酶67 U/L,天冬氨酸轉移酶59 U/L,谷氨酰轉酞酶90 U/L,白蛋白28.2 g/L,膽堿酯酶1 955 U/L,堿性磷酸酶138 U/L,總膽紅素40μmol/L,非結合膽紅素40.0μmol/L,肌酐52μmol/L,尿素氮6.3 mmol/L,鉀離子3.20 mmol/L,鈉離子132.1 mmol/L,鈣離子1.83 mmol/L,氯離子111.0 mmol/L;乙肝兩對半定量:乙肝病毒e抗原0.078 COI,乙肝病毒表面抗原147.500 IU/m L。胸腹水彩超:左側胸腔積液,腹腔積液。心電圖、胸部平片未見異常。西醫診斷:原發性肝癌術后復發,乙型肝炎后肝硬化,頑固性呃逆;中醫診斷:呃逆(正氣虧損,痰濕瘀阻)。立即施治,予以利尿、補充氯化鉀,予山莨菪堿片解痙,改善呃逆,予托烷司瓊止嘔,輔助緩解呃逆。請針灸科會診,行針刺治療,以健脾理氣、降逆止呃為治法,取足三里、三陰交、天突等穴,治療3 d,效果不佳。刻下癥:面色萎黃,精神疲憊,腹部平軟,舌質暗,苔薄膩,左脈弦細,右脈濡弱。給予內關透外關及針刺合谷、足三里、三陰交。患者取仰臥位,消毒局部穴位,在前臂掌側正中,腕橫紋上2寸處取內關,向外關方向快速進針,針刺深度28~32 mm,得氣后緩慢退針至內關處,反復施行重插輕提1 min,留針10 min。隨后在針下得氣處,反復施行小幅度重插輕提手法30 s,留針5 min。同時針刺合谷、足三里、三陰交,單手進針28~32 mm,快速提插捻轉,得氣后行平補平瀉手法1 min,留針20 min。
30 min內呃逆停止,持續8 h未見呃逆。第2日效上法施治,病情穩定,未見呃逆,睡眠佳,納香,于2020年8月14日出院。出院后繼續中西醫結合治療。
2 討論
頑固性呃逆以持續呃逆48 h以上為主要特征,是多種疾病過程中的常見臨床癥狀。頑固性呃逆的發病機制復雜,根據病因可以分為中樞性呃逆和周圍性呃逆,中樞性呃逆常見于腦血管病、顱內腫瘤、腦外傷、多發性硬化癥、帕金森病等[2],周圍性呃逆多由胃腸道、腹膜、胸膜、膈等組織刺激迷走神經和膈神經所致。目前臨床主要采取中樞神經鎮靜、神經阻滯等對癥支持治療。本案患者經常規對癥治療1周后,水腫緩解、血鉀正常,但呃逆癥狀未緩解,且患者失眠,胸痛,納差,精神萎靡。
呃逆最早在?黃帝內經?中被稱為“噦”,明·張景岳將其命名為“呃逆”,正如?景岳全書·呃逆?所言:“噦者,呃逆也,非咳逆也。咳逆者咳嗽之甚者也,非呃逆也。干嘔者,無物之吐,即嘔也,非噦也。噫者,飽食之息,即噯氣也,非咳逆也。”呃逆是以氣逆上沖、喉間呃呃連聲、聲短而頻、難以自制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種病證,其病機為胃失和降,膈間氣機不利,胃氣上逆動膈。本案患者癥見呃逆頻頻,胸痛不適,納差,口干,不寐,乏力,精神萎靡,面色萎黃,大便少而溏,小便黃,舌淡暗,左脈細弦,右脈沉濡。醫者早期采用常規取穴及針刺手法,同時采用西藥解痙、止嘔等治療方案,但療效不佳。究其原因,本案病機為肝積久病體虛,加之藥毒攻伐,損傷中氣,致脾失運化,胃失和降,胃氣上逆,發為呃逆;又因肝腎陰虛,陰血不足,不能斂陽,使肝不疏泄,腎失攝納,濁陰上乘,上逆動膈。遂以柔肝補腎、健脾和胃、益氣降逆為治法,采用內關透外關及針刺合谷、足三里、三陰交的針刺治療方案。
內關透外關常用于治療神志疾病、脾胃疾病、心胸疾病等[3]。內關為手厥陰心包經絡穴,與三焦經相通,又通陰維脈,針刺內關可寬胸利膈、豁痰開竅、降氣止呃。外關位于腕背側遠端橫紋上2寸,尺骨與橈骨間隙中點,為手少陽三焦經絡穴,手少陽三焦經、陽維脈之會,針刺外關有和胃降逆、寬胸理氣、鎮靜止痛之功。內、外關是機體陰陽氣血通行內外之門戶。內關透外關之法一針貫通二穴,發揮了“從陰引陽,從陽引陰”的作用,可疏通手厥陰心包經與手少陽三焦經氣血,使肝氣平和,濁陰下降,陰陽和濟,呃逆立止。
合谷屬手陽明大腸經,為大腸經之原穴,針刺合谷穴可以調經和胃,安和臟腑,恢復機體胃腸功能[4]。足三里為足陽明胃經合穴,可調理三焦之氣[5],針刺足三里具有生發胃氣、健脾化濕之功[6]。研究表明,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療頑固性呃逆操作簡便,安全性好[7]。吳濤等[8]采用哌甲酯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療肝癌行經導管肝動脈化療栓塞術術后呃逆,效果滿意。三陰交為足太陰脾經腧穴,足太陰、足少陰、足厥陰交會穴,刺激三陰交能增強結腸下部及直腸蠕動[9]。針刺合谷、足三里、三陰交達調理氣血、疏通經脈、和胃降逆之功。
本案中,醫者在治療初期采用常規取穴及針刺手法,同時采用西藥解痙、止嘔等治療方案,但收效甚微,而在筆者采用內關透外關及針刺合谷、足三里、三陰交的針刺方案后,患者癥狀明顯改善。究其原因:①選擇功能相近和位置相關聯的穴位配合使用,可明顯增強臨床療效。②內關透外關的針刺方法使人體內外之氣相交,陰陽之氣相合,氣血調和,治療呃逆療效顯著。③晚期肝癌患者正氣不足,邪毒內陷,治療藥物引起的頑固性呃逆在手法上應攻補兼施,祛邪扶正。
3 小結
由納武利尤單抗免疫治療晚期肝癌引起的頑固性呃逆案例在臨床中較為少見。筆者以中醫理論為指導,針對患者肝腎陰虛、脾失運化、胃失和降、上逆動膈的病機特點,予以內外相通、氣血相連、陰陽相從的透刺穴位之法,并配合針刺合谷、足三里、三陰交等穴,使患者氣血疏通,脾胃氣機調暢,肝之陰血充盈,肝氣疏泄有度,腎精得以補充,腎氣攝納、腎陽溫化濁陰之功相得益彰,共達滋補陰血、健脾和胃、益氣化濁、降逆止呃之功,從而使藥毒外排,呃逆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