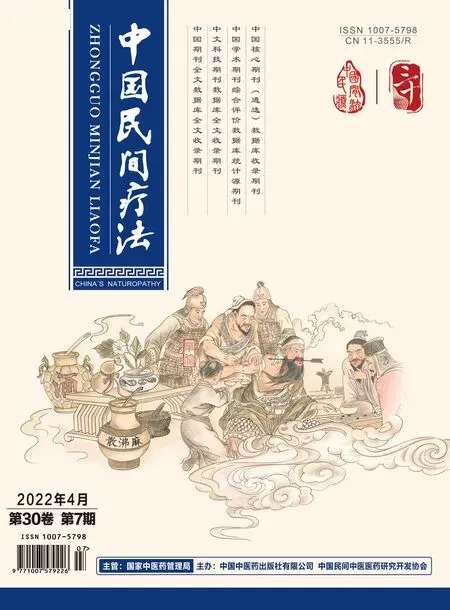偶刺法為主針刺治療帶狀皰疹性脊髓炎案
馮 宇,于學平,李明月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帶狀皰疹性脊髓炎是帶狀皰疹少見的嚴重并發癥,其發病率為0.3%,常以皮疹癥狀為首發,數月內出現脊髓損害癥狀,主要表現為受累脊髓節段以下的運動、感覺障礙等[1]。該病通常出現于皮疹后3~20 d,最長為2個月[2],病變部位多位于皮疹相應脊髓節段,也可出現在其遠隔部位[3]。研究認為,該病發病是多種機制共同參與的結果,包括病毒直接感染和/或免疫介導而致的脫髓鞘、繼發性血管炎的梗死、軟膜蛛網膜炎及神經元、星形膠質細胞等其他成分感染[4-5]。當機體免疫功能下降時,潛伏在神經元中的水痘-帶狀皰疹病毒在神經節內復制、傳播,并沿感覺神經纖維下行,釋放至皮膚或黏膜中,引起帶狀皰疹和神經痛,嚴重時感染的神經節上下背根神經節也可受累,并向內擴展至腦膜和沿神經根進入中樞神經系統,造成脊髓炎或腦炎[3]。目前,西醫治療該病多運用激素沖擊療法,如早期使用大劑量抗病毒聯合糖皮質激素治療[5],但口服鎮痛類藥物易產生頭暈、惡心、嘔吐等不良反應,且有成癮性,停藥后病情易反復,不能完全根治。針灸治療帶狀皰疹性脊髓炎有止痛效果好、操作簡單、起效快、無明顯不良反應和依賴性等優勢。筆者跟隨于學平教授學習期間,發現其用偶刺法治療帶狀皰疹性脊髓炎效果較好,現將其治療經驗分享如下。
1 病案資料
患者,女,81歲,因“帶狀皰疹后雙下肢活動不利、排尿困難3周”于2021年2月26日至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針灸三科門診就診。患者5周前左側胸背部出現針刺樣疼痛及簇狀小水皰,就診于本院皮膚科,診斷為“帶狀皰疹”,口服阿昔洛韋等藥物治療后帶狀皰疹逐漸消退,但疼痛未緩解。3周前出現雙下肢麻木、脹痛、無力且不能獨立行走,僅能勉強站立,雙下肢痛溫覺減退,左側重于右側,伴有二便失禁,排尿困難。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未能至醫院進行系統治療,自服甲鈷胺片等藥物營養神經,無好轉。既往有高血壓病、周圍神經病、腦梗死、動脈粥樣硬化病史。查體:患者由輪椅推入診室,自帶留置導尿管,雙下肢肌力4級弱,雙下肢膝腱反射活躍,雙側跖反射消失,雙側T4以下痛溫覺減退,左側背部T5~7神經分布區可見皰疹后結痂及色素沉著(掃描題目右側二維碼查看圖1),舌淡暗,苔薄白,脈沉弱。頸部MRI示頸椎退行性改變,C3~4、C4~5、C5~6、C6~7椎間盤突出,部分層面黃韌帶增厚,雙側橫突孔不對稱。胸部MRI示胸椎退行性改變,T5~6、T6~7、T10~11椎間盤略突出,T9~10、T10~11黃韌帶略增厚,T2~3、T3~4脊髓內異常信號(掃描題目右側二維碼查看圖2、3)。西醫診斷:帶狀皰疹性脊髓炎。中醫診斷:痿證(氣虛血瘀證)。治以益氣活血通絡,以偶刺法為主進行針灸治療。選穴:主穴取夾脊穴(T2~T7雙側)、腎俞(雙側)、命門、上髎(雙側)、次髎(雙側)、膻中、關元、中極,配穴取右側三陰交、太溪,左側足三里、昆侖。選取華佗牌0.35 mm×40 mm一次性毫針(蘇州醫療用品廠有限公司),患者取右側臥位,雙腿微屈,左小腿置于右腿前方,在保持舒適體位的前提下,充分暴露背腰、胸腹及下肢穴位。夾脊穴均向脊柱方向斜刺約15 mm,腎俞、上髎、次髎均直刺約15 mm,命門直刺約10 mm,膻中向下平刺約15 mm,關元、中極直刺約15 mm,太溪、昆侖直刺約7 mm,三陰交直刺約15 mm,足三里直刺約30 mm。各穴進針得氣后,夾脊穴及膻中施捻轉提插瀉法,腎俞、命門、關元、中極、三陰交、太溪、足三里、昆侖施捻轉提插補法,上髎、次髎施平補平瀉法,留針50 min,每日治療1次,周日休息。治療1周后,患者膀胱充盈時尿意明顯,且尿道口時有尿液流出,肢體活動無明顯變化,繼續予以原針灸方案治療。治療2周后,拔除尿管,患者可自行排尿,但尿頻,下肢活動好轉,肌力4級強。治療4周后,患者排尿正常,可扶物行走,雙下肢肌力5級弱,T4以下痛溫覺略差,左側胸背部疼痛感明顯減輕。因患者居住地變更,距離醫院較遠,且病情恢復達到患者滿意程度,遂結束治療。
2 討論
帶狀皰疹歸于中醫“蛇串瘡”范疇,又有“纏腰火丹”“火帶瘡”“蛇丹”和“蜘蛛瘡”等名稱。?諸病源候論·甑帶瘡候?稱該病為“甑帶瘡”:“甑帶瘡者,繞腰生,此亦風濕搏血氣所生,狀如甑帶,因此為名。”?外科啟玄·卷七?稱該病為“蜘蛛瘡”:“此瘡生于皮膚間,與水窠相似,淡紅且痛,五七個成攢,亦能萌開。”?瘡瘍經驗全書·火腰帶毒?曰:“火腰帶毒,受在心肝二經,熱毒傷心,流滯于膀胱不行,壅在皮膚。”竇漢卿認為濕熱毒邪侵襲心、肝二經,流散于膀胱,壅滯于皮膚,發為該病。?證治準繩·瘍醫?云:“或問:繞腰生瘡,累累如珠何如?曰:是為火帶瘡,亦名纏腰火丹。”首次將該病命名為“纏腰火丹”。?醫宗金鑒?云:“(纏腰火丹)此證俗名蛇串瘡,有干濕不同、紅黃之異,皆如累累珠形,干者色紅赤,形如云片,上起風粟,作癢發熱。”提出該病的兩種病機,其一為心、肝二經受風火侵襲,其二為濕熱阻滯肺、脾二經。由此可見,古代醫家認為該病多與風、毒、濕、熱等邪氣相關,是由肝膽火熱與肺脾濕熱壅郁于內、毒邪侵襲于外所致。
該患者就診時帶狀皰疹病程已超過3周,皰疹已結痂,以胸背疼痛、排尿困難、下肢無力為主癥,為帶狀皰疹之變證。因患者素體虛弱,易染毒邪,濕熱留戀,耗傷正氣,濕熱毒邪稽留日久,正不勝邪,邪阻氣血,臟腑、筋骨、肌肉失于濡養而成該病,治宜扶助正氣、活血通絡,因背痛連胸,故以偶刺法治之。偶刺為?靈樞?“十二刺法”之一,出自?靈樞·官針?:“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后,以治心痹。刺此者,傍針之也。”另外,“偶”也有相對之義,總的意思是臨近、靠近、相對。張介賓言:“偶,兩也。前后各一,故曰偶刺。”因進針時一前一后,前后配偶,故稱偶刺,因前胸屬陰,后背屬陽,又稱陰陽刺。?黃帝內經靈樞集注?云:“偶刺者,一刺胸,一刺背,前后陰陽之相偶也。旁取之,恐中傷心氣也。”?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云:“一曰偶刺,以一手直其前心,以一手直其后背,皆以直其痛所。直者,當也。遂用一針以刺其胸前,用一針以刺其后背,正以治其心痹耳。然不可正取,須斜針以旁刺之,恐中心者一日死也。前后各用一針,有陰陽配合之義,故曰偶刺。”
本案采用以偶刺法為主的針刺療法,上取背部夾脊穴和胸部膻中,一前一后,施捻轉提插瀉法,以行氣活血,疏通氣街,緩解胸背部疼痛。頸部夾脊穴靠近病所,屬近部取穴,刺之可刺激相應神經根,增加局部血流,有利于炎癥的消退和局部神經的恢復;膻中為八會穴之氣會,可行氣止痛。下取腰骶部腎俞、命門,配腹部關元、中極,一前一后,施捻轉提插補法,以扶助正氣。命門居腰屬督脈,?素問·骨空論?言:“督脈者……上額交顛上,入絡腦……入循膂絡腎。”命門為陽氣之根,可固攝陽氣;腎俞為腎之背俞穴,位于命門左右,前后相配,可調補督任、益氣養精、平衡陰陽,配八髎穴能補腎氣,助膀胱氣化。關元為任脈穴,小腸經之募穴,為元陰元陽交關之處,配中極可補精血、壯元陽、利小便。督脈主陽氣,任脈主陰精,一陰一陽,可調理任督二脈,陰陽調則氣血充。該患者處于皰疹后期,經絡瘀滯,氣血不充,發為痿證。足三里為陽明經下肢穴位,可疏通經絡,補氣血,強腰膝,增強下肢行走力量;配三陰交可清利濕熱,健脾益腎,濡養經筋,治療患者排尿困難;配合針刺太溪、昆侖益氣養精,活血通絡。應用偶刺法和相應穴位的補瀉手法可達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的治療目的[6]。
近年來,偶刺法廣泛應用于婦科、內科、骨科等疾病的治療中。宋家敏[7]應用偶刺法治療乳腺增生癥,結果顯示患者乳腺結節明顯縮小。高珊杉等[8]應用偶刺法聯合電針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上腹痛綜合征,結果顯示患者的消化不良癥狀及生活質量均明顯改善。現代醫學認為,針刺通過促進內源性阿片肽釋放,上調炎性反應中的局部內啡肽和周圍阿片受體,抑制內源性致痛物質的產生,提高機體痛閾及耐痛閾,從而有效緩解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9]。陳邦國教授運用以膝關節前后取穴為主的偶刺法治療膝骨關節炎,可有效緩解患者膝關節疼痛、腫脹癥狀[10]。
本案以偶刺法為主針刺治療帶狀皰疹性脊髓炎,治療思路明確,辨證得當,療效甚好,結束針刺時患者可獨立行走,自主排尿,胸背部疼痛感明顯緩解,表明該療法可減輕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為臨床治療相關疾病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