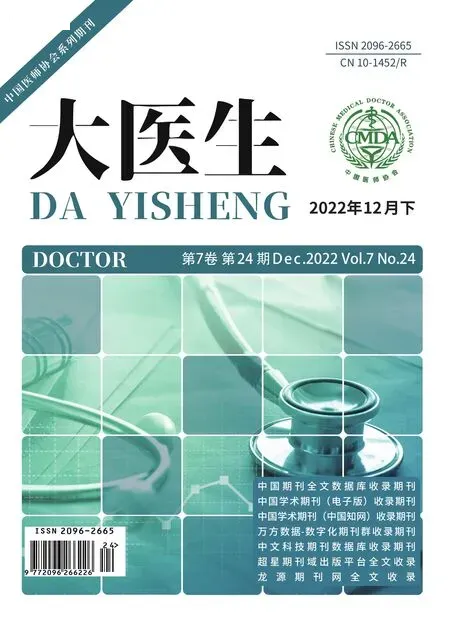布拉酵母菌聯合雙歧桿菌四聯活菌治療輪狀病毒性胃腸炎患兒的療效
陳 杰
(泗水縣人民醫院兒科,山東濟寧 273200)
輪狀病毒性胃腸炎好發于秋季,且多以嬰幼兒為主,主要由于嬰幼兒自身免疫機制發育未完全,患兒臨床癥狀主要有發熱、嘔吐、腹脹、腹瀉等,嚴重時還可誘發患兒脫水、酸中毒及機體電解質失調,威脅幼兒的健康成長[1]。此前對于該病臨床尚無特效藥物治療,主要通過補液糾正水電解質失衡并進行食療等方式改善患兒癥狀,但由于無法對其腸道菌群進行有效調節,故整體臨床療效不佳[2]。現階段,在小兒腹瀉的治療中應用益生菌已取得較好的效果,其中雙歧桿菌四聯活菌為復方益生菌制劑,具有補充正常生理細菌、調節腸道菌群、維持腸道正常蠕動等作用;布拉酵母菌則是微生態制劑,在進入患兒腸道后,可與致病菌競爭,從而維持腸道菌群的平衡,亦有利于免疫功能的調節[3]。基于此,本文通過隨機對照的方式,選取70例輪狀病毒性胃腸炎患兒,探討布拉酵母菌聯合雙歧桿菌四聯活菌治療方案的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1年1月至12月泗水縣人民醫院收治的輪狀病毒性胃腸炎患兒70例,按數字隨機表法分為對照組(口服蒙脫石散及雙歧桿菌四聯活菌治療)與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之上再聯合布拉酵母菌治療),各35例。對照組患兒中男性19例,女性16例;年齡3個月~7歲,平均年齡(2.88±1.26)歲;體質量指數(BMI)5~26 kg,平均BMI(10.78±2.14)kg。觀察組患兒中男性20例,女性15例;年齡2個月~7歲,平均年齡(2.76±1.18)歲;BMI 5~25 kg,平均BMI(10.66±2.06)kg。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經泗水縣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兒家屬對研究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納入標準:①滿足《現代臨床兒科疾病學》中輪狀病毒性胃腸炎的診斷標準[4],且大便樣檢輪狀病毒(+);②認知功能無異常。排除標準:①嚴重器質性損傷者;②對本研究用藥過敏者;③嚴重營養不良者。
1.2 治療方法 對照組患兒口服蒙脫石散(海南先聲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9990307,規格:3 g×10袋)及雙歧桿菌四聯活菌(杭州遠大生物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S20060010,規格:0.5 g×24片)治療。其中蒙脫石散根據患兒年齡調整服藥劑量:2歲以下1.5 g/次;2歲以上3 g/次,均以溫水沖服,3次/d。雙歧桿菌四聯活菌1 g/次,2次/d。觀察組則在對照組基礎上,聯用布拉酵母菌[BIOCODEX(法國),國藥準字SJ20150051,0.25 g×6袋]治療,0.25 g/次,3次/d。兩組患兒均治療1周后評價療效。
1.3 觀察指標 ①兩組患兒臨床療效。顯效為治療1周后患兒臨床各項指標基本恢復正常,且大便次數、量及性質均恢復正常;有效為治療1周后患兒臨床各項指標部分恢復,大便次數、量及性質部分正常;無效為治療1周后患兒各臨床指標及大便次數、量及性質等均未見好轉或有加重跡象。臨床總有效率=顯效率+有效率。②兩組患兒大便次數及腹瀉持續時間比較。于治療前、治療1周后分別觀察記錄患兒的大便次數,并統計其腹瀉的持續時間。③兩組患兒胃腸激素指標比較。于治療前、治療1周后采集患兒空腹外周靜脈血4 mL,經3 000 r/min離心10 min,取上層血清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其胃泌素(GAS)、胃動素(MOT)、血管活性腸肽(VIP)水平。④兩組患兒炎癥因子水平比較。取血方法、檢測方法同③,測定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2(IL-2)、白細胞介素-10(IL-10)水平。⑤兩組患兒T淋巴細胞亞群水平比較。取血方法同③,取上層血清以流式細胞儀(美國BD公司,型號:FACSCalibur)檢測CD4+、CD8+水平。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1.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用[例(%)]表示,行χ2檢驗;計量資料用(±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比較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兒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患兒總有效率為94.29%高于對照組的77.14%,差異顯著(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兒臨床療效比較[例(%)]
2.2 兩組患兒大便次數及腹瀉持續時間比較 治療后在大便次數這方面的比較可以看出,兩組患兒次數均有所減少,觀察組顯著少于對照組,且觀察組腹瀉持續時間短于對照組,差異顯著(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兒大便次數及腹瀉持續時間比較( ±s )

表2 兩組患兒大便次數及腹瀉持續時間比較( ±s )
注:與治療前比較,*P<0.05。
組別 例數 大便次數(次) 腹瀉持續時間(d)治療前 治療后觀察組 35 7.75±0.90 3.74±0.46* 3.65±1.15對照組 35 7.71±0.86 4.54±0.67* 4.73±1.36 t值 0.190 5.824 3.587 P值 0.850 <0.001 <0.001
2.3 兩組患兒胃腸激素指標比較 治療后兩組患兒GAS、MOT、VIP水平均降低,且觀察組水平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兒胃腸激素指標比較( ±s )

表3 兩組患兒胃腸激素指標比較( ±s )
注:與治療前比較,*P<0.05。GAS:胃泌素;MOT:胃動素;VIP:血管活性腸肽。
組別 例數 GAS(μg/L) MOT(μg/L) VIP(pg/mL)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觀察組 35 92.12±8.66 75.25±6.59* 557.89±64.37 265.58±40.58* 29.52±2.76 23.16±2.14*對照組 35 91.87±8.52 82.46±7.42* 559.31±65.63 312.73±47.63* 29.35±2.63 26.86±2.58*t值 0.122 4.298 0.091 4.458 0.264 6.530 P值 0.904 <0.001 0.928 <0.001 0.793 <0.001
2.4 兩組患兒炎癥因子比較 治療后兩組患兒TNF-α水平均下降,觀察組水平低于對照組,而兩組患兒IL-2、IL-10水平均升高,且觀察組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兒炎癥因子比較( ±s )

表4 兩組患兒炎癥因子比較( ±s )
注:與治療前比較,*P<0.05。TNF-α:腫瘤壞死因子-α;IL-2:白細胞介素-2;IL-10:白細胞介素-10。
組別 例數 TNF-α(μg/L) IL-2(pg/mL) IL-10(pg/mL)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觀察組 35 4.56±0.87 1.44±0.42* 39.97±5.11 70.37±7.34* 33.32±5.86 68.53±8.85*對照組 35 4.61±0.92 2.86±0.54* 40.16±5.15 59.83±6.85* 33.25±5.74 50.28±7.63*t值 0.234 12.280 0.155 6.211 0.051 9.240 P值 0.816 <0.001 0.877 <0.001 0.960 <0.001
2.5 兩組患兒T淋巴細胞亞群水平比較 治療后兩組患兒CD4+水平均升高,觀察組水平高于對照組,而兩組患兒CD8+水平均降低,且觀察組水平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5。
表5 兩組患兒T淋巴細胞亞群水平比較(%,±s )

表5 兩組患兒T淋巴細胞亞群水平比較(%,±s )
注:與治療前比較,*P<0.05。
組別 例數CD4+ CD8+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觀察組3535.11±2.1945.63±3.57*31.95±1.7824.25±1.06*對照組3534.84±2.1540.06±2.63*32.08±1.8428.83±1.77*t值 0.521 7.432 0.300 13.133 P值 0.604 <0.001 0.765 <0.001
3 討論
輪狀病毒性胃腸炎屬于嬰幼兒時期常見且多發的感染性疾病,其主要會造成細胞損傷進而導致腹瀉。對小兒輪狀病毒性胃腸炎,臨床主要針對脫水、腹瀉等采取對癥和支持治療。但是由于輪狀病毒性胃腸炎患兒腸道菌群失衡,會導致腸道黏膜保護功能失效,從而發生腹瀉等癥狀,且腹瀉會進一步導致腸道菌群及黏膜保護功能失衡,進而形成惡性循環[5]。因此,在改善患兒臨床癥狀的同時要加強攝入益生菌以完成對腸道菌群的重建,這樣不僅可促進腹瀉癥狀的改善,還可維持腸道內菌群的平衡。
現階段臨床常用的益生菌包含細菌類和真菌類微生態制劑,而作為細菌類微生態制劑,雙歧桿菌四聯活菌進入腸道后可對人體所需的各種正常細菌進行直接補充,同時,還可對腸道的蠕動起到促進作用,激發機體免疫力[6]。而布拉酵母菌則屬于真菌類微生態制劑,該種益生菌不屬于人體腸道菌群,其不會被腸道吸收,主要在患兒腸道內起到一過性的微生態調節功效。布拉酵母菌在進入患兒腸道后,可發揮抗病毒、抗微生物及營養腸道黏膜等作用[7]。
本次研究中,觀察組患兒的總有效率為94.29%高于對照組的77.14%高于對照組,且治療后大便次數、腹瀉持續時間均少于、短于對照組,GAS、MOT、VIP水平均低于對照組(均P<0.05),提示布拉酵母菌聯合雙歧桿菌四聯活菌治療可提高療效,縮短患兒的臨床癥狀改善時間,并促進腸道黏膜的生長及修復,進而達到改善腸道功能的目的。原因在于,布拉酵母菌可迅速在腸道定植,并形成厭氧環境,促進雙歧桿菌及乳酸菌的生長,兩種益生菌聯用后可起到協同增效的作用,促使患兒的臨床癥狀得到快速改善[8]。
輪狀病毒性胃腸炎的致病機制與機體炎癥反應、免疫應答機制有緊密聯系,該病毒能夠激活患兒機體內的抗炎信號,并分泌大量炎癥因子,進而導致疾病的不斷進展。其中IL-2主要源于CD4+T細胞分泌,同時利用NK細胞、巨噬細胞和T淋巴細胞上調免疫應答,故IL-2的升高對輪狀病毒感染的細胞免疫應答和抗體能力均有增強作用,對受到損傷的腸道上皮細胞也有顯著的修復作用。IL-10能夠使機體中的巨噬細胞特異性免疫功能得到抑制,使免疫誘導得到加強,最終將巨噬細胞對炎癥因子的釋放能力進行一定程度地降低,減少黏附分子的表達[9]。本次研究中,治療后觀察組患兒的TNF-α水平低于對照組,而其IL-2、IL-10水平則均高于對照組(均P<0.05);治療后觀察組患兒的CD4+水平高于對照組,CD8+水平則低于對照組(均P<0.05),提示聯合用藥方案可減輕患兒炎癥反應,并提升其機體免疫功能,促進患兒的盡早康復。原因考慮為,布拉酵母菌可通過激活網狀內皮系統以及補體系統促進患兒抗病性,并通過抑制炎癥信號轉導達到抗炎、增強免疫機制的目的[10]。
綜上所述,布拉酵母菌聯合雙歧桿菌四聯活菌可提高療效,促進輪狀病毒性胃腸炎患兒腹瀉癥狀和腸道功能的改善,并減輕炎癥反應,提高免疫能力,值得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