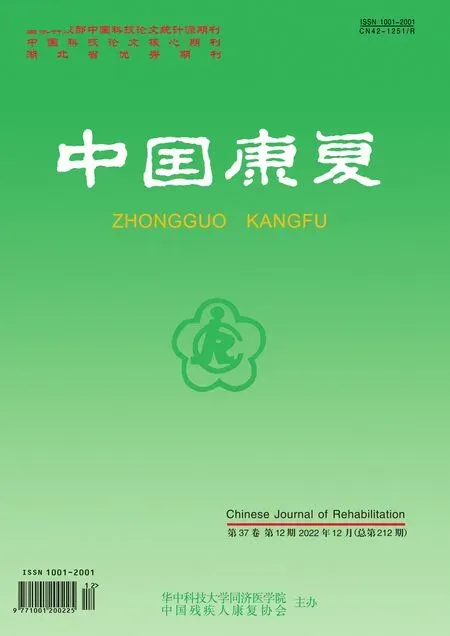腦卒中后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康復治療
張立超,馮婷怡, 2,李源莉,單春雷,
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是腦卒中后常見的功能障礙之一,對其進行評定和康復治療是腦卒中康復中重要的一部分[1]。盡管有大量關于卒中后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文獻,但對其診斷、評估缺乏共識,臨床治療方法單一,關注度不足。本文對腦卒中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有關的臨床表現(xiàn)、神經(jīng)機制、評定、常規(guī)康復治療及基于神經(jīng)調控的干預模式進行歸納總結,為進一步探究其機理及臨床康復治療提供依據(jù)和幫助。
1 腦卒中后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臨床表現(xiàn)
自主神經(jīng)系統(tǒng)在大腦和脊髓中具有高度復雜的解剖和功能組織,通過不同的網(wǎng)絡對正常和異常的心血管功能產(chǎn)生重大影響。腦卒中后心血管問題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表現(xiàn)為血壓不穩(wěn)定、體位性低血壓、發(fā)熱和心律失常,嚴重的出現(xiàn)腦心綜合征等[2]。有一些研究表明患者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與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有關[3]。還有一些研究認為膀胱過度活動(尿急和尿頻)或短暫性尿潴留與腦梗死導致短暫的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膀胱充盈期間感覺障礙和排尿期間的逼尿肌活動不足等原因有關[4]。另外有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交感神經(jīng)過度活動可能抑制胃腸蠕動最終導致便秘[5]。卒中后肩-手綜合征(should-hand syndrome, SHS)是一種以疼痛、出汗、手腫脹、血管運動不穩(wěn)定和運動功能受損為特征的慢性疾病,患者存在肢體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和炎癥,包括卒中后復雜性區(qū)域疼痛綜合征(complex regional syndrome, CRPS)或上肢反射性交感神經(jīng)營養(yǎng)不良[6]。
臨床上存在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腦卒中患者一般預后較差。Korpelainen等[7]發(fā)現(xiàn)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6個月后心率變異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受損與神經(jīng)功能障礙嚴重程度呈一定正相關性。Li等[8]發(fā)現(xiàn)AIS 3個月后,相比輕微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患者,嚴重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患者預后較差。Eleonora等[9]研究表明心率變異性增加和迷走神經(jīng)控制降低的急性非心源性卒中患者有發(fā)生譫妄的風險。Arboix等[10]認為有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腦卒中患者可能有發(fā)生心臟并發(fā)癥的風險,導致不良結局與死亡率增高。
2 腦卒中后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神經(jīng)機制
研究表明高HRV可能導致卒中風險增加,長期以來,“自下而上”的機制被認為是自主神經(jīng)調節(jié)的主要方式,其依賴于周圍神經(jīng)、激素與內啡肽。血液中激素及內啡肽物質的改變激活相關的腦干結構(如延髓腹外側核、背內側核等),再經(jīng)由周圍神經(jīng)系統(tǒng)來對心臟和血管作出相應調控,從而維持人體正常心血管內環(huán)境,降低卒中風險[11]。與之相對,“自上而下”的機制則是大腦皮質對周圍神經(jīng)影響的方式,其涉及到感覺運動皮質、內側前額葉皮質和島葉皮質等主要腦區(qū)[12]。這些腦區(qū)自身或通過影響與情緒相關的邊緣系統(tǒng)來激活涉及皮膚電導、瞳孔反應、心率和呼吸頻率等變化的交感神經(jīng)高興奮性狀態(tài)。許多腦卒中患者都被發(fā)現(xiàn)皮膚電導反應和心率變異性與健康人不同,同時急性期和病程6個月均出現(xiàn)交感神經(jīng)皮膚反應(sympathetic skin reaction, SSR)雙側異常[13],這一結論也支持了大腦皮質對自主神經(jīng)有調控作用。
腦卒中后血壓異常的調節(jié)包含中樞機制和外周機制,例如交感神經(jīng)活性降低導致持續(xù)血管舒張。壓力反射的調節(jié)是由孤束核和延髓頭端腹外側核介導的。大腦皮質如島葉(insular cortex, IC)、丘腦和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的興奮性抑制也會引發(fā)此癥狀[14]。研究發(fā)現(xiàn)IC是心臟自主神經(jīng)興奮性的主要調節(jié)中心[15]。同時在關于抑郁癥的機制研究中[16],對膝下前扣帶回皮層(sub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ACC)的腦深部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取得了不俗的療效。Tao等[17]在分析了與sACC密切相關的解剖位置相對表淺的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 PFC)的解剖連接后,發(fā)現(xiàn)右側和左側PFC均與sACC緊密連接,但兩半球之間的峰值解剖連接坐標略有不同:左側PFC在解剖和功能上直接與sACC相連,而右側PFC則與后扣帶回皮質(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相連。其解剖連接的不同提示了不同精神癥狀患者對應不同的PFC部位機制。鑒于早年的研究發(fā)現(xiàn)應激事件的發(fā)生會激活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 HPA)軸[18],會導致與焦慮、抑郁等精神狀態(tài)相關的糖皮質激素分泌急劇增加。而應激反應由連接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 PFC)和杏仁核(amygdala)的神經(jīng)回路控制,其中背外側前額葉(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對杏仁核產(chǎn)生抑制作用[19],也會影響相關激素釋放。以上機制為腦卒中后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中樞神經(jīng)機制探究和治療提供了前期理論依據(jù)。
3 主要評定指標與臨床治療
3.1 主要評定指標 臨床上有很多方法用以評估腦卒后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20],包括HRV、立位血壓變化、抬頭傾斜測試、等長握力、出汗定量(蒸發(fā)量測定法)、壓力反射敏感性、Valsalva動作、深呼吸心率反應,以及血漿兒茶酚胺含量、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6以及超敏C反應蛋白等檢驗指標。自主反應篩查作為腦卒中后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評估的工具量表,通過對自主神經(jīng)功能評估進行量化,具有評估交感神經(jīng)和副交感神經(jīng)自主神經(jīng)功能的優(yōu)勢,同時考慮了節(jié)前和節(jié)后結構[21]。它包括:使用定量泌汗運動軸突反射試驗(一個上肢和三個下肢部位)評估節(jié)后交感泌汗運動功能;使用深呼吸心率反應和Valsalva比率評估心臟迷走神經(jīng)功能;在Valsalva動作和抬頭傾斜試驗期間,測定心臟腎上腺素功能。HRV稱心率變異性,是自主神經(jīng)調控心臟的評定指標,也是臨床上運用最廣泛的指標之一,它反映正常竇性心搏之間心動周期頻率和時間的區(qū)別[22]。低頻率(low frequency, LF)與高頻率(high frequency, HF)之比(LF/HF)來反映心臟節(jié)律性改變規(guī)律及自主神經(jīng)對心腦系統(tǒng)的影響,其中LF表示交感神經(jīng)功能而HF與副交感神經(jīng)特異性有關,故LF/HF越低副交感神經(jīng)占優(yōu)勢,反之交感神經(jīng)占優(yōu)勢[23]。目前HRV分析方法包括頻域、時域和非線性分析,通常使用動態(tài)心電圖檢測。也有學者在臨床上使用SSR測定評估PSD導致的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24]。這是一種電生理測試,記錄交感神經(jīng)系統(tǒng)激活后皮膚電導的變化,腦卒中后CRPS患者交感神經(jīng)活動過度,SSR可能增加。
3.2 康復治療
3.2.1 呼吸訓練、有氧運動和心理治療 常規(guī)的呼吸訓練、心理治療和有氧運動可以調控腦卒中患者自主神經(jīng)功能。章志超等[25]發(fā)現(xiàn)常規(guī)康復干預(包括藥物治療)結合漸進性吸氣肌抗阻訓練及呼吸控制訓練能有效改善PSD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抑郁情緒狀態(tài)及HRV指標。容偉等[26]通過心理干預結合帕羅西汀治療PSD患者后發(fā)現(xiàn)患者漢密爾頓抑郁量表評分、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shù)評分、詞語流暢性測驗、SSR波起始波潛伏期及波幅均明顯優(yōu)于治療前,患者體內5-羥色胺水平提高,抑郁狀態(tài)及自主神經(jīng)功能得到明顯改善。Yao等[27]使用生理相干與自主平衡系統(tǒng)(self-generate physiological coherence system, SPCS)發(fā)現(xiàn)其可以減輕患者的疲勞和抑郁,改善患者的HRV。腦卒中后患者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tǒng)呈現(xiàn)病理狀態(tài),焦慮、抑郁等消極情緒的產(chǎn)生過程與交感神經(jīng)和自主神經(jīng)的神經(jīng)調節(jié)機制有關。SPCS是以心腦交互作用理論和減壓理論為基礎的心肺訓練系統(tǒng),動態(tài)顯示患者訓練時的HRV的變化,幫助平衡患者的自主神經(jīng)系統(tǒng),協(xié)調和改善HRV,改變腦電波活動,促進額葉底部與杏仁核纖維束連接。Rodrigo[28]的研究表明腦卒中患者在休息時LF/HF和整體變異性較低,副交感神經(jīng)占優(yōu)勢,在有氧運動時交感神經(jīng)占優(yōu)勢,并且在休息30min后LF/HF沒有恢復到基線水平,與健康老年人反應一致,此前HRV模式分析已運用于健康人群的運動處方制定,提示其也可以作為一種簡易且無創(chuàng)的評估工具,幫助腦卒中患者制定安全有效的運動處方。
3.2.2 其他傳統(tǒng)物理療法 AZRA等[29]研究表明,相比于經(jīng)皮神經(jīng)電刺激(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TENS)治療,在腦卒中反射性交感神經(jīng)營養(yǎng)不良患者肩關節(jié)三角肌、肱二頭肌長頭肌腱進行激光照射療法可以減少肩關節(jié)疼痛,減輕手背腫脹程度,降低抑郁發(fā)生率,改善日常生活能力。以往很多學者對于SHS治療更多關注于腫脹、疼痛、關節(jié)活動度等功能障礙問題,也有一部分學者通過調控交感神經(jīng)進行治療。Sourov等[30]用鏡像療法治療腦卒后上肢交感神經(jīng)營養(yǎng)不良后發(fā)現(xiàn)與對照組相比,鏡像治療的試驗組在水腫、疼痛強度、功能活動指標上的改善更顯著。在隨訪2周時,改善得以持續(xù)。淋巴組織中存在交感神經(jīng)元,交感神經(jīng)系統(tǒng)與炎癥密切相關,腦卒中患者表現(xiàn)出較弱的延遲交感反應和交感功能障礙,導致皮膚血管收縮和循環(huán)不良,進而導致SHS患者肢體內炎性液體積聚。因此,通過針對動機和意識進行的鏡像治療可能通過誘導抗炎癥反應,激活交感神經(jīng)群發(fā)的活動,以糾正水腫[31]。徐勝等[32]發(fā)現(xiàn)神經(jīng)松動術可以有效改善卒中后痙攣模式所導致的周圍神經(jīng)活動性下降和張力增高,從而緩解SHS伴隨的的交感神經(jīng)癥狀,提高交感營養(yǎng)狀態(tài)。Asli等[33]研究表明常規(guī)物理治療結合上肢有氧運動是治療CRPS的一個很好的綜合方法,患者疼痛、抑郁及健康狀態(tài)得到顯著改善。其治療機制是CRPS中的神經(jīng)源性炎癥是由神經(jīng)肽(如P物質、血管活性腸蛋白和緩激肽)觸發(fā)的,在進行交感神經(jīng)干預后,疼痛和炎癥減輕[34]。Burcy等[35]將腦卒中患者分為CRPS組和無CRPS組,冷熱交替浴(contrast bath, CB)治療后2組癱瘓手的SSR振幅均顯著降低,此外,CB降低了CRPS組健康側手的SSR振幅,而無CRPS組無顯著變化,一方面大面積的大腦皮層激活具有跨半球作用,而CB利用大面積感覺運動皮層興奮性提高來影響多模態(tài)感覺加工,另一方面表明CB具有降壓作用,降低交感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張力,增強體質,減少心肌耗氧量。也有研究表明CB在冷水浴結束時對交感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張力有更明顯的作用[36]。
3.2.3 針灸 我國傳統(tǒng)的針灸治療對自主神經(jīng)也有調控作用。王軒等[37]發(fā)現(xiàn)針刺曲澤穴組時logLF/HF與治療前比增高,針刺曲澤穴和天井穴時LF、HF與治療前比較降低,都可使HRV頻域指標達到正常范圍,且相比之下針刺曲澤穴能更好調控患者自主神經(jīng)平衡性。文立楊等[38]發(fā)現(xiàn)相比于針刺非經(jīng)非穴組(左側大鐘穴下1cm),針刺大鐘穴組各個時間段(針刺前、針刺時、留針時、出針時、出針后)的LF、HF、LF%、HF%、TP低于非經(jīng)非穴組,大鐘穴組針刺各個時間段LF/HF高于非經(jīng)非穴組,提示針刺左側大鐘穴可以降低右側腦梗死患者交感神經(jīng)活性和迷走神經(jīng)活性,改善患者交感神經(jīng)與自主神經(jīng)的平衡張力,降低患者總的自主神經(jīng)功能,治療還具有一定的針刺遺留效應。張亞君等[39]通過針刺內關、氣海、水溝、人迎、血海等穴發(fā)現(xiàn)腦卒中導致的腦心綜合征患者心血管和神經(jīng)系統(tǒng)反應明顯減少,心腦保護效應加強,其機制可能為心臟自主神經(jīng)狀態(tài)被調節(jié)后抑制應激反應從而減少兒茶酚胺的含量有關。
3.2.4 遠端缺血后適應 遠端缺血后適應(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RIPostC)是指靶器官在缺血持續(xù)一段時間之后,在遠端器官進行幾輪短暫缺血和再灌注循環(huán)缺血的適應,對靶器官有較好的內源性保護作用[40]。Lin等[41]發(fā)現(xiàn)AIS患者在健側上臂接受4個周期的交替充氣(袖套充氣至200mmHg)和放氣,每次5min,每天1次,共30d。通過HRV評估自主神經(jīng)功能,結果提示除LF/HF以外,所有HRV參數(shù)均隨時間顯著增加。RIpostC組在第7d和第30d所有正常R-R間期(SDNN心動周期標準差)和高頻的標準偏差值,以及在第30d相鄰正常R-R間期(pNN50)之間的差異百分比值均顯著高于假刺激組,PNN描述心動周期的逐搏變異,比值越大提示迷走神經(jīng)張力越高,表明30d 的RIpostC訓練可通過增強腦卒中患者的總自主神經(jīng)活動和迷走神經(jīng)活動,減少殘疾的發(fā)生,其介導自主神經(jīng)功能的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魏琳等[42]通過Ewing測試和HRV等方法評估也發(fā)現(xiàn)遠端缺血后適應有類似的結論。
3.2.5 非侵入性神經(jīng)調控 大腦皮質是心血管等自主神經(jīng)控制的關鍵結構,所以認為能有效調節(jié)大腦皮質功能的非侵入性神經(jīng)調控技術例如經(jīng)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和經(jīng)顱直流電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等可通過對大腦皮質產(chǎn)生持續(xù)、長時程的影響來調節(jié)心率,血壓等自主神經(jīng)興奮性,在腦卒中、自閉癥譜系障礙[43]、神經(jīng)退行性疾病、運動障礙、耳鳴、慢性疼痛和功能性神經(jīng)障礙等神經(jīng)疾病中廣泛應用。Hasan等[44]在一項CPSP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使用10Hz高頻rTMS作用于患側初級運動皮質(M1)可以有效緩解CPSP患者上肢疼痛并降低熱閾值,改善冷感覺。但實驗不能確認熱閾值降低相關的島葉和ACC的激活是M1區(qū)直接影響亦或是通過初級感覺皮層(S1)或丘腦來間接影響。Malfitano等[45]同樣使用10Hz的rTMS作用于CPSP患者M1區(qū)減輕患者疼痛的主觀感覺、提高痛閾,同時通過對患者神經(jīng)電生理指標的分析發(fā)現(xiàn)與健康人相比反映皮質-皮質興奮性的指標ICF雙側均抑制、iSP持續(xù)時間減少,同時反映皮質-脊髓興奮性的rMT并未受到影響,作者認為這一結果或許與γ-氨基丁酸選擇性的抑制雙側通路或是與參與疼痛感覺評估來調節(jié)運動皮質興奮性相關的丘腦損傷相關。同樣是針對中樞性疼痛(central neuropathic pain, CNP)的研究,Galhardoni等[46]使用真假10Hz深部重復性經(jīng)顱磁刺激(deep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dTMS)作用于腦卒中或脊髓損傷導致的CNP患者的腦島后上葉(posterior superior insula, PSI)或ACC,發(fā)現(xiàn)只有真刺激作用于PSI的CPN患者的熱閾值降低,故支持選用島葉作為CNP治療的主要靶點。根據(jù)Okano等[47]的研究,在10名運動員的左側顳葉(temporal cortex, TC)也就是T3點上使用10mA的陽極tDCS后LF/HF降低,同時測得左TC的誘導電場且實驗組主觀疲勞量表評分下降。以此為基礎,Heinz等[48]在腦卒中患者進行跑步機訓練前使用電流強度2mA的tDCS陽極放置于左TC,結果同樣支持tDCS能影響副交感神經(jīng)調制。而在AIS的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研究方面,He等[49]將頻率為18kHz電流強度10mA的經(jīng)皮乳突電刺激(percutaneous mastoid electrical stimulator, PMES)應用于發(fā)病時間3h內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成功緩解AIS患者的HRV異常。
4 小結與展望
腦卒中的各個階段常伴隨不同的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對患者后期的功能恢復、心理健康和社會家庭職能回歸均造成重大阻礙。其發(fā)生和作用機制涉及體液、免疫、神經(jīng)等多方面,目前仍在探索中。前文總結了目前臨床上主要的中西醫(yī)結合物理康復治療和非侵入性神經(jīng)調控干預腦卒中后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理論機制和方法。然而即使國內外對腦卒中后的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高度關注,但實際臨床療效依然欠佳,療效維持的時間也較短,評估指標也無統(tǒng)一。國內研究多集中于腦卒中后遺癥期,而針對急性期的干預方式稀少且單一。因此針對腦卒中后自主神經(jīng)功能障礙的機制和干預新方法值得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