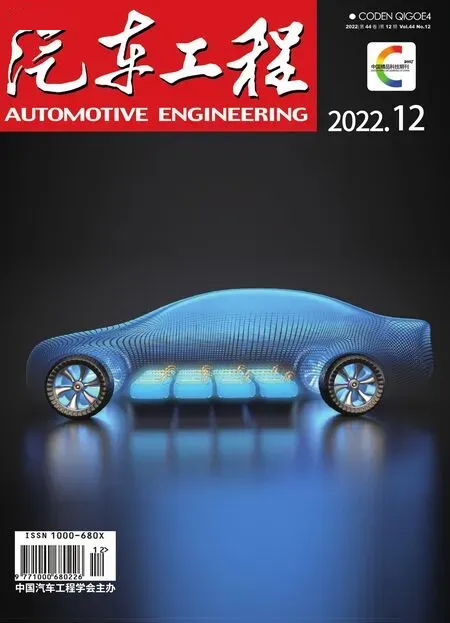雙離合器協同的功率分流式混合動力汽車動態協調優化控制研究*
施德華,容香偉,汪少華,張開美,陳 龍,李 春
(1.江蘇大學汽車工程研究院,鎮江 212013;2.汽車零部件先進制造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重慶理工大學),重慶 400054;3.金龍聯合汽車工業(蘇州)有限公司,蘇州 215026)
前言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技術路線圖2.0》中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混合動力技術,其中高集成度、高性能的功率分流式混合動力汽車(hybrid electric vehicle,HEV)更是研究的熱點[1]。面對結構更智能的動力耦合裝置的需求,國內外科研機構和整車企業相繼推出了集成多離合器的功率分流式動力耦合裝置[2],但復雜的多離合器構型對HEV瞬態模式切換的動態協調控制帶來了更大挑戰,影響駕駛平順性。
為改善HEV由純電動切換至混合動力模式時伴隨發動機起動及離合器狀態切換對行駛平順性造成的不利影響,國內外研究學者基于模型預測控制、滑模控制和動態規劃等算法對發動機起動轉速進行優化[3-5],以提高發動機起動階段或離合器狀態變化時的切換品質,但這些控制策略計算量大、實際應用較為復雜。針對發動機起動需求,Chen等[6]基于功率分流式傳動系統的耦合特性設計了前饋-反饋控制器。Chen等[7]設計一款連接發動機與變速器的新型阻尼離合器,并根據行星排傳動系統的耦合特性研究了發動機起停過程降低轉矩波動的方法。汪佳佳等[8]針對一款功率分流式傳動系統提出基于電機補償的協調控制方法。同時,為解決模式切換過程中離合器狀態切換的問題,Yang等[9]基于一款同軸并聯混合動力客車,將切換過程劃分為5個子階段并基于H∞魯棒控制設計動態協調控制器。秦大同等[10]結合二次型最優控制研究AMT與DCT離合器的起步與換擋過程。Zhu等[11]根據離合器和發動機的工作狀態將模式切換過程劃分多個子階段,采用模糊PID控制設計轉矩反饋補償器降低切換沖擊,并通過最優控制改善了離合器滑摩損失。然而,上述控制方法的設計僅針對單離合器的傳動系統,鮮有研究雙離合器協作下伴隨發動機起動過程的模式切換。
針對集成多離合器的功率分流式混合動力系統,通過控制不同離合器的工作狀態組合可以實現更豐富的工作模式,擴大動力源經濟工作區間,但在進行模式切換時,往往伴隨兩個離合器工作狀態的協同變化(超過兩個離合器協同的復雜情況應避免)[12],而不同離合器滑摩時的功率分流式傳動系統不僅自由度增加,耦合效果減弱,而且隨著發動機起動、離合器工作的非連續性進一步導致控制變量增多,協同狀態發生遷移,在面對不同加速工況時,對動力源輸出轉矩分配更加敏感,極容易引起總輸出轉矩的波動,造成瞬態模式切換品質的下降。
本文中以一款集成多離合器的功率分流式HEV為對象,開展包含兩個離合器狀態協同切換的純電動模式到混合動力模式的動態協調優化控制策略研究。通過分析其瞬態模式切換行為,確定各個切換階段不同動力源及離合器動態協調控制方法,在此基礎上,基于模擬退火算法優化雙離合器的協同滑摩行為,并提出面向不同加速工況的發動機轉速自適應調節策略,通過電機MG1輸出轉矩的自適應調節提高大范圍運行工況下的整車瞬態模式切換品質,為集成多離合器的功率分流式HEV動態協調控制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1 功率分流式混合動力汽車建模
1.1 模式切換動力學模型
所研究的功率分流式HEV構型如圖1所示,集成4個離合器的雙行星排構型實現發動機、電機MG1和MG2輸出動力的耦合。即發動機與前行星排PG1的齒圈R1相連,前行星排的行星架C1分別接有離合器CR3和CR1,電機MG1和MG2分別與PG1的太陽輪S1和后行星排PG2的太陽輪S2相連,PG2的齒圈R2通過離合器CR2與PG1的 太 陽輪S1相連,PG2的行星架C2連接離合器CR1和輸出軸。

圖1 混合動力構型
該構型模式切換常涉及雙離合器的協同工作,本文中以如圖2所示的純電動模式到混合動力模式的瞬態切換過程為研究對象,該切換過程具有典型性,不僅包含兩個離合器的協同作用,還涉及發動機起動過程。針對瞬態模式切換過程,基于杠桿法和矩陣法建立動力學模型[13],以CR1和CR3同時滑摩的階段為例,建立圖3所示的雙行星排杠桿模型。

圖3 雙行星排杠桿模型
根據圖3所示的杠桿模型,進一步通過矩陣的形式描述其動力學方程,如式(1)所示。
同理,建立純電動模式和混合動力模式的傳動系統動力學矩陣方程,如式(2)和式(3)所示。

式中:Ie、IR1、IMG1、IS1、IMG2、IR2和Iout分別為發動機、R1、MG1、S1、MG2、R2以及輸出軸的轉動慣量;IC1、IC2分別表示為離合器CR3與行星架C1的轉動慣量之和、離合器CR1與行星架C2的轉動慣量之和;ωe、ωC1、ωout、ωMG1、ωMG2分別為發動機、C1、輸出軸、MG1以及MG2的轉速;Te、TMG1、TMG2、TCR1和TCR3分別為發動機、MG1、MG2、CR1以及CR3傳遞的摩擦轉矩;K1、K2為行星輪系特征參數,且K1=K2;Tin為S1與R2連接間的內力矩;Tin1為CR3鎖止的內力矩;Tin2為行星架C1與C2之間的內力矩;Tout為輸出軸負載轉矩。Tout可由汽車平衡力矩方程計算:

式中:m為整車質量;g為重力加速度;θ為坡度角;froll為滾動阻力系數;ρ為空氣密度;Cd為空氣阻力系數;Av為迎風面積;v為車速;R為車輪半徑;ifd為主減速器傳動比。
整車模型參數如表1所示。

表1 整車模型參數
1.2 關鍵零部件建模
(1)發動機和電機模型
本文采用“1階慣性延遲環節”描述發動機和電機的瞬態轉矩輸出模型[14],發動機和電機輸出轉矩定義為

式中:α為節氣門開度;ωe為發動機轉速;τe、τMG1分別表示發動機和電機的動態響應時間,且τMG1遠小于τe;TMG_d為電機目標轉矩。
(2)離合器模型
國外大量離合器油壓試驗表明離合器接合過程及分離過程滑摩時的油壓曲線可描述為指數函數形式[15],進而結合濕式離合器摩擦轉矩表現形式[16],離合器接合和分離過程的摩擦力矩可表示為

式中:σ為油路充油速度相關的系數;tc為接合或者分離所用的時間;TCRj和TCRf分別定義為離合器接合目標轉矩、剛分離時轉矩;ωini、ωpas分別為離合器主、從動片轉速;μ為離合器摩擦因數;psj、psf分別為離合器結合與分離時的主油道油壓;Z為摩擦片個數;Ac為摩擦片面積;rw、rn分別為摩擦片外、內徑。研究中不考慮離合器摩擦因數μ的變化特性。
2 動態協調優化控制策略
2.1 雙離合器協同的模式切換行為分析
綜合考慮模式切換品質及發動機起動需求,在純電動模式,通過MG1將發動機調速至600 r/min以避免發動機在模式切換階段中因轉速耦合被反拖,并減少發動機到達怠速轉速(900 r/min)的時間。在發動機和雙電機聯合驅動的混合驅動模式階段,通過電機調速使發動機工作于經濟轉速區間。瞬態模式切換過程涉及兩個離合器的協同工作:CR3由鎖止經滑摩到分離,CR1則由分離趨向鎖止。
CR1和CR3的工作時序存在著豐富的組合方式,須結合發動機的起動需求進行切換可行性分析。因此,假設存在圖4中所示的4類雙離合器協同切換序列。

圖4 工作時序
假設a:CR3在CR1工作過程中分離(t0+t1、t0+t2表示CR3分離開始、結束時刻)。
假設b:CR1在CR3工作過程中結合(t0+t3、t0+t4表示CR1接合開始、結束時刻)。
假設c:CR1先結合、先鎖止,CR3后滑摩、后分離(t′1為CR3與CR1工作重合或間隔時間)。
假設d:CR3先滑摩、先分離,CR1后結合、后鎖止(t″0為CR3與CR1工作重合或間隔時間)。
其中,t1、t2、t3、t4分別為[0,(tf-t0)/2]內的值;當為重疊時間時當為間隔時間時
由式(6)可知,當離合器主、從動盤轉速差為正時,離合器摩擦轉矩為正,反之為負。假設b中,CR3先滑摩傳遞給行星架C1負摩擦轉矩,降低C1角加速度。雖然CR1滑摩會給C1傳遞正摩擦轉矩,但若CR3滑摩時間長于CR1滑摩時間,行星架C1的轉速很難與輸出軸轉速同步,難以完成模式切換,導致離合器無效工作。而假設a的CR3工作時間小于CR1,更容易縮小行星架C1與輸出軸轉速差,完成模式切換。同理,在假設c和d中,當CR1工作時間小于CR3時,很難迫使C1和輸出軸轉速同步;而在假設c和d中,當CR3工作時間小于CR1時,從切換時間角度來看,同等工作條件下的假設c和d切換時間要長于假設a,故綜合考慮切換時間和離合器的工作有效性,選擇假設a作為雙離合器工作時序。
在假設a的基礎上,可以通過控制t1、t2細分為更多的工作時序,但進一步考慮到雙離合器控制難度,選擇雙離合器同時分離、鎖止的時序最為簡單適宜,便于后續控制策略設計。結合純電動切換至混合驅動模式中發動機起動及CR1兩端轉速差的控制需求,可設計如圖5所示的模式切換邏輯。其中,vthr為切換速度閾值,取5.5 m/s。

圖5 模式切換邏輯圖
2.2 動態協調控制策略設計
為了改善不同加速工況下的功率分流式HEV模式切換品質,根據系統穩態轉矩分配、驅動軸動態加速以及發動機轉速調速等需求,建立各切換階段不同動力源轉矩分配策略。
2.2.1 純電動模式
純電動模式下兩電機均參與工作,針對系統的2自由度特征,采用PI轉速調節模塊由MG1調節發動機轉速,使發動機工作在目標轉速。根據行星排動力耦合機構轉矩平衡表達式并結合PI調速模塊對電機進行轉矩分配:

式中TPI1為純電動模式下PI轉速調節模塊的需求轉矩,具體表示為

式中:ωd為發動機目標轉速;kp1和ki1分別為純電動模式下PI調節模塊的比例、積分增益;Treq為輸出軸需求轉矩。Treq可基于結合汽車動力學平衡方程和PI控制的駕駛員模型求解,記為

式中:kp_req和ki_req分別為PI控制模型的比例和積分增益;vd為目標車速。
該模式系統沖擊度表示為

由式(10)可以看出,該模式系統沖擊度受到TMG2、Tout以及MG2加減速行為的影響。由于S1與R2相連,MG2與MG1的轉速成比例關系,又由于CR1鎖止,發動機與MG1轉速也成比例關系,因此,整車沖擊還將受到MG1對發動機PI調速功能的影響。當該模式切換到下一模式前,發動機轉速已達到目標轉速,純電動模式的PI調速模塊輸出轉矩經過較長時間已經趨于穩定,發動機轉速也趨于穩定,進而MG2轉速也趨于穩定,轉矩分配更多地表現為準穩態特性。在模式切換的瞬態過程,車速和加速度視為恒定,根據系統的轉速耦合行為和準穩態轉矩分配特性,系統模式沖擊度也幾乎為零。
2.2.2 雙離合器協同滑摩模式
該模式下CR1和CR3同時處于滑摩狀態,不同于前述純電動模式后期的準穩態行為,該瞬態切換階段離合器因滑摩傳遞輸出轉矩且各動力源轉速持續變化,系統沖擊度表示為

可以看出,該切換階段系統沖擊度將受到各動力源輸出轉矩以及不同行星排構件轉速(各動力源轉速)變化的影響。此時,由于瞬態切換車速變化不大,Tout可視為定值,而CR1和CR3均處于滑摩狀態,CR1和CR3傳遞的滑摩轉矩持續變化,如式(12)所示,僅按照能量管理策略的各動力源準穩態轉矩分配將導致驅動軸實際輸出轉矩與需求轉矩的失配,不同行星排構件轉速(各動力源轉速)持續變化。因此,為了減小輸出軸的轉矩波動,電機不僅需要提供目標車速和加速度下的驅動軸需求轉矩,還需要補償發動機的起動阻力矩和動力源加減速行為帶來的轉矩波動。進一步仍需協調離合器滑摩轉矩,發動機轉速可由離合器傳遞的摩擦轉矩提升至怠速。為此,設計如式(13)所示的MG1和MG2輸出轉矩動態協調控制律。


式中:σCR1和σCR3分別為CR1與CR3油路充油速度相關的系數;TCR1j為CR1接合時目標轉矩;TCR3f為CR3剛分離時轉矩,根據穩態轉矩方程可得TCR3f=(K1+1)Te;Te為起動阻力矩,同樣可根據發動機起動阻力數據通過BP神經網絡進行訓練預測。
CR1和CR3傳遞的摩擦轉矩是造成該階段各部件加減速和輸出軸轉矩波動的重要因素,為進一步減小由雙離合器協同滑摩造成的影響,通過優化CR1和CR3摩擦轉矩以提高該切換階段的瞬態工作品質。基于表征模式切換品質的沖擊度、滑摩功及切換時間3個指標建立加權優化目標,分別對CR1的接合目標轉矩TCR1j以及CR1與CR3油路充油速度相關的系數σCR1和σCR3進行參數優化,其中,離合器CR1的目標轉矩TCR1j僅需優化接合時主油路油壓ps即可,具體優化模型描述為

式中Q、P和O分別為沖擊度、滑摩功和切換時間的權重系數。
模擬退火算法能夠處理不同類型的優化設計變量,具有較強的全局收斂性和廣泛的自適應性[17],這種算法基于Metropolis準則重復進行“產生新解-計算目標函數誤差-接受(舍棄)新解”,通過控制溫度T使得固體內能E趨于最佳平衡狀態,通常表示為

式中:p為出現能量差為dE的降溫的概率;Em、En分別表示為新、舊時刻固體內能;T為固體溫度;k為常數。
本文中結合模擬退火算法將離合器動作參數TCR1j、σCR1和σCR3當做算法的解,通過逐步降溫并添加隨機干擾得到最優的目標函數值。將離合器傳遞轉矩限制在物理約束內,當其參數變化后得到的Jm小于Jn時,則接受該次變化,當參數變化后的Jm大于Jn時,則以一定概率繼續移動且此概率隨著時間而衰減。
2.2.3 混合動力模式
(1)切換沖擊機理分析
該階段CR1和CR2處于鎖止狀態,CR3和CR4分離,發動機參與驅動,雙行星排動力耦合機構具有2自由度,在根據能量管理策略確定各動力源穩態轉矩分配的基礎上,分別對MG1和MG2增加基于PI控制的動態轉矩調節模塊,由MG1和MG2調節發動機轉速,使發動機工作在目標轉速。MG1和MG2輸出轉矩為

式中:TMG1_stat和TMG2_stat分別為MG1和MG2根據能量管理策略得到的穩態輸出轉矩;TPI2和TPI3分別為混合動力模式下基于PI控制的MG1和MG2動態調節轉矩,PI轉速調節模塊的輸入均為發動機理想轉速與實際轉速的差值。
混合動力模式下,輸出軸沖擊度為

雙離合器協同滑摩階段切換到混合動力模式的初始階段,發動機轉速仍未達到目標轉速,階躍式的發動機轉速跟蹤使式(16)中MG1和MG2提供較大的動態調節轉矩,即TPI2和TPI3均不為零,由于行星排轉速耦合關系,發動機轉速動態調節也使MG1和MG2轉速隨之時變。另一方面,在該模式初始階段,發動機輸出轉矩由于響應遲滯尚未達到能量管理策略確定的穩態輸出轉矩,即dTe/dt不為零。因此,結合式(16)可知,該模式初始階段產生的沖擊不僅受到MG1和MG2對動力耦合機構調速功能的影響,也受到發動機響應遲滯特性的影響。
(2)自適應動態協調控制策略
針對發動機響應遲滯以及MG1和MG2調速導致的模式切換沖擊,構建如圖6所示的混合動力模式各動力源協調控制策略。在結合能量管理策略轉矩分配[18]以及PI控制的轉速調節的基礎上,針對MG1設計自適應調節系數實現不同加速工況下的MG1輸出轉矩自適應調節,MG2輸出轉矩還需要提供額外的補償轉矩TMG2_com以彌補由于發動機響應遲滯導致的發動機實際輸出轉矩與理想轉矩的差異。發動機轉矩控制指令Te_EM由能量管理策略給定,本文中主要研究瞬態模式切換行為,穩態能量管理策略在此不再贅述[19]。
圖6中,發動機響應遲滯補償轉矩可表示為

圖6 混合動力模式協調控制策略

式中Te_AEM為通過神經網絡估計的發動機輸出轉矩,可基于發動機動態響應輸出轉矩數據通過BP神經網絡訓練估計得到[20]。
由于駕駛汽車工況的復雜多變性,導致系統在切換至混合動力模式時發動機轉速與目標跟蹤轉速并非定值,因此,固定的調速模塊PI參數難以兼顧發動機轉速調節性能和輸出軸轉矩波動的限制。圖7對比了加速度分別為2、2.1和2.2 m/s2的不同加速工況下采用固定PI調節系數時的模式切換沖擊度。當加速工況為2.2 m/s2時,最大沖擊度為23.6 m/s3,超出我國限定的沖擊標準(17.64 m/s3),而對于2 m/s2的加速工況,最大沖擊度僅為8.8 m/s3,低于德國標準(10 m/s3),不同加速工況系統沖擊度差異顯著。這主要是因為,加速工況的改變使整車需求轉矩發生變化,從切換階段進入混合動力模式時,固定的PI調節系數使電機根據發動機轉速提供固定的調節轉矩,不隨加速工況改變,因此在混動階段初始時刻,各動力源轉矩經過耦合后難以滿足不同加速工況下的轉矩需求,降低切換品質。

圖7 不同加速工況下的沖擊度
針對固定PI調節參數無法保證大范圍工況下瞬態模式切換的高品質控制,提出MG1對發動機轉速的自適應調節方法。由式(16)可知,當不考慮MG1調速時,MG1的輸出轉矩與總需求轉矩Treq成正相關關系。結合式(17)的混合動力模式的沖擊機理分析可知,通過保持MG1輸出轉矩與整車需求轉矩成正相關的關系,就能夠維持總輸出轉矩平緩變化。為此,當考慮PI調速時,需要自適應PI調節系數能夠隨著加速工況的變化不斷調節參數使MG1輸出轉矩與整車需求轉矩維持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在某一加速工況下,通過優化選擇最優的PI調節參數以兼顧轉速調節性能且維持輸出轉矩平緩波動,并將此時的PI模塊的輸出轉矩與總需求轉矩之間的關系作為參考設計能實時調整的自適應調節系數。定義n為PI模塊輸出轉矩與總需求轉矩之間的關系,進而根據式(16)反向求解出自適應調節系數μ。

式中:TPI2_opt和Treq_opt均為通過某一工況下優化后得到的值;Te_EM在此瞬態中可視為定值。
結合式(16),混合動力模式下的各動力源輸出轉矩最終可表示為

通過引入MG1調速模塊的自適應調節系數μ即可實現MG1輸出轉矩面向不同加速工況的自適應調節,從而在實現發動機目標轉速控制的同時保證大范圍工況模式切換品質。
3 仿真結果與分析
為驗證本文提出的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分別對既無離合器滑摩轉矩優化也無發動機轉速調節自適應的切換策略(策略A)、僅有發動機轉速自適應調節(策略B)以及本文提出的動態協調優化策略(策略C)進行對比測試。通過前述動態協調控制方法選取1.8、2.3和2.8 m/s2的加速工況為測試工況,具體仿真參數如表2所示。

表2 仿真參數
表中:Q、P、O權值可通過權重系數除以基準值得到;沖擊度、滑摩功和切換時間的基準值可設計為17.64、2 200和0.55;權 重 系 數 分 別1.2、0.6和0.7。
圖8對比了不同控制策略下的模式切換評價指標,包括整車沖擊度、離合器滑摩功和模式切換時間。由圖8(a)可知,策略A未優化離合器參數,導致在模式切換過程中難以協調整車輸出轉矩,所產生的沖擊度最大絕對值可達15.1 m/s3,策略B未采用本文設計的自適應調節系數,在加速度為2.3 m/s2以上的工況下效果良好,但在1.8 m/s2的加速工況下沖擊度達到47.7 m/s3,無法適用于大范圍加速工況,而策略C既通過模擬退火優化參數又采用自適應調節系數,其沖擊度在不同的加速工況下均能保持在10 m/s3以內。圖8(b)和圖8(c)表明,策略B、C的滑摩功和切換時間一致,工況的變化僅影響到整車沖擊,而且相較于策略A,離合器參數經過模擬退火優化后,降低了離合器的滑摩功和模式切換時間,以1.8 m/s2的工況為例,策略A的滑摩功和切換時間分別為2 411 J、0.59 s,大于策略B、C的2 120 J和0.52 s,分別提升12.1%和11.9%。隨著加速工況的變化,切換時間也會隨之呈正相關變化,當離合器參數確定后,離合器滑摩產生的能量損失將會隨著切換時間降低而減小。

圖8 評價指標
通過對比A、B、C 3種策略在不同加速工況下的結果,發現本文設計的動態協調策略C在整個模式切換過程中都能保持良好的切換品質。
圖9給出了策略B、C下行星排混合動力系統不同部件轉矩和轉速的動態響應。由圖9(a)可以看出,B、C 2種策略均能夠在純電動模式中將發動機轉速維持在600 r/min附近,且可在混動模式下將發動機轉速維持在經濟轉速區間。圖9(b)和圖9(c)表明在3種不同加速工況下C1與輸出軸轉速皆有較好同步效果。圖9(d)和圖9(e)分別為電機MG1與MG2的輸出轉矩,可以看出,當采用策略B時,在1.8 m/s2加速工況下整車由離合器滑摩階段切換至混合動力模式的瞬間為9.6-9.7 s,電機MG1為了跟蹤發動機的目標轉速,產生較大的突變轉矩,而采用策略C時,MG1輸出轉矩更加平緩,2種策略下的MG2輸出轉矩均比較平緩。

圖9 動力源轉矩和轉速
4 硬件在環測試
通過硬件在環(hardware in the loop,HIL)測試進一步驗證本文所提出的控制策略的性能,HIL測試原理如圖10所示。HIL測試臺主要包含上位機和HCU-HIL機柜,其中機柜主要由快速成型控制器(D2P)、包含各種板卡的NI實時仿真機、信號調理模塊、總開關以及可編程電源等部件組成。控制器模型在Motohawk平臺進行搭建,并利用Mototune下載至D2P控制器中,被控對象模型編譯為dll文件并添加至NI Veristand中,同時添加實時目標機使得上位機IP地址與實時仿真機在同一子網段內,通過數據庫CAN接口文件(DBC)進行軟硬件I/O口映射,連接控制器與被控對象的輸入、輸出信號,根據以太網進行通信,實現控制器與被控對象之間的閉環連接,通過Veristand在線顯示仿真結果[21]。最后,運行HCU-HIL機柜的總開關,實現NI實時模擬器底層數據到控制器的傳輸,HIL測試的模型參數與仿真保持一致。

圖10 HIL測試原理圖
圖11為本文設計的動態協調策略的仿真與HIL測試結果對比。圖11(a)~圖11(e)分別為發動機、電機MG1和MG2的轉速、轉矩和沖擊度信號,由于HIL測試的硬件配置問題以及信號經過傳輸時存在誤差,而且Motohawk平臺中積分與微分模塊計算能力相對仿真軟件存在誤差,HIL測試的整個切換過程相對實際仿真更快,關鍵零部件轉速以及轉矩也存在不同程度上的頻繁波動,但其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測試結果依舊在可接受范圍內。從沖擊度角度來看,不同加速工況下的最大模式切換沖擊度為9.34 m/s3,仍小于德國標準(10 m/s3)。因此,HIL測試結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動態協調策略不僅能夠滿足模式切換控制需求,提高模式切換品質,還具有較好的工況適應性。

圖11 仿真與HIL測試結果
5 結論
(1)針對一款集成多離合器的功率分流式HEV,根據杠桿法和矩陣法建立了涉及雙離合器協同的純電動模式切換至混合動力模式的切換階段動力學模型,確定了模式切換序列和切換邏輯,制定了不同切換階段各動力源和離合器動態協調控制策略。
(2)針對雙離合器協調滑摩的切換階段,基于模擬退火算法優化了考慮模式切換沖擊度、滑摩功和切換時間的離合器滑摩行為,并設計了混合動力模式下適應不同需求轉矩的發動機轉速自適應調節策略,通過自適應動態調節電機MG1轉矩提高大范圍工況模式切換平順性。
(3)在仿真分析的基礎上,搭建了HIL測試平臺,進行了所提出策略的試驗驗證,結果表明,發動機轉速、輸出軸端轉速以及行星架C1轉速均能夠滿足切換控制需求,而且不同加速工況下沖擊度的絕對值都能夠控制在10 m/s3下,能夠提高大范圍加速工況的整車行駛平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