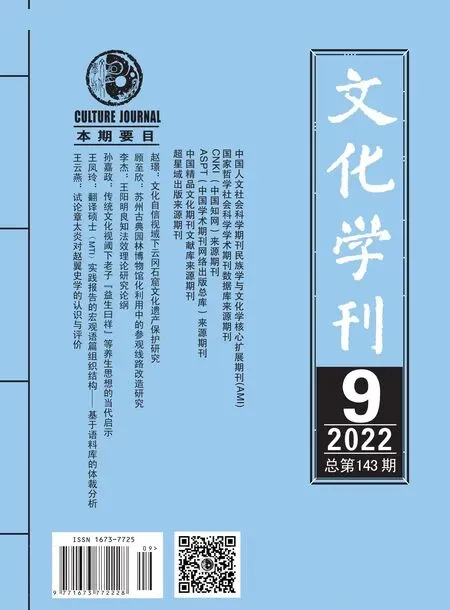熵理論視角下的耕讀文化傳承與發展
陳冬梅
一、研究背景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以被認識的。熵理論揭示了自然界運動的根本奧秘,其理論發展涉及了物理學、地理學、信息學、生物學等領域,其原理同樣適用于社會科學領域,為揭示社會科學發展變化最基本的規律提供了參照。我國自古就是農業大國,耕讀文化歷史悠久,底蘊深厚,耕讀不僅澆筑了中華文明的底色,更涵養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源泉。近年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中對鄉村文化振興的需要以及全社會的勞動教育的關注,耕讀文化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其傳承與發展正向著縱深方向發展。但耕讀文化不能只是我們的“不動產”,在歷史的變遷和發展中,耕讀文化既要在堅守自身存續范本中傳承,又要在時代變遷的調試中創新[1]。而耕讀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是一個含有經濟、文化、制度、科技等多個子因素組成的復合系統,通過各子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使其形成了一個開放的有機的整體。作為一個開放系統,耕讀文化在其產生、發展和變化過程中,始終不斷地與外界環境交換能量、信息,在這個過程中進行著熵增與熵減。故通過熵理論的視角,立足新時代,研究耕讀文化系統的非平衡態勢的運動,從中探究耕讀文化系統優化升級的邏輯和規律,有利于提高耕讀文化傳承和發展的自覺性和能動性。
二、耕讀文化之“熵”
(一)熵與負熵
“熵”概念是德國的物理學家克勞修斯于1864年在《熱之唯動說》一書中提出的,它是用來度量一個系統的混亂程度的量度[2]。熵理論表明,封閉系統的能量只能沿著一個方向轉換,即從有序到無序,從有效到無效,從有使用價值到無價值,簡而言之,熵是不能再被轉化為有用功并不斷增加的能量,是混亂和無序的度量,熵值越大,混亂無序的程度越大,直到限度地無序和混亂。
“負熵”的概念是由諾貝爾獎獲得者,量子力學理論的創始人之一薛定諤于1944年在《生命是什么》一書中最先提出的。他提出的負熵是指熵的變化量是負的,這個負熵變化量平息了系統的熵增從而使系統朝有序化變化發展[3]。所以,在自然狀態下,一個生命有機體的正熵總是在不斷地增加,并且趨向于熵最大的狀態,也就是死亡;而要克服這種趨勢即擺脫死求生存,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從環境里汲取負熵來抵消機體內正熵的增加,由于系統不斷地從環境中獲取物質和能量,這個系統的負熵在增加,于是系統的有序的增量大于無序的增量,系統就形成了新的結構和新的組織,實現了進化和發展。
總之,“熵”是系統混亂度的量度,“負熵”是系統有序性的量度。“熵”理論在宇宙具有普遍指導意義,要維持系統的穩定性,就需要有一定的“負熵”。隨著對熵認識的不斷深入,熵理論所啟發的熵思維方式已逐漸被引入多個領域之中,熵理論也適合于傳統文化系統中的耕讀文化系統研究。
(二)耕讀文化的“熵源”
根據熵的思維,可以將對耕讀文化系統產生影響的因子稱為“熵源”“熵源”對耕讀文化系統演化產生積極或消極的作用,“熵源”的來源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從結構上,可以將耕讀文化的“熵源”分為內部熵源和外部熵源,而從“熵源”對系統的影響和作用上看,可以分為熵和負熵,因此,我們對耕讀文化的“熵源”做如下的歸類和分析[4]:
1.內部熵與內部負熵
(1)內部熵是指耕讀文化系統內部產生熵的因素。比如,傳統耕讀生活方式的式微而導致文化載體衰弱、耕讀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對耕讀文化的局限并以此引起的失衡、宗族組織等文化載體的變遷引起的親族圈的社會變遷等。
(2)內部負熵是指耕讀文化系統內部的負熵因素。主要體現在耕讀文化的源遠流長,底蘊深厚,內涵豐富,耕讀文化系統不僅包含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一種情懷、文化和價值追求,已經刻入了中華文化基因。同時耕讀文化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因時而新,從耕以養生、讀以明道,演化為化耕為勞、化讀為育,其內涵和精神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從而也增加了耕讀文化生命力的韌性。
2.外部熵與外部負熵
(1)外部熵是指耕讀文化系統外部產生熵的因素。比如產業結構調整,生活方式變遷,多元文化沖擊,加之城鎮化、現代化、工業化、信息化使得文化趨向統一化,耕讀文化的存續在時間和空間上遭遇壓縮和排擠,加速了耕讀文化系統的熵增。
(2)外部負熵是指耕讀文化系統外部產生負熵的因素。比如,全社會范圍內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的重視,鄉村振興發展戰略對耕讀文化的挖掘,伴隨勞動教育而興起的耕讀文化傳承,以及全民閱讀、鄉村圖書館、鄉村文化館、農耕博物館、耕讀村落古建筑群保護、鄉村文旅文創、信息化時代的耕讀“云”傳播等,為耕讀文化系統注入了持續的負熵。
三、耕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一)重塑耕讀文化的重要性
一方面,要正視耕讀文化系統熵增的客觀實際。雖然耕讀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特色和底色,綿延數千年而不斷,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迅速推進,特別是城市鄉村對立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得知識分子疏離農村,而農村也視知識分子為“異己”,耕讀結合的文化土壤受到了銷蝕[5]。同時,隨著鄉村生產生活基本模式的變遷,農村空殼化、青年外流、親族圈淡薄、人文生態失衡等原因,耕讀文化的發展滯后,面臨諸多的挑戰,減熵勢在必行。另一方面,要重視耕讀文化的“負熵流”價值。“耕以養生、讀以明道”,以耕讀結合為特點,耕讀傳家為核心的耕讀文化在歷史的演變中沉淀了豐富的文化價值和內涵,比如孝悌為本、崇尚道德、天人合一、克勤克儉、自強不息、協和萬邦等[6],已經浸潤成為中華傳統文化基因的底色。挖掘耕讀文化的豐富內涵,立足新的時代背景,發揮耕讀文化的當代價值,有助于提高公民文化素養、弘揚傳統文化精髓、增強文化自信。總之,耕讀文化不只是“傳家寶”,不該是“過去式”,不應是博物館里的“展品”,不能在現代化過程中因熵增而走向文化熱寂,相反,其應該成為傳承傳統文化和構建民族文化自信的“負熵流”。
(二)增加負熵供給,促進耕讀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1.增加內部負熵,提高文化自覺。
從文化邏輯上看,自古以來,中國以農業立國,農耕不僅哺育了中華民族的體魄,更滋養著中華民族的靈魂,耕讀結合既是物質生產的基礎也是精神依托的載體。耕讀文化傳統的產生與存在的本身就表明,那些以此為依托而生存的人們都從中獲得了益處,實現了耕讀傳家[7]。伴隨著農耕時代的遠去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耕讀相兼對于個人的價值日漸式微,但耕讀文化傳統所體現的勤儉自強、務實堅韌、克己自律、親友睦鄰、尊重自然、尊知重學、崇德向善已然內化為我們的共同精神和價值,刻入我們的文化基因中。然而,在歷史長河中,耕讀文化的傳承更多地是在民眾自用自取中實現的,是一種自用而不自知的“自然”傳承,那么,耕讀文化的熵增必然隨著其實踐基礎和精神載體在現代生活發生巨大變遷而加劇,因此,要通過提高文化自覺來增加負熵。要站在弘揚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認同感、培養民族向心力的高度,發揮耕讀文化在弘揚傳統文化、提升民族文化素養、提升文化軟實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及賦能鄉村振興等方面的“蝴蝶效應”。
2.挖掘文化資源和創新文化載體。
從歷史邏輯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每一代人總是生活在特定的時代條件下,根據時代提出的問題,基于時代所提供的認識結構和條件,通過挖掘歷史來塑造現實從而影響未來。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耕讀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從宏觀上看,包括物質、制度和心理三個層面;從微觀看,涉及行為、習慣、風俗、思想、理念、價值、精神等,從個人的安身立命到家國同構的經世濟民[8]。“耕織傳家久,經書濟世長”,在耕讀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的先賢們沉淀下來了豐富的耕讀文化資源,它們成了耕讀文化能夠穿越時空,滋養后人的精神載體。然而,這些載體并不會自發發揮效用,往往容易在文化系統的熵增中走向寂寥。因此,一方面,要提高文化自覺性,深入挖掘耕讀文化資源,保護和傳承給后人,讓后人在探尋先賢的足跡中繼承遺志,在觀瞻遺跡中體會耕讀文化的精華,在實踐中弘揚傳統美德并賡續文明。另一方面,創新文化載體,傳承耕讀文化在現代情境下,并非是要回歸到古人田園牧歌、晴耕雨讀的生活模式,耕讀的空間不拘泥于鄉野,主體也不局限于農人,內容也不拘束于儒家經典或者自身專業[9],而是全社會范圍內的“全民閱讀式”。比如可以依托農村圖書館、農村博物館、農村文化館、耕讀特色民宿、村落古建筑群保護以及以耕讀相關的文旅活動中,通過創新文化載體來實現活化傳承。
3.打造新鄉賢,賡續耕讀文脈
從實踐邏輯看,耕讀文化系統中,耕讀的緊密結合,是耕讀相互影響相互成就的結果。一方面,農耕體驗,可以讓讀書人有機會更真實地了解生活,從而影響到他們的思想和品格;另一方面,讀書人的參與又給農耕生活注入了“靈魂”,農業科技的進步,往往是由耕讀并重的知識分子完成的,比如寫出《齊民要術》的中國古代杰出農學家賈思勰、現代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在古代,耕讀人生的生活軌跡,幼年在鄉耕讀,青年時期到城市從政或經商,年老告老返鄉,榮歸故里,作為德高望重的鄉賢里長,往往是耕讀傳家的文化“代言人”。因此,重塑耕讀文化,需要發揮新時代鄉村賢達的“反哺”功能,鼓勵他們回歸家鄉發展、投身鄉村建設,為塑造良好家風、培育文明鄉風、助推振興鄉村提供人力財力物力的支持。鄉土是一個人情社會,桑梓情懷是重要的情感紐帶,因此,要重視發揮具有新時代特征的新鄉賢的影響力,制定新鄉賢回歸的評選標準和相關政策,激勵從故土走出去的各行各業人才,回饋家鄉當鄉賢,為家鄉發展貢獻智慧、發揮獨特作用。鼓勵鄉賢回歸鄉村建書院、辦學堂、傳文化,留住鄉賢,傳承耕讀傳家文脈,打造耕讀傳家的現代樣板。
4.加強頂層設計,發揮社會效應。
從理論邏輯上看,熵增定律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有生命力的系統,都必須是耗散結構也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只有開放的系統,才能與周圍環境不斷地進行能量轉換,從環境中獲取負熵得以維持系統運作和延續。相反,如果系統是封閉的,短時間內熵增就會達到最大值,使生命迅速崩潰。耕讀文化的燦爛與長壽也與其自身系統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息息相關。因此,要加強頂層設計,在新時代為耕讀文化傳承和發展營造社會環境和開放系統。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及近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重視保護“耕讀文化”的政策導向的基礎上,各級政府要因地制宜,出臺相關政策,為耕讀文化傳承和發展營造政策氛圍,將耕讀文化傳承放在構建學習型、創新型社會建設體系構建的高度,納入新時代勞動教育體系,開辦耕讀特色教育體系,納入新農村公共服務文化體系、融入現代鄉土社會管理秩序、產業結構、生活方式和鄉土文化的構建中[10]。要發揮社會效應,依托城市的力量來弘揚耕讀文化,動員和鼓勵城市各行業的人才到農村的廣闊天地去投資創業、實現價值,創辦耕讀文創園、耕科技館、耕讀學校、耕讀民宿、耕讀驛站等,實現干在耕讀、學在耕讀、游在耕讀、創業在耕讀、養老在耕讀。同時要把控“熵勢”,避免在吸收負熵時而加劇熵增,一方面,要注重打造耕讀文化精品,不能在市場化的運作中走向文化民粹的自由海選,走向商業化、舞臺化、低俗化的傳承;另一方面,要注意保護和開發并舉,要避免因開發造成的人文和自然環境破壞等等。
四、結語
耕讀文化以耕讀結合為起點,在演化過程中不斷地吸收負熵,逐漸生成為耕讀傳家的文化邏輯,從“勤耕立家、苦讀榮身”的耕讀理念,到“耕以養生、讀以明道”的人本精神,它以豐厚的底蘊滋養著中華文明。但在耕讀文化沉淀的同時,其熵增也在積累,當吸收的負熵大于系統內的增熵時,則耕讀文化興;當吸收的負熵小于系統內的增熵時,則走向衰落。重塑耕讀文化,要努力將負熵最大化,積極構建耕讀文化系統的耗散結構,增強文化自覺和自信,挖掘文化資源和創新文化載體,豐富耕讀文化在新時代的內涵,探索耕讀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路徑,促進耕讀文化在新時代背景下的活態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