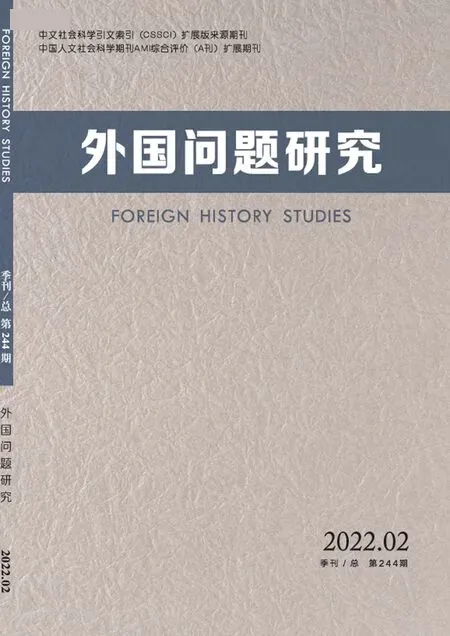羅馬帝國晚期異教內部的衰弱
——以神廟和獻祭儀式為中心
焦漢豐
(復旦大學 歷史系,上海 200433)
長期以來,西方古典學界認為希臘羅馬傳統宗教的衰弱是基督教壓迫的結果,對此,彼得·布朗曾總結了“異教終結”的傳統觀點:“從愛德華·吉本到布克哈特再到現代的歷史學家,在大多數學者的歷史敘事中,一旦遭遇到基督教態度堅決的壓迫,異教的終結似乎是不可避免的。”(1)Peter Brown, “Christianization and Religious Conflict,”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XIII: The Late Empire, AD 337-4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33.德國學者弗里德里希·戴希曼(Friedrich Deichmann)和英國學者加斯·佛登(Garth Fowden)認為羅馬帝國晚期的神廟遭遇了各種形式的暴力,它們的衰弱主要源于帝國當局的反異教法令和基督教系統的破壞運動(2)Friedrich Deichmann, “Frühchristliche Kirchen in antiken Heiligtümern,” Jahrbuch des (kaiserlich)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 Vol.54, 1939,S.105-136;Garth Fowden, “Bishops and Temples in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A. D. 320-435,”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Vol.29, Issue 1 (April 1978), pp.53-78.
然而近些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從長時段的角度來考察羅馬帝國晚期異教的命運,他們試圖逐步將政府和基督教對異教“壓迫”的實際影響最小化,認為基督教崛起并成為國教后,在皇帝的法令下,異教儀式被禁,神廟遭到的破壞、關閉和轉為教堂其實只是歷史的一部分,這只是異教衰弱的原因之一。其實異教早在基督教崛起之前已經出現衰退的跡象(3)部分研究見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Leiden · Boston:Brill, 2011; 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hoenix, Vol.49, No.4, 1995, pp.331-356; Christophe J. Goddard, “The Evolution of Pagan Sanctuaries in Late Antique Italy (Fourth to Sixth Century A.D.): A New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Framework, A Paradox,” Massimiliano Ghilardi, Christophe J. Goddard, Pierfrancesco Porena, eds., Les cités de l’Italie tardo-antique (IVe-VIe siècle): institutions, économie, société, culture et religion, Roma: école fran?aise de Rome, 2006, pp.281-308.比如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埃及的一些神廟就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問題,一些神廟在羅馬帝國早期就已轉為了世俗之用。(4)Roger Bagnall, Egypt in Late Antiq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60-268.所以我們可以嘗試拓寬研究視野,從當時的時代大背景中出發,考察異教的衰弱進程。本文試圖結合文獻和考古證據,從神廟和獻祭儀式的視角來考察異教的衰弱進程。總的來說,當時異教自身的衰弱體現在兩方面,其一,神廟修建活動的衰退,二是異教獻祭儀式的衰弱,其中神廟建設活動的衰退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新建神廟數量的下降,第二個是新建神廟規模的縮小。
一、神廟修建活動的衰退
從公元3世紀開始,羅馬帝國大部分地區修建新神廟的步伐大大放緩,而新建神廟中大部分是皇帝崇拜神廟。3世紀開始非洲的神廟建設就已經出現衰弱跡象,相關銘文顯示,在3世紀末和4世紀初,雖然原來的一些神廟仍舊得到了維護和修葺,但幾乎沒有新建神廟的證據。有記錄的只有兩座,一座是公元283—284年修建的維列昆達(Verecunda)的神圣卡魯斯神廟(Divus Carus),這是獻給卡魯斯的皇帝崇拜神廟,另一座神廟位于提格尼卡(Thignica),修建于四帝共治時期,但無法確定該神廟具體獻給哪位神祇。(5)Gareth Sears, “The Fate of the Temples in North Africa,”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231.小亞地區的神廟建設活動相較前幾個世紀也顯得不值一提,無論是皇帝還是當地精英似乎不再熱衷于為神廟及其相關儀式提供資金。目前已知的神廟中只有米利都的狄俄尼索斯神廟和愛奧尼亞沿海狄迪馬的阿波羅神廟修建于3世紀,當時得到修復的神廟也只有以弗所的阿爾忒彌斯神廟。(6)Peter Talloen and Lies Vercauteren, “The Fate of the Temples in Late Antique Anatolia,”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p.347-387.
同一時期羅馬城的新建神廟也是屈指可數,雖然原有的舊神廟繼續得到了維護,但根據文獻記載,整個3世紀羅馬城新建的神廟只有微不足道的3座。塞維魯·亞歷山大(Severus Alexander)時期的羅馬城新建了2座神廟,分別是朱庇特·瑞度克斯(Iubbiter Redux)神廟和蘇利亞女神(Dea Suria)(7)這里的蘇利亞(Dea Suria)似乎是一位凱爾特女神,但是敘利亞女神(Dea Syria,即阿塔加提斯[Atargatis])有時也作Dea Suria,而考慮到賽維魯·亞歷山大和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一樣的敘利亞出身,因此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廟,原來的復仇者朱庇特神廟(Iubbiter Ultor)和平原伊西斯神廟(Isis Campensis)也得到了修復。(8)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56.奧勒里安(Aurelianus)也修建了一座新神廟。他在擊敗芝諾比婭后收復了帕爾米拉,公元273年,勝利歸來的他在羅馬興建了一座神廟獻給無敵太陽神(Sol Invictus)。(9)Zosimus, New History, 1.61.4世紀羅馬城的新神廟可能也寥寥無幾,有記錄的只有一座。4世紀初,馬克森提烏斯將他夭折的兒子封神,并于公元309年在神圣大道(Via Sacra)之旁為其修建了神圣羅慕路斯(Divus Romulus)神廟。(10)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458.
可見公元3—4世紀羅馬帝國的新建神廟數量寥寥可數。學者們對其原因有著不同的解釋,傳統異教的逐步衰弱是其一。“整個世界似乎都在等待著基督教的到來。”薩奧爾這樣說道,他認為神廟這方面的變化反映了羅馬帝國公共工程模式的變化,當時新建公共建筑數量的下降是一種普遍趨勢。不過從比例上來說,神廟建設活動的衰退程度顯然要比新建公共建筑數量的總體下降趨勢更為嚴重。(11)Eberhard Sauer, The Archaeology of Religious Hatred in the Roman and Early Medieval World, Stroud & Charleston (SC): Tempus, 2003, pp.114-130.北非地區銘文所提供的證據為我們充分展現了這一情況,當時涉及公共工程的銘文數量相較于前兩個世紀呈下降趨勢,而在所有建筑活動的銘文中,涉及神廟的銘文所占比例明顯下降了。(12)Gareth Sears, “The Fate of the Temples in North Africa,” p.237.希臘和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也有著相似的趨勢,(13)Luke Lavan, “Political Talismans? Residual ‘Pagan’ Statues in Late Antique Public Space,”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p.439-478.因此當時各個地區的神廟建設都存在著衰退的情況,當然這并不能說明異教本身無可挽回地衰弱了。
四帝共治時期公共工程的優先順序更能說明神廟的處境。戴克里先力圖恢復帝國的榮光,他自詡為朱比特,馬克西米安則自稱為赫拉克勒斯,但在他們治下,帝國各大城市并沒有為這兩位神靈修建宏偉的神廟,戴克里先只是在各地的行宮中修建了小型的神廟。按照約翰·馬拉拉斯的記載,馬克西米安在與波斯作戰時,戴克里先則駐守在安條克,他在城市里修建了一座行宮,在城市近郊的達芙妮(14)這里的達芙妮是地名,位于安條克近郊,是阿波羅和達芙妮崇拜的圣地。則修建了一座體育場,并在其內部修建了一座奧林匹亞宙斯神廟和一座尼米西斯宙斯神廟(Temple of Nemesis Zeus),另外還修建了一座赫卡特的地下神廟。這些神廟規模都比較小,只是附屬性質的建筑,馬拉拉斯在敘述戴克里先的行宮時才順便提及。(15)Malalas, Chronicle, 12.38.
這一時期帝國公共工程的重點在其他建筑上,四帝共治時期皇帝們選擇優先在大城市里修建規模宏大的公共浴場。羅馬、米蘭、尼科米底亞和安條克在這一時期都興建了新的大型公共浴場,(16)約翰·馬拉拉斯在他的《編年史》中提到了戴克里先在安條克修建的浴場,詳見John Malalas, Chronicle, 12.38;利巴尼烏斯提到了尼科米底亞的浴場,詳見Libanius, Oration, 61.16-61.18.羅馬的戴克里先大浴場是其中規模最大的,占地面積12萬平方米,中央大廳的面積達到了280米×160米,超過了賽維魯王朝時期的卡拉卡拉大浴場。可見雖然戴克里先自詡為帝國的拯救者,力圖恢復羅馬帝國和異教諸神往日的榮光,但他對修建新神廟的熱情并不高。(17)Roger Rees, Diocletian and the Tetrarc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7-71.
公元3—4世紀的異教皇帝似乎都對興建新神廟失去了興趣,甚至后來力圖振興和改革異教的背教者尤利安也是如此,這是值得深思的現象。尤利安發布法令逐步將基督徒從政府和教師隊伍中清除出去,還打算模仿基督教會,為異教建立一個具有相似等級制度的“教會”,但他的關注點并不是神廟。雖然他重新開放了一些被基督徒皇帝勒令關閉的神廟,但并沒有修建新神廟。按照利巴尼烏斯的說法,尤利安只在自己的宮殿中修建了小型神廟,“因為皇帝他不可能每天離開皇宮前往神廟,而與諸神的持續交流又是極其重要的事情,人們在皇宮的中心為他這位統治者興建了一座神廟……”(18)Libanius, Oration, 18.126-127.
尤利安時期新建神廟的缺乏也許與他在位不到兩年多少有些關系,畢竟神廟作為大型工程營建周期較長,兩年不到的時間不足以讓他的宗教政策在神廟建設上出現成果,但是時間短不足以完全解釋這一現象。他振興異教的重心在于宗教沖突嚴重的東部地區,特別是小亞、希臘和敘利亞地區,因此東部地區缺乏新建神廟的情況還是很能說明問題。另外,尤利安時期其實有不少新建的公共建筑。(19)尤利安時期部分工程見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457.尤利安還打算重建耶路撒冷的猶太圣殿,最后因為突然出現的大火不了了之。(20)圣殿地基附近持續噴出火球,因此重建工作無法繼續進行,詳見Ammianus, Res Gestae, 23.1.3.他同樣修復了羅馬元老院的勝利女神祭壇,并將其重新安置到了元老院,(21)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457.但是他似乎對修建新神廟缺乏熱情。
總之,從3世紀開始,原先由神廟主導的古典城市布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共和國末期和帝國早期的神廟將城市中心位置讓于廣場和大型會堂等政治建筑,到了帝國中晚期則讓位于皇宮和公共浴場。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亞的宏偉皇宮以及達爾馬提亞行省的龐大行宮體現了這種轉變,后者位于薩羅納(Salona)附近,是戴克里先退位后的居所。考古學證據顯示從公元4世紀70年代開始,城市的神廟和廣場都已經喪失了其原來的中心地位,在很多城市中,大型浴場似乎成了城市生活的中心。(22)根據理查德森所列舉的羅馬城的公共建筑,可以發現在公元3—4世紀的公共工程中,浴場占了較高的比例,詳見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p.456-458.相關文獻也證實了羅馬帝國中晚期公共浴場在城市中的重要性。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us)喜歡住在公共浴場建筑群中。(23)轉引自Anna Leone, The End of the Pagan City: Religion, Economy, and Urbanism i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2.公共浴場也經常是舉行正式會議的場所,公元411年,北非的多納圖派和羅馬公教就在迦太基的伽爾基利阿納(Thermae Gargilianae)浴場舉行了宗教會議。愈來愈多的浴場成了城市的中心,也取代廣場成了陳列雕像的重要場所。在北非提姆加德城的浴場遺址中,考古學家在一系列雕像的基座上發現了當時獻給瓦勒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父子的銘文。(24)Anna Leone, The End of the Pagan City: Religion, Economy, and Urbanism i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p.22.君士坦丁堡的宙克西帕斯浴場(Zeuxippus)也陳列著從各處收集而來的大量雕像。因此,羅馬帝國城市公共空間發生了變化,帝國晚期公共浴場突出的地位也許與神廟修建活動的衰退存在著密切的聯系。
第二個衰弱的表現是神廟規模的縮小。從3世紀開始,不僅是新建神廟的數量大幅下降,而且相較于以前規模宏偉的希臘羅馬神廟,當時神廟的規模明顯縮水了。肯特大學的考古工作者在2009—2010年對羅馬奧斯提亞港進行了挖掘,發現了一座帝國晚期的小型神廟。該神廟建于帝國早期一座蓄水池之上,只有3.6×3.8平方米的面積。(25)詳細情況參閱此次考古發掘工作的官方網站https://lateantiqueostia.wordpress.com/。希臘地區也有相似的趨勢,阿哥斯廣場上的一座小型神廟也只有4.2×1.8平方米的面積。(26)Helen Saradi-Mendelovici, “Late Paganism and Christianisation in Greece,”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pp.263-310.4世紀的昔蘭尼(Cyrene)也是如此,當地的豎琴演奏者阿波羅神廟(Apollo the Cithara Player)面積只有5×5平方米,公元365年大地震以后新落成的奧姆布里俄斯宙斯神廟(Temple of Zeus Ombrios)的面積也只有5×7平方米。(27)Gareth Sears, “The Fate of the Temples in North Africa,” p.237.
那些只出現在文獻中的神廟也是如此,比如前文戴克里先修建的神廟,他下令在安條克的達芙妮體育場內修建了一座尼米西斯宙斯神廟和奧林匹亞宙斯神廟,這些神廟的結構也可能相對簡單,所以能夠融入體育場的整體建筑之中。(28)詳見John Malalas, Chronicle, 12.38.尤利安皇帝也只在自己的皇宮內修建了小型神廟。(29)Libanius, Oration, 18.126-127.君士坦丁大帝在君士坦丁堡總共修建了三座神廟,其中兩座是堤喀(Tyche)神廟和瑞亞(Rhea)神廟,(30)Zosimus, New History, 2.31.3.但這兩座神廟都位于一座庭院之內,因此面積不會很大。第三座神廟是卡皮托利神廟(Capitolium),從神廟的考古報告來看該神廟似乎是供奉君士坦丁王朝皇帝雕像的神龕,具體規模目前無從得知。(31)Luke Lavan, “Political Talismans? Residual ‘Pagan’ Statues in Late Antique Public Space,” p.451.此外,還有位于希斯佩魯姆(Hispellum)的君士坦丁王朝的皇帝崇拜神廟,目前還無法確定其規模。根據這一時期用來容納皇帝雕像的神龕大小來推算,該神廟應該只是小型神廟。(32)Luke Lavan, “Political Talismans? Residual ‘Pagan’ Statues in Late Antique Public Space,” p.463.
二、血祭傳統的衰弱
除了神廟修建活動的停滯外,羅馬帝國傳統的異教獻祭儀式也逐漸衰弱了。尤利安個人已經體驗到了這一時期羅馬帝國異教自身的變化,有一個例子能生動地說明當時傳統的獻祭儀式所經歷的變化。尤利安在安條克時準備向阿波羅進行獻祭,但是神廟祭司并沒有按傳統提供牛羊等大型牲畜作為祭品,僅僅奉獻了一只鵝。尤利安對此有著詳細的描述:
……但是當我進入神廟,我看不到貢香,沒有蛋糕,更沒有獻祭之用的動物。我愣了一會兒,還以為自己仍在神廟之外,以為你為了向我這個大祭司表示敬意,所以你還在等待我的信號。但是當我開始詢問,為了榮耀阿波羅,城市打算在一年一度的節日上獻祭什么動物,祭司這樣回答道:“我從家里帶了一只鵝過來作為獻給神的貢品,但是城市這次沒有做什么準備。”(33)Julian, Misopogon, 361d-362b.
可見當時就連安條克的異教民眾也不認可這種血腥的儀式,在尤利安宗教政策重點針對的東部地區,民眾對血祭的反應普遍比較冷淡,這其中包括小亞、敘利亞和希臘。(34)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41-347.而在過往,傳統上公開的獻祭儀式比較隆重,祭司會精心挑選大型牲畜作為祭品,并提前幾個月做好準備。(35)Alan Cameron, The Last Pagans of Rome, p.66.尤利安在安條克所遇到的情況也許反映了血祭的民眾基礎已然不再,就連尤利安原本的支持者阿米阿努斯·馬賽林努斯也因此批判了他,馬賽林努斯在書中表達了自己對奢侈的血祭儀式的厭惡:
他用了過多祭品的血去浸濕祭壇,有時候一次性要獻祭上百頭公牛,以及無數的其他動物,還有在陸上和海里被獵殺的白鳥,以至于幾乎每天他的士兵都在貪婪地吃著大量的肉……(36)Ammianus, Res Gestae, 22.12.6.
利巴尼烏斯的演說中也體現了類似觀念,他認為尤利安每天進行的獻祭儀式不符合傳統,明顯過于奢侈了。(37)Libanius, Oration, 12.80.卡梅隆的《羅馬最后的異教徒》涉及了帝國晚期獻祭儀式的衰弱。卡梅隆認為一些異教儀式,比如曾經占主導的公共獻祭儀式,在被政府禁止之前就已經衰弱了,這是異教自身演變的結果:
在完全缺少證據的情況下,沒有什么能得到證實,但我懷疑在4世紀80年代(也許更早),西部和東部的公共儀式就已經不包含常規的動物祭品了……(38)Alan Cameron, The Last Pagans of Rome, p.67.
古代世界公開的獻祭活動曾是各類崇拜的標志性儀式,但是這一儀式逐漸衰弱了。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之前,異教內部就已經出現了反對這種血腥儀式的聲音,他們追求更高級的、純潔的、精神性質的儀式。一些新柏拉圖主義者對宗教儀式有新的觀點,波菲利(Porphyry)就質疑了傳統獻祭儀式,他認為獻祭是一種低級的儀式。波菲利厭惡血祭以及隨后進行的無節制的宴會,他提倡崇拜的智力性和精神性,強調用精神的方式去榮耀和崇拜神靈,認為最高神靈理應得到信徒精神上的祭品。他甚至還聲稱遠離肉食才能保持靈魂的純潔性。(39)轉引自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2-333.一些新畢達哥拉斯主義者也持有類似的觀念,他們同樣認為血腥的動物獻祭是最低級的崇拜方式,只是用來撫慰惡魔的低級儀式,因此應該盡量避免執行這類儀式。提阿納的波羅尼烏斯(Apollonius of Tyana)在實踐中就只進行無血的宗教儀式,他甚至拒絕出現在獻祭現場,并批評了雅典人對獻祭的喜愛。(40)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6.這一點與基督教類似,基督徒厭惡異教的獻祭儀式,強調信仰的個人性和精神性,這可能也對當時的異教知識分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公元3世紀以來,異教儀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動物獻祭不再是最主要的儀式,而焚香、點亮油燈和吟誦贊美詩等私下的崇拜行為在異教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突出。(41)Martin P.Nilsson, “Pagan Divine Service in Late Antiquity,”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Vol.38, No.1 (Jan.1945), pp.63-69.考古發現和銘文都證明了當時油燈在祈愿中的重要性,(42)詳見Richard Rothaus, Corinth, the First City of Greece: An Urban History of Late Antique Cult and Relig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pp.32-63; 126-134.焚香也比以前更為流行,這些來自東方的異國情調的芳香更能凸顯儀式的莊嚴性,在成本上也要比奢侈浪費的動物獻祭要低,是比較受人推崇的精神化崇拜儀式。而歌頌神靈的贊美詩也是很好的精神獻祭,愛奧尼亞沿海狄迪馬和克拉羅斯(Claros)的銘文證實了當時流行神靈贊美詩。狄迪馬的一份阿波羅神諭中,阿波羅自己也表達了對贊美詩的喜愛。(43)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1-356.最重要的是,這些崇拜活動并不局限于神廟和神龕等崇拜中心,人們在私下也能通過這些方式表達自己對神的崇敬。
尤利安皇帝則受揚布利庫斯(Iamblichus)和撒魯斯提烏斯(Sallustius)等哲學家的影響,(44)詳見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8-339.依然十分重視傳統的獻祭儀式。對于血祭傳統的逐漸衰弱,尤利安曾無可奈何地感嘆道:“告訴我,卡帕多西亞還有哪些是真正的希臘人?據知,有些人拒絕獻祭,另一些人盡管愿意,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去獻祭。”(45)Julian, Epistula, 78.利巴尼烏斯也抱怨安條克的異教民眾都把錢都花在了城市的賽馬表演而非阿波羅的節日慶典上。(46)Libanius, Oration, 15.19.這些情況真實反映了傳統的異教儀式正在經歷的變化,也許與神廟的衰弱有著密切的關系。最遲從3世紀開始,傳統異教的獻祭儀式的確逐漸衰弱了。對于其中的原因,布拉德伯里指出這更多是源于祭司威望的下降和羅馬城市中傳統 “公益捐助(Euergetism)”(47)euergetism中文譯名,詳見劉津渝:《羅馬史研究入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序言第5頁。模式的變化,這一變化進一步推動了原本就已經出現的異教儀式上的變化,讓獻祭的衰弱成為現實。總的來說,神廟原先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市政府的宗教資金、公共資金和市民捐助,傳統節日中的大多數獻祭儀式由公共資金提供支持,(48)A. H. M. Jones,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227-235.但宗教資金只限于包括神廟修建和維護等特定支出,公共資金又不足以應付龐大的獻祭儀式和宗教游行等費用。因此富裕市民的捐助就成了城市宗教生活資金的重要來源,這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祭司階層自身來承擔,祭司職位因此是由那些富裕市民來擔當,他們在承擔財政義務的同時也享有部分特權。但3世紀危機無論對城市經濟還是上層市民都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相關儀式因此也失去了原來的經濟支柱,資金上的縮水導致異教儀式和節日在規模和數量上都有所減少,奢侈的獻祭儀式因此衰弱了,而更迎合帝國政府的皇帝崇拜以及更受普通民眾喜好的節日戲劇和賽馬表演得以保留,這些活動比傳統的獻祭更具吸引力,民眾生活也因此逐步世俗化了。
三、異教自身衰弱論
綜上所述,可見異教自身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傳統的血祭儀式衰弱了,異教徒的崇拜活動也轉移到了宗教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焚香、吟誦贊美詩和點燈祈愿等活動。(49)Scott Bradbury, “Julian’s Pagan Revival and the Decline of Blood Sacrifice,” pp.334-337.根據阿爾勒的愷撒略烏斯(Caesarius of Arles)的記述,異教徒會在草地上向神祇獻上些物品,或者在水池旁點亮陶制油燈,或是向泉水投擲硬幣抑或是為某棵圣樹系上絲帶,斯巴達和科林斯當地的一些圣地就出土了信徒留下的大量陶制油燈。(50)Béatrice Caseau, “Late Antique Paganism: Adaptation under Duress,”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130.雖然這些活動后來也被法令所禁止,(51)Codex Theodosianus, 16.10.12.但是法令在現實中的執行力度又是另一回事了,這類私下的供奉和崇拜活動通常很難得到有效的監督和控制,因此無法從根本上被禁止。
城市神廟和公共獻祭儀式緩慢衰弱的現象有跡可循,特別是西部的少數城市為我們提供了相關證據,西部地區神廟被破壞的現象較少,神廟保存率相對較高。雖然帝國政府的法令要求關閉所有神廟,但是考古證據顯示一些城市神廟在公元4世紀末仍然在正常運作。羅馬大競技場南部的花神弗洛拉(Flora)神廟在公元400年左右得到了修復,而每年4月花神節(Floralia)上圍繞神廟的慶典活動仍在繼續。(52)Michael Mulryan, “The Temple of Flora or Venus by the Circus Maximus and the New Christian Topography: The ‘Pagan Revival’ in Action?” Luke Lavan and Michael Mulryan, eds., The Archaeology of Late Antique ‘Paganism’, pp.209-228.位于奧斯提亞的大母神神廟狀況也較好,附近兩座修建于公元4世紀的新廣場并未占用其領地。(53)Luke Lavan, “Public Space in Late Antique Ostia: Excavation and Survey in 2008—2011,”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116, No.4, 2012, pp.649-691.甚至到了5—6世紀也是如此,著名的朱比特·卡皮托利努斯神廟在東哥特的狄奧多里克時期得到了修復,維斯塔神廟于5世紀初得到了修復,羅馬廣場的農神廟也差不多是同一時間得到修復,元老院外的密涅瓦雕像則在公元472/473年得到了修復。(54)詳見Christophe J. Goddard, “The Evolution of Pagan Sanctuaries in Late Antique Italy (Fourth-Sixth Centuries A.D.): A New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Framework, A Paradox,” pp.303-304; Lawrence Richardson,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pp.457-458.而且這一時期鄉村神廟仍然十分活躍,它們和西部的城市神廟是差不多的處境,很少遭到人們的暴力破壞。可見部分地區神廟的衰弱是沒有暴力的過程,特別是羅馬城所在的意大利本土地區。(55)Michael Mulryan, “The Temple of Flora or Venus by the Circus Maximus and the New Christian Topography: The ‘Pagan Revival’ in Action?” pp.209-228.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有了這樣的結論,從公元3世紀開始,似乎是異教自身儀式上的變化導致了神廟的衰弱,而非基督教和帝國政府的壓迫性政策。
這種異教自身“衰弱”的理論也許還不夠成熟,我們目前無法明確神廟的衰弱與異教儀式變化之間的具體關系,但是這一說法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這種“翻案”也存在著先例,這里可以回顧一下學術界古代晚期猶太人的研究情況,學者們的成果已經讓我們對這一時期猶太人狀況的認識大大改觀。猶太人曾在羅馬帝國內飽受歧視,以前的學者大都認為公元5—6世紀的猶太人大多處于貧窮之中,社會地位低下,因此沒有能力在公共生活和建筑中展現自己的存在。但考古證據卻否定了這一論點。地中海東岸當地猶太人的建筑顯示了當時存在一個富裕的猶太社區。小亞阿佛洛狄西亞斯(Aphrodisias)的銘文顯示猶太人在當地劇場擁有較好的固定位置,他們在推羅的競技場也享有同樣的待遇。薩迪斯的一座猶太會堂的面積達到了80米×20米,可容納1500人集會,規模要明顯大于當地的教堂。(56)Peter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Chichester, West Sussex;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3, p.63.可見古代晚期的猶太人享有一定的宗教自由,猶太教是一種合法的宗教(religio licita)。
近幾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已經證明了戴希曼和佛登等學者異教終結和神廟轉變理論的局限性。他們的研究也許適用于中東地區,但羅馬帝國的其他地區并非如此。教會對待傳統宗教的立場并不總是打壓,雙方還有共存和交流,很多古代神廟因其出眾的藝術價值而被保留下來。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當時異教和基督教之間的沖突也是確實存在的,但問題在于沖突是否對當時的宗教和社會變化有根本的影響,在彼得·布朗看來,這些宗教沖突的影響相對于當時龐大的日常社會生活而言就顯得無足輕重了,“羅馬帝國社會的活力、公共生活的節奏、向所有階層都敞開的公民游戲,以及上層社會所共享的文化,這些都讓基督教和異教的區別無足輕重”。(57)Peter Brown, “Pagans and Christians at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1958,” Peter Brown and Rita Lizzi Testa, eds.,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Breaking of a Dialogue (IVth-VIth Century A.D), Zurich/Berlin: LIT Verlag, 2008, pp.21-22.宗教對于古代民眾來說是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但并非僅有的內容。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是一個宗教和文化多元的社會,并非充斥著宗教暴力,以前基督教作家給讀者留下了這種負面印象。當時異教的消亡以及基督教的擴張并不迅速,而是經歷了一個長期且緩慢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利用各種史料來重新研究古代晚期的宗教變化,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考古證據,異教自身“衰弱”的理論也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