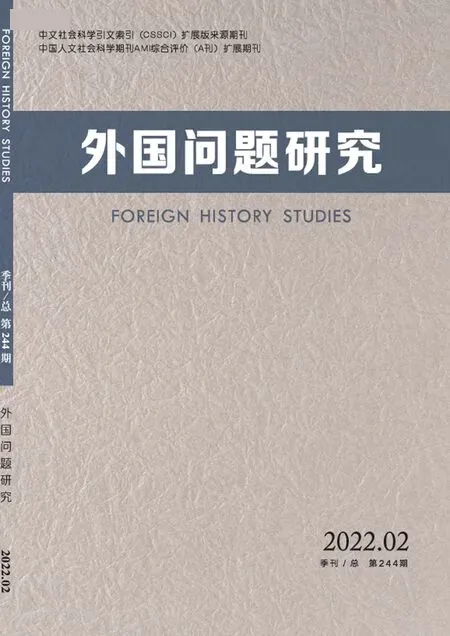1971年澳工黨代表團訪華與澳中民間交往
謝曉嘯
(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
1972年12月,由澳大利亞政治家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領導的澳大利亞工黨在國內大選中擊敗了自由黨和鄉村黨聯盟(Liberal-Country Coalition),在一舉終結后者長達23年之久的執政紀錄的同時,也宣告了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即將改轅易轍。此前,由于澳自由黨和鄉村黨聯盟政府始終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對華采取敵視和戒備的態度,中澳兩國遲遲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惠特拉姆在就任總理當天即宣布他已要求澳駐法大使阿蘭·雷諾夫(Alan Renouf)與中方聯系以便雙方就建交事宜展開談判,同年12月21日中澳正式建立外交關系。(1)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392—393頁;Gough Whitlam, “Sino-Austral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972—2002,”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6, No.3, 2002, p.330.
澳中關系之所以能夠在工黨政府上臺后迅速實現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惠特拉姆在前一年率領工黨代表團訪華時就已經與中方圍繞相關問題達成了初步的共識。(2)在與中方舉行會談的過程中,惠特拉姆曾向周恩來總理坦言,如果由他率領的工黨在次年的大選中獲得勝利,新政府將立即尋求與中國建交。參見“Transcript of Discussions between Gough Whitlam and Zhou Enlai, 5 July 1971,” the Whitlam Institute, ed., For the Record: Gough Whitlam’s Mission to China 1971, Rydalmere, NSW: Whitlam Institute within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2014, p.25.對于這一澳中關系的“破冰之旅”的前因后果,許多專家已有申論。國內學者中,汪詩明和張秋生曾分別撰文從不同角度對當時澳大利亞國內兩大政黨自由黨和工黨在對華政策上的不同之處做過剖析,并在此基礎上闡明了惠特拉姆此次中國之行的重要歷史意義。(3)汪詩明:《論澳中關系正常化》,《世界歷史》2003年第2期;張秋生:《試論澳中建交及其對澳亞關系的影響》,《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放眼國際學界,除了眾多以澳中關系為研究對象的論著之外,還有兩名學者,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 和比利·格里菲斯(Billy Griffiths)曾相繼以專著的形式對這一事件的緣起及其深遠影響進行過細致的歷史學考察。(4)參見Stephen FitzGerald, Talking with China: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Visit and Peking’s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2;Billy Griffiths, The China Breakthrough: Whitlam in the Middle Kingdom, 1971, Clayton,Victoria: Monash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12.
然而,無論是以澳中關系為研究對象的分析性論著或是圍繞工黨這次出訪展開的歷史性敘事,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兩國之間延續多年的民間交往為惠特拉姆等人此次訪華之旅的成功創造的有利條件。事實上,在惠特拉姆以反對黨領袖的身份到訪中國之前,早已有數以百計的澳大利亞民間人士曾經來華訪問。在這些澳中民間交流的先行者之中,有許多是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工會人士和議會議員,也正是通過他們在返澳后的積極宣傳和“牽線搭橋”,才為澳中兩國在缺乏穩定的官方溝通渠道的情況下,提供了一個相互了解和接觸的機會,并由此在“潤物細無聲”之間為1971年工黨代表團的歷史性訪問鋪平了道路。(5)關于中澳建交前雙方的民間往來,參見拙作《中澳建交之前兩國民間往來初析——以1949—1965年間來滬的澳方人士為例》,《史林》2021年第3期。
值得一提的是,縱觀新中國成立之后與西方各大主要國家的建交過程,“民間”因素無不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朝鮮戰爭結束之后,以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為代表的西歐各國都相繼廢除了名為“中國差別”(China Differential)的對華貿易禁運政策,同時開始積極重建對華民間貿易和人文交流的渠道,這些舉措為上述國家日后與中國建交埋下了伏筆。(6)“中國差別”(China Differential)是朝鮮戰爭爆發后,以美國首的西方國家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China Committee)出臺的對華貿易禁運政策的總稱。參見崔丕:《美國的冷戰戰略與巴黎統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1945—1994》,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291—292頁。關于20世紀50—60年代,英、法、西德、意等西歐國家與中國展開的具有半官方性質的經貿談判和商貿往來,中外學界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參見吳浩、劉艷斐:《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與英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調整(1952—1957)》,《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1期;吳浩、劉艷斐:《1954年日內瓦會議與英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調整》,《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27卷第6期;李華:《新中國與意大利關系正常化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27卷第1期。西方學界的研究成果可參見《現代亞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近期刊發的一期專輯中的相關文章:Carla Meneguzzi Rostagni, “The China Question in Italian Foreign Policy,”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51, No.1 (January 2017), pp.107-132; Angela Romano, “Waiting for De Gaulle: France’s Ten-Year Warm-up to Recogniz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51, No.1 (January 2017), pp.44-77; Giovanni Bernardini, “Principled Pragmatism: The Eastern Committee of German Economy and West German-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1949—1958,”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51, No.1 (January 2017), pp.78-106.相較而言,目前學界對于澳中建交前雙方在民間層面建立的聯系,特別是圍繞這種聯系對兩國關系的影響的探考仍尚付闕如。
作為一項個案研究,本文致力于將1971年澳工黨代表團訪華這一重要事件置于澳中建交之前的民間貿易和人員往來這一更大的歷史脈絡中加以考察,通過聚焦于邁克·楊(Mick Young)和羅斯·特里爾(Ross Terrill)兩人早年的訪華經歷以及他們在1971年惠特拉姆的中國之行中分別扮演的重要角色,深入揭示推動澳中關系走向正常化背后的民間助力因素。
一、工黨訪華提議出臺的背景
1949年12月,由羅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率領的澳自由黨在選舉中擊敗了執政的工黨,由此開啟了一個他本人連續擔任總理長達16年之久的“孟席斯時代”(the Menzies Era)。孟席斯在擔任總理期間,從未真正將與中國建交作為一個近期目標。(7)關于這一時期澳政府的對華政策,參見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5, pp.21-35.此后接替孟席斯擔任澳總理的自由黨領導人在大體上延續了由前者制訂的對華政策基本方針。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同樣反對發展對華民間貿易。
事實上,雖然孟席斯政府并未像上述提到的西歐各國一樣在朝鮮戰爭之后徑直廢除“中國差別”的貿易禁運政策,但其在實際執行該政策的過程中卻體現出一種不同于美國的靈活性。(8)參見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303-307.因此,在經歷了朝鮮戰爭時期的貿易銳減之后,澳對華出口貿易自1956年起就呈現出一種持續增長的趨勢,并最終發展成了一個影響兩國關系的重要因素。在兩國建交之前的23年時間里,特別是在1956年之后,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了大量羊毛、小麥以及相當數量的各類礦石和金屬材料,其中尤以小麥的出口最為重要,甚至一度占據了澳大利亞對華貿易出口總量的60%—80%。(9)參見Yi Wa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Sixty Years of Trade an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13. 關于這一時期澳中貿易的總體情況和相關數據,參見Australia Parliament: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Industry and Trade and Australia, Australia-China trade: report from The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Industry and Trade,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4, pp.35-44.進入60年代之后,隨著澳對華小麥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執政的澳大利亞自由黨—鄉村黨聯盟政府在發展對華貿易上所持的曖昧態度,開始頻繁遭到反對黨工黨的攻訐,同時也引起了美國方面的擔憂。(10)關于工黨在澳對華貿易這一問題上的立場變化,詳見下文。關于60年代初澳對華小麥出口貿易引發的美方不滿,參見Timothy P.Maga, “The Politics of Non‐Recognitio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China, 1961—1963,”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Vol.14, No.27, 1990, pp.10-11.盡管面臨來自國內外各方的壓力,但澳政府仍堅持未對澳中兩國之間的貿易進行干預,而是采取了一種放任自流的做法。對此,A.W.斯塔加特(A.W.Stargardt)指出,這種將政治與經濟區別對待的做法,反映了一種外交政策服務于國內政治需要的特點。具言之,他認為,執政的自由黨和鄉村黨聯盟政府并不希望對澳對華小麥出口橫加干涉,因為這很可能會損害其在鄉村地區的支持率。(11)參見A. W. Stargardt, Australia’s Asian Policies: The History of a Debate, 1839—1972,Hamburg: Institute of Asian Affairs in Hamburg, 1977, pp.229-230.
然而,澳對華小麥出口貿易在經歷了近十年(1960—1970年)的穩定增長之后,卻在1970年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同年,加拿大在與中國建交后不久即宣布同中方簽訂了一筆金額可觀的小麥銷售合同,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前一直負責澳對華小麥銷售業務的澳大利亞小麥局卻遲遲未能與中方續簽合同。(12)參見“Canada to sell more wheat to China,” The Canberra Times, October 29, 1970, p.8. 關于澳小麥局未能與中方續簽小麥銷售合同的情況及其影響,參見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p.105-106.
更為火上澆油的是,當上述消息公之于眾之后,澳政府采取了不甚明智的強硬立場,在被問到是否會為了發展對華小麥貿易而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時,澳大利亞副總理和鄉村黨的領袖道格·安東尼(Doug Anthony)公開表示:“我不會僅僅為了在貿易上獲利,而出賣自己的靈魂。”(13)“Foreign Policies Not Changed for Trade,” The Canberra Times, February 08, 1971, p.7.安東尼的這一聲明自然遭到了中方的抗議,同時也在澳大利亞國內引起了一片嘩然。澳大利亞政府在對華建交問題上擺出的強硬姿態遭到了此時已經轉變了立場的工黨的公開反對,甚至在與自由黨結盟的鄉村黨內都有人希望盡快與中國建交。(14)參見E. 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Clayton,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8-199.澳小麥種植業主作為對華小麥出口貿易的直接受益者,更是在中國與加拿大建交之前,就已經表態希望澳政府能夠盡快同中國改善關系。(15)參見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102.
在這一澳對華小麥出口貿易陷入危機的背景下,當時在野的澳工黨的立場顯得尤為引人注目。在1966年之前,澳工黨主要領導人雖然并不希望在國際舞臺上對中國實行外交孤立,但他們同孟席斯等人一樣認為中國對于澳大利亞而言是一個“威脅”,這也是工黨一度批評澳政府將政治和貿易區別對待的做法是“虛偽”的原因。(16)參見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p.37-38; 95-96.但在1969年惠特拉姆確立了其在工黨黨內的領導地位之后,工黨在澳對華貿易出口問題上的口徑開始發生變化,其不再把矛頭指向執政黨將貿易與政治分離的做法的虛偽性,而是轉而呼吁澳政府改善對華關系以利于澳對華小麥出口貿易。因此,澳工黨的主要領導人才會對安東尼的聲明提出批評,甚至建議澳政府為后者和其他官員的過激言論向中國道歉。(17)參見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pp.103-104, 107.工黨在惠特拉姆成為其領袖之后摒棄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并不令人意外。早在1954年,惠特拉姆在澳大利亞政壇初露鋒芒之時,他就曾在議會中對當時執政的孟席斯政府推行的反華政策進行過駁斥,并公開呼吁澳大利亞應當直面現狀,基于現實主義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8)參見“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nsard, August 12, 1954, p.274.更重要的是,在其后的十多年時間里,惠特拉姆從未改變過其上述立場。(19)參見Billy Griffiths, The China Breakthrough: Whitlam in the Middle Kingdom, 1971, p.13.
考慮到澳對華小麥出口貿易的重要性,工黨在相關問題上會擺出與政府針鋒相對的立場或許并不令人意外,但真正令許多時人側目的是此后工黨領導人做出的派遣高規格代表團訪華的決定。1971年4月14日,惠特拉姆以工黨領袖的名義向周恩來總理致電,表達了工黨希望派遣代表團訪華與中方就外交及貿易問題舉行會談的意愿。(20)惠特拉姆致電周恩來總理的電文原文詳見Gough Whitlam, “Telegram from Gough Whitlam to Zhou Enlai, 14 April 1971,” For the Record: Gough Whitlam’s Mission to China 1971, p.7.
二、澳中民間往來與工黨訪華計劃的提出
工黨決定派遣代表團訪華的消息曝光之后,立即在澳大利亞國內引起了輿論轟動。考慮到澳大利亞即將在一年之后迎來大選以及對華關系在澳國內政治中的敏感性,工黨在當時提出訪華的計劃無疑是冒著一定政治風險的。(21)比利·格里菲斯指出,出于規避政治風險的考慮,惠特拉姆本人甚至一度猶豫是否要親自率團出訪中國。Billy Griffiths, The China Breakthrough: Whitlam in the Middle Kingdom, 1971, p.24.然而,惠特拉姆等工黨領導人做出的這一看似出人意料的決定,實際上卻并非是毫無先例的投機之舉。在澳中建交之前的23年時間里,盡管反華的論調始終在澳大利亞國內占據著輿論的主流,但兩國在民間層面仍然保持著一定的人員往來,并因此在潛移默化之間為1971年工黨通過訪華的方式推動澳中關系實現正常化創造了有利條件。
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早在1957年,也就是工黨重新確立了其支持澳大利亞與中國建交的立場之后,就曾派遣過一支以黨內議員萊斯利·海倫(Leslie Haylen)為首的代表團訪問中國。(22)工黨在1949年大選失利下臺后曾一度在對華問題上持保守態度,直到1955年霍巴特會議后,工黨才重新明確了其支持澳中建交的政策立場。參見Henry Stephen Albinski, Australia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hina, pp.113-118.海倫在華期間曾受到過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在會談過程中,他介紹了工黨在1955年舉行的霍巴特會議之后明確的一系列對華政策的基本方針,包括推動“發展不受限的對華貿易、在外交上承認中國以及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23)Leslie Haylen, Chinese Journey: the Republic Revisited.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59, p.145.除了海倫之外,工黨主席弗蘭西斯·張伯倫(Francis Chamberlain)和議員托馬斯·尤倫(Thomas Uren)等人亦曾在1958年和1960年分別到訪過中國。(24)“A.C.T.U. SENDS 3 TO CHINA,” Tribune, February 26, 1958, p.1; Tom Uren, Straight left, Milsons Point, N.S.W: Random House, Australia, 1995, pp.117-118.
上述案例表明,在1971年惠特拉姆等人決定出訪中國之前,工黨方面就已經有過類似的嘗試,只是由于彼時工黨尚不具備獲得贏得大選以推動澳中建交的條件,因此這些早期的訪華人士未能獲得像此后惠特拉姆等人一樣的關注度。(25)費思棻指出,工黨在當時并未切實地貫徹其支持澳大利亞與中國建交的宗旨的原因可能有兩個,首先是其不得不顧及持反華立場的民主工黨(Democratic Labor Party)在大選中的影響力,其次是因為“中國威脅論”的觀點在工黨內部仍有一定市場。Stephen FitzGerald, Talking with China: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Visit and Peking’s Foreign Policy, pp.6-7.盡管如此,這并不意味著海倫等工黨內的實力派人士的訪華之旅毫無意義可言,相反,從他們在返回澳大利亞之后的一些言行來看,訪華的經歷不但給海倫等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強化了他們支持澳大利亞與中國建交的信念。海倫在返澳后不久就曾在時任工黨領袖H.V.伊瓦特(H.V.Evatt)的支持下,公開致電美國駐澳大使W.J.塞巴爾德(W.J.Sebald),反駁其發表的反對澳大利亞與中國建交的言論。(26)參見“Mr. Sebald Attacked On Anti-China View,” The Canberra Times, 29 July, 1957, p.7.張伯倫則是對當時在澳大利亞國內以反共斗士著稱的B.A.桑塔馬利亞(B. A. Santamaria)發表的反華言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駁斥。(27)參見“ALP president’s China trip,” Tribune, July 2, 1958, p.5.尤倫同樣曾在議會辯論中多次對新中國在社會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給予肯定,并且呼吁澳大利亞應當支持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28)參見“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nsard, September 28, 1960, pp.1461-1463.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尤倫的上述言論絕非僅僅代表了他個人的觀點,而是恰如馮兆基(Edmund S.K. Fung)和馬克林(Colin Mackerras)所指出的那樣,表達了工黨黨內許多人的心聲。(29)參見Edmund S. K. Fung and Colin Mackerras, 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5, p.37.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海倫等人早期的訪華之旅,為此后惠特拉姆等人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做了鋪墊。
當然,在1972年澳中建交之前到訪過中國的絕非僅僅只有工黨人士。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曾迎接過不少澳大利亞知識分子或是和平人士。澳大利亞著名左翼記者威爾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即是為數不多的幾名在50年代初就曾到過中國的民間人士,伯切特在1951年訪華后撰寫了《中國掙脫枷鎖》(China’sFeetUnbound)一書,其中詳細記錄了他在北京、天津和淮河流域等地旅行的見聞,在其筆下,中國人民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呈現出一幅與此前截然不同、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同時也與他眼中物欲橫流的西方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30)參見Wilfred G. Burchett, China’s Feet Unbound,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2.
盡管以伯切特為代表的這些早期訪華人士對于新中國的正面敘述,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當時澳大利亞國內保守勢力極力營造的反華浪潮所淹沒,但他們的著作仍然在不經意間激發了少數澳大利亞的有識之士對于中國的興趣,同時也對包括工黨在內的澳大利亞各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事實上,在1971年工黨的訪華計劃從最初提出到付諸行動的各個環節中,都可以觀察到此前澳中民間往來留下的“蛛絲馬跡”。
如上所述,1970年末澳對華小麥出口受挫是促使工黨做出派出高規格代表團訪華的直接誘因,但首先意識到“小麥危機”為工黨提供了一個重要政治機遇的卻恰恰是一名曾經熟讀伯切特的著作并且有過早年親身訪華經歷的工黨領導人邁克·楊。在1971年4月于阿德雷德召開的工黨聯邦執委會會議上,楊提議工黨派遣一支代表團訪問中國,并獲得了包括惠特拉姆在內的其他工黨領導人的一致支持。(31)參見Gough Whitlam, The Road to China,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9, p.103; Stephen FitzGerald, Talking with China: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Visit and Peking’s Foreign Policy, p.10.楊之所以能夠敢為人先,提出這一大膽倡議,一方面反映了他本人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敏銳性,另一方面也與他早年的訪華經歷息息相關。(32)關于楊在捕捉政治機會方面的能力,參見Stephen FitzGerald and Garry Sturgess, “Stephen Fitzgerald Interviewed by Garry Sturgess in 2012 for Beyond the Cables-Australian Ambassadors to China Oral History Project,”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2012, Session 3, ORAL TRC 6440/3.
出生于草根階層的楊在于1969年獲選成為澳工黨聯邦書記之前,曾在新南威爾士州的布羅肯希爾(Broken Hill)從事過多年的剪羊毛工作并且擔任過工會的干事。(33)關于楊的生平參見Stephen Guest, “Young’s Career Mirrors the Party’s Past 30 Years,” The Canberra Times, February 9, 1988, p.8; “The Rise, Fall, of Mick,”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29, 1984, p.4; Ross McMullin, The Light on the Hill: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1891—199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 1991, p.324.在此期間,通過工友的介紹,楊接觸到了由伯切特撰寫的《中國掙脫枷鎖》一書。(34)參見Stephen Guest, “Young’s Career Mirrors the Party’s Past 30 Years,” p.8.原文中提到伯切特的著作名為“China Freedom Bound”,應系筆誤。伯切特在其書中所描繪的中國顯然給楊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就在他讀到前者的這本著作后不久,年僅21歲的楊便參加了由尤里卡青年團(Eureka Youth League)選派的代表團,先赴蘇聯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后又應邀前往中國進行訪問。(35)參見“Keen Interest in Socialism,” Tribune, December 18, 1957, p.5. 尤里卡青年團是當時澳大利亞共產黨的青年組織。
據楊在工黨內的導師克萊德·卡梅隆(Clyde Cameron)回憶,這次訪問蘇聯和中國的經歷對楊起到了一種思想上的啟蒙作用,使得他的政治立場更加趨向于“開明”和“進步”。(36)參見“The Rise, Fall, of Mick,” p.4.曾與楊同行共事的費思棻亦表示,雖然楊日后與左翼政治漸行漸遠,但他始終對中國抱有濃厚的興趣,并且堅信澳大利亞應當盡早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37)參見Stephen FitzGerald and Garry Sturgess, “Stephen Fitzgerald Interviewed by Garry Sturgess in 2013 for Beyond the Cables-Australian Ambassadors to China Oral History Project,” Session 3.惠特拉姆亦曾在回憶錄中提到,每當憶起自己早年的訪華經歷時,楊常常滿懷激情。(38)參見Gough Whitlam, The Whitlam Government, Ringwood, Victoria: Penguin Books, 1985, p.55.
楊早年的這次中國之行,顯然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很深的觸動,并且使得他堅信澳大利亞應當盡早與中國建交。也正是因為這一信念,楊才會在澳對華小麥銷售受阻之時,大膽提議澳工黨派遣代表團赴華,為澳中兩國關系實現歷史性的突破提供了可能。從一開始閱讀伯切特的著作,到親赴中國,再到日后提出工黨派團訪華的倡議,楊的上述經歷看似偶然,實際上卻恰恰體現了澳中建交前雙方的民間往來對兩國關系正常化起到的積極推動作用。
三、促成澳工黨代表團訪華的民間“先鋒”
承上所述,工黨領導人邁克·楊因為其早年的訪華經歷,成了促成1971年工黨代表團出訪中國的一個重要“幕后推手”。然而,工黨方面在后續推進其訪華計劃時,卻遭遇了一個無法與中方取得有效聯系的尷尬局面,而惠特拉姆等人之所以能夠最終順利出訪中國,還有賴于一名與中國淵源頗深的青年漢學家羅斯·特里爾的鼎力相助。
惠特拉姆在向周恩來總理致電表達了工黨希望派遣代表團訪華的意愿之后,并沒有立刻收到中方的回應。考慮到若是中方不回復甚至直接拒絕己方提議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將在政治上造成的負面效應,工黨方面自然倍感焦慮,惠特拉姆本人甚至在同年4月21日(也就是電報發出7天之后)專門要求他的私人秘書理查德·豪爾(Richard Hall)向澳大利亞海外電訊委員會詢問中方是否確實收到了來自工黨方面的函電。(39)參見“F.A. Stanton’s letter to Gough Whitlam, 21 April, 1971”, Papers of Richard Hall, MS 8725,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Box 51, Series 15, File 2.
為了盡快敲定訪華相關事宜,工黨方面開始通過各種渠道探聽中方對其來電的態度。當時負責工黨農業事務的雷克斯·帕特森(Rex Patterson)就曾嘗試聯系他認識的“負責銀行和小麥業務的中方技術人員”,希望后者能夠助工黨一臂之力,(40)Rex Patterson, “Letters to the Editor Solomon report,” The Canberra Times, 7 June, 1971, p.2.而惠特拉姆的私人秘書豪爾則是向特里爾發出了求助。
史料顯示,在接到豪爾為工黨訪華一事向其求助的請求之后,特里爾曾多次聯絡他在世界各地的熟人朋友,包括彼時擔任法國駐華大使的艾蒂安·馬納克(étienne Manac’h),希望他們能夠施以援手。(41)特里爾在與豪爾的通信中提及,他曾就工黨訪華一事求助過當時身在加拿大的林達光(Paul T.K. Lin)、馬納克以及香港《大公報》方面,參見“Ross Terrill’s letter to E. M. Manac’h, 28 April, 1971”; “Ross Terrill’s letter to Richard Hall,28 April, 1971”; “Ross Terrill’s Telegram to Lee Tsung-Ying, 26 April, 1971”, Papers of Richard Hall, all in Box 51, Series 15, File 2.其他佐證材料參見:Ross Terrill, “Australia and China,” Nation, August 7, 1971, pp.12-14;“How Labor group got to Peking,”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14, 1971, p.10, both in “China-Relations with Australia-Visits to China - ALP Delegation 1971,”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NAA): 3107/38/12/7 PART 2.在其于1971年4月28日寄給馬納克的求助信中,特里爾介紹了工黨的訪華計劃出臺的背景和惠特拉姆致電周恩來總理的情況,并且特別強調如果工黨能夠順利贏得來年的大選,那么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將會迎來重大改變。(42)參見“Ross Terrill’s letter to E.M.Manac’h, 28 April, 1971”, Papers of Richard Hall, Box 51, Series 15, File 2.結合馬納克在5月27日給特里爾的電報,以及后者在其回憶錄中的說法可知,馬納克是在5月7日接到了特里爾的信件,隨后在第二天乘坐飛機時,遇見了時任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的韓敘,并請他向周恩來總理代為轉達了工黨方面的口信。后續的事態發展表明,馬納克這一打破外交慣例的舉動應當是起到了效果,因為僅僅在兩天之后,惠特拉姆就接到了來自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正式訪華邀請。(43)參見“E.M.Manac’h’s telegram to Ross Terrill, 27 May, 1971”, Papers of Richard Hall, Box 51, Series 15, File 2; 羅斯·特里爾:《我與中國》,劉慶軍、許道芝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76頁;Gough Whitlam, The Whitlam Government, p.55;另外,關于韓敘當時與周恩來總理在工作上的聯系情況,阮虹曾在其所著《韓敘傳》中提道:“(韓旭)幾乎天天都能見到周恩來。”阮虹:《韓敘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125頁。
如果沒有特里爾通過馬納克在澳工黨和中方之間牽線搭橋,惠特拉姆等人或許最終仍會收到中方同意他們訪華的回信,但也很可能因為等待回信的時間過長而在政治上錯失先機。事實上,在接到中方的電報之前,當時擔任澳總理的威廉·麥克馬洪(William McMahon)即抓住了工黨方面“久候”中方回應未至的尷尬,對惠特拉姆致電周恩來總理的行為多有嘲諷。(44)參見“Uproar as Pm Plays His Hand on China,” The Canberra Times, April 21, 1971. p.1.更重要的是,即使工黨的訪華代表團最終能夠順利成行,如果他們未能在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其訪華決定之前抵達中國并與周恩來總理舉行會談,那么他們此番出訪的政治意義亦將大打折扣。(45)關于工黨代表團訪華的時間節點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參見Graham Freudenberg, “Introduction,” For the Record: Gough Whitlam’s Mission to China 1971, pp.4-6.因此,特里爾在確保工黨代表能夠順利訪華一事中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中間人”的作用,正是因為他通過馬納克向中方及時傳達了工黨方面的口信,才使得惠特拉姆等人不至于錯失出訪中國的最佳時機。
工黨之所以會在當時尋求特里爾的幫助,很可能是因為后者是少數幾名曾經有過親身訪華經歷的中國問題專家。正像與他年紀相仿的楊一樣,特里爾很早就萌生了對于中國的興趣,并且同樣受到過一名熟悉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影響。在墨爾本大學求學期間,特里爾曾受教于多名思想左傾的老師,其中就包括任教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知名漢學家費子智(C.P. Fitzgerald)。根據特里爾本人的回憶,費子智曾在重訪中國后不久到過墨爾本大學給他和其他學生上過課,并且在課上介紹了當時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巨變。(46)羅斯·特里爾:《我與中國》,第6頁。實際上,在這一時期訪問過中國的澳大利亞知識分子之中,費子智或許是最具影響力的一人,由他發起創建并任首任主席的澳中協會(Australia China Society),是一個致力于推動澳中兩國民間文化交流的組織。因此緣故,他與當時澳大利亞國內眾多對中國抱有興趣的各界人士都保持著一定的聯系,并且曾經推薦他們中的部分人前往中國訪問。(47)關于費子智當時與澳大利亞同情中國的各界人士保持的密切聯系,參見C. P.(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 and Ann Turner, “C. P.FitzGerald Interviewed by Ann Turner,”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Session 2, ORAL TRC2797.費子智本人亦曾經于1956年率領澳大利亞文化代表團到訪中國,并在返回澳大利亞后積極撰文分享他在華時的見聞。(48)參見C. P.FitzGerald, “The Changed Face of China,” Australian Cultural Delegation, ed., Report on China, Australia-China Society, Glebe: N.S.W. Branch, 1956. 關于費氏本人的著作和活動對澳大利亞公眾眼中的中國形象和澳政府對華政策產生的影響,另可參見樊林:《漢學家費子智與澳大利亞公眾中國觀1949—1972》,《歷史學教學問題》2013年第3期。除了撰寫文章和講學之外,他還頻繁在澳大利亞各地舉辦公開演講,向公眾介紹他眼中的中國。(49)參見“CHINA MAY SOON MAKES DRIVE FOR MARKETS,” The Mercury, November 02, 1956, p.17; “Easier To See Red China Now, Says Professor,” The Mercury, November 06, 1956, p.2; “Professor claims that Red China has changed its attitude to the West,” Advocate, November 09,1956, p.4, all in “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Volume 2,” NAA: A6119, 675.
或許正是因為在大學期間就已經意識到中國對澳大利亞的重要性,特里爾才會參與創辦了一個名為“承認中國”的學生團體,公開呼吁澳大利亞應當盡早承認新中國,并且在畢業后就決定親赴中國旅行。(50)關于特里爾在大學期間參與創建“承認中國”團體并為其撰稿的情況,參見羅斯·特里爾:《我與中國》,第8—9頁。在從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取得簽證之后,特里爾于1964年取道莫斯科來華。在北京停留期間,特里爾對當地的市容市貌進行了細致的觀察。他曾前往人民大會堂、天安門、頤和園參觀,還去過北京市圖書館,并在米市大街教堂與趙復三牧師有過會面和交流。(51)羅斯·特里爾:《我與中國》,第18—21頁。如同許多在這一時期到訪過中國的西方人一樣,特里爾注意到當時的中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一整套基礎社會保障制度,在其日后為《新共和國》(TheNewRepublic)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北京的街頭“并不總是永遠干凈或者沒有任何異味,但卻也未曾有明顯惡化的跡象,亦沒有像亞洲許多城市那樣有著倒在路邊的乞丐和病人。”(52)參見Ross Terrill, “A Trip to China II,” The New Republic, Vol.152, No.3, (January 16, 1965), p.14.在他的日記中,特里爾同樣寫道:“盡管小巷內比較擁擠,人們比較貧窮,但是沒有一人衣衫襤褸,沒有一人目光呆滯坐著或者躺著……盡管生活還很貧窮,但是整個社會井然有序,每個人都有尊嚴地活著。”(53)羅斯·特里爾:《我與中國》,第24頁。
正如特里爾日后在《八億人:真正的中國》(800,000,000:TheRealChina)一書中所提到的那樣,盡管他的首次中國之旅只有短短兩周時間,但這已經足以促使他下定決心“了解中國和學習中文。”(54)Ross Terrill, 800,000,000: The Real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9.也正是因為這一決心,在結束了其訪華行程之后,特里爾旋即于1965年遠赴美國就讀哈佛大學,師從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攻讀博士學位,由此正式踏上了中國研究之路。在攻讀博士期間,特里爾曾基于自身的訪華經歷撰寫了多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一舉奠定了其作為一名青年漢學家的聲名,為其之后參與到惠特拉姆的訪華之行埋下了伏筆。(55)參見Ross Terrill, “A Trip to China,” The New Republic, Vol.152, No.1, (January 2, 1965), pp.9-11; “A Trip to China II,” pp.13-15; “A Trip to China III,” The New Republic, Vol.152, No.4, (January 23, 1965), pp.15-16.
正是由于特里爾是當時少數幾名了解中國并擁有廣泛人脈的澳大利亞人,澳工黨方面才會在遲遲無法獲知中方對其來電態度時向他求助,并最終通過他積極的“鴻雁往來”與中國方面取得了聯系,確保了代表團能夠順利出行。作為澳工黨代表團的“先鋒”,特里爾本人則是在代表團抵達北京之前就已經事先應邀來華,并且在之后參與了周恩來總理與惠特拉姆的歷史性會談。(56)“先鋒”一語為特里爾轉述周恩來總理的說法,其意指前者為惠特拉姆等人的出訪先行做了相關的準備工作,參見羅斯·特里爾:《我與中國》,第76—78頁。
由特里爾上述的訪華經歷和他后續在工黨代表團訪華一事中發揮的作用可知,澳中建交之前雙方的民間往來雖然看似雁過無聲,實則在不經意間為兩國關系的正常化鋪平了道路。同時,我們也需注意到的一點是,相較于執政的自由黨而言,工黨在1955年霍巴特會議之后,對于發展對華關系這一點抱有更為積極的態度,因此才會在支持海倫等黨內高層人士出訪中國的同時,主動地與像特里爾這樣的知識分子保持接觸,確保了其能夠在時機成熟之時采取果斷的措施,從而推動了澳中關系的正常化。
結 語
作為一名以雷厲風行的施政風格而著稱并因此備受爭議的澳大利亞政治家,惠特拉姆生前曾多次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強調,早在1954年,也就是他所屬的澳工黨重新明確了其對華政策之前,他就曾基于現實主義的政治立場,公開呼吁澳大利亞應當盡早與中國建交。(57)參見Gough Whitlam, The Road to China, pp.5,9,30,46.澳中兩國的關系之所以能夠在1972年工黨政府上臺之后迎來歷史性的突破,惠特拉姆在一眾參與其中的澳方政治人物中自然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我們同樣不應忽視的一點是此前兩國之間存在的民間貿易往來和人文交流為此創造的有利條件。
這一“民間”因素的重要性在澳中建交的前奏曲即1971年由惠特拉姆率領的工黨代表團對于中國的訪問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首先,工黨在當時做出的訪華決策絕非僅僅是一種帶有政治投機性質的草率之舉,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葉,以海倫為代表的部分工黨人士就曾以各種名義訪問過中國。這些早期的訪華嘗試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強化了工黨內部支持澳大利亞與中國盡早建交的信心。其次, 如果說澳大利亞對華小麥出口貿易在1970年遭遇到的危機,是促使惠特拉姆等工黨領導人決定派出高規格代表團訪華以尋求澳大利亞對華關系突破的一個重要契機,那么,邁克·楊和羅斯·特里爾則是確保了工黨的這一大膽設想能夠得以實現的關鍵。是楊首先意識到澳對華小麥銷售危機對于工黨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機遇并提出了訪華的動議,而遠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的特里爾,則是在惠特拉姆等人因遲遲無法與中方建立直接聯系而一籌莫展之時,靈活運用了自己的人脈關系,在雙方之間頻繁牽線搭橋,一舉敲定了澳工黨的訪華行程。
楊和特里爾之所以能夠在促成工黨代表團訪華一事中發揮上述重要作用,無疑與他們早年的訪華親身經歷息息相關。這一共同點的存在絕非偶然,而是恰恰印證了澳中建交前澳國內少數訪華人士為推動兩國關系正常化做出的努力,雖然時常被澳大利亞政壇彌漫的反共反華的言論所掩蓋,卻始終是一縷未曾間斷的“執拗低音”。(58)“執拗低音”一詞借用自王汎森所著《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但拙文中的“低音”并非意指遭受壓抑的學術論述,而是指一種由部分澳訪華人士建構的,更為廣義的關于中國的敘事。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第1—2頁。無論是以伯切特和費子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還是海倫等工黨人士的訪華之旅都表明,當時西方部分反共人士所極力渲染的“竹幕”(bamboo curtain)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其并未完全阻斷澳中兩國民間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正是通過許多澳方訪華人士在回國后的積極宣傳,一種不同于當時澳國內主流的“中國威脅論”的中國形象才得以隨著時局的變化日漸深入人心,并由此為工黨最終在推動澳中關系正常化的道路上邁出關鍵性的一步奠定了民意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