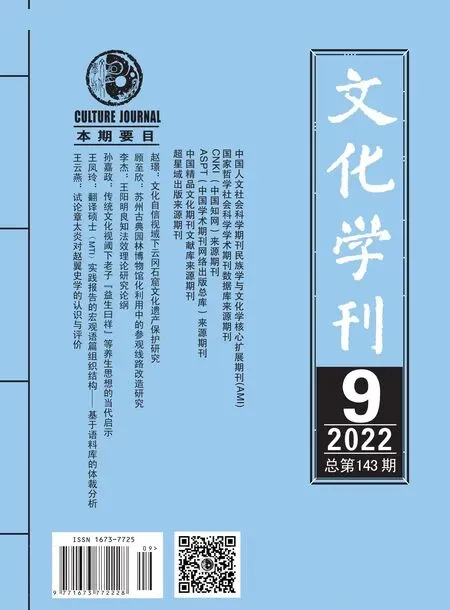弗雷格、羅素、邁農和斯特勞森的對象理論對比研究
劉萬秋 鄭 穎
一、引言
在西方語言哲學史上,弗雷格、羅素和斯特勞森的指稱論分別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對對象的指稱問題、真值問題、意義問題等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與探討。邁農提出的對象論其實與上面三位學者的指稱論都是在研究對象的問題,且對象問題是學者們一直在激烈探討的一個問題。本文試將四位學者的理論聯系起來,統稱為“對象理論”,而且本文所說的對象理論是一個廣義上的范疇,不局限于指稱論或意義論等。
關于對象問題,國內外學者已經做過很多相關研究,尤其是對弗雷格、羅素和斯特勞森的指稱論研究居多。比如周惟亮(2015)研究了弗雷格的概念和對象思想[1]1-39;賈可春(2007)探討了羅素的意義指稱論,其中也與弗雷格做了一定層面的比較[2];張力鋒(2000)對斯特勞森的指稱論進行了比較詳細的闡釋和客觀的評價[3]。另外,也有不少學者進行對比研究,如楊海波等(2018)就弗雷格與羅素的意義理論及對象思想作比對討論[4]5-6;田然(2008)對前述三位學者關于指稱論的核心觀點進行對比分析等[5]。在這些研究里,學者們對指稱理論做了詳細的分析與闡述,也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但是,相對于弗雷格、羅素和斯特勞森的指稱論來說,學界對邁農的對象論研究較少,尤其少有學者將邁農的對象論與指稱論聯系起來探討。邁農的對象論在對象問題上提出了與指稱論不同的觀點,因此,將其與指稱論放在一起進行對比研究是有一定價值的。基于此,本文試圖對弗雷格、羅素、邁農和斯特勞森四者的基本理論觀點進行比較分析。
二、對象理論的比較
本文的論述主要基于這四篇文章:弗雷格《論意義和指稱》[6];羅素《論指謂》[7];珀爾茲克《非存在對象:邁農與當代哲學》[8];斯特勞森《論指稱》[9]。這四篇文章分別詳細闡述了弗雷格、羅素、邁農以及斯特勞森的對象理論。
(一)弗雷格的基本理論觀點
1892年,弗雷格發表《論意義和指稱》,將符號、意義和指稱的含義區分開來,并具體而微地討論了語句的意義和指稱問題。他認為,語言的特定組成部分的價值在于藉由符號指稱對象實現與世界的聯系。據其觀點,符號的功能除表達含義以外,還能夠標示該含義的指稱,兩個不同符號的指稱對象可以是同一對象。換言之,一個名稱的構成元素包括有意義和指稱,名稱不同、意義不同,但指稱對象可能是相同的,如晨星和暮星。
弗雷格所提到的專名是包括摹狀詞在內的廣義上的專名,他認為專名和摹狀詞具有相同的邏輯作用。弗雷格認為,專名不僅有指稱也有含義,且其指稱取決于含義,即表達式在清楚表達含義的前提下,才可以指稱特定對象。但反過來是不成立的,表達式是否具有含義與是否有指稱無關,比如“最小收斂級數”“離地球最遠的天體”等,雖然有含義但沒有指稱,他將這類沒有指稱的對象名稱歸為空類。
總的來說,弗雷格的理論服務于研究“科學的真”。弗雷格認為“真”是實在的東西,因此,必須要有專名即明確指稱,由此使得其理論應用于部分自然語句的分析時出現相互抵觸的現象,比如專名對象并不客觀存在時句子缺少真值。弗雷格的研究重點是有指稱對象的這一類專名,對于空類的名稱他并未作出過多的研究探討。
(二)羅素的基本理論觀點
羅素駁斥并發展了弗雷格的指稱理論。1905年,羅素發表了《論指謂》一文,提出了摹狀詞理論。相比弗雷格的理論,羅素嚴格區分了專名和摹狀詞。他主張專名是直接指稱個體的詞,其語義作用就是其所指而非其他任何事物。至于摹狀詞,則屬于函數的一種,取值與其構成部分的意義存在直接關聯[1]1-39。
羅素與弗雷格在專名的指稱問題上觀點基本一致,但在專名的意義問題上,羅素認為專名的意義取決于它所指稱的個體是否存在,而專名指稱的對象是由摹狀詞決定的。羅素的重要觀點之一即“邏輯的任務乃是消除。”此處所指的消除對象并不是語詞,而是部分語詞的指稱功能。羅素強調,一切涉及限定摹狀詞或普通專名的語句,都應改寫為缺少原來專名與限定摹狀詞的語句。比如“孫悟空不存在。”應該改寫為(或意思等同于)“并非唯一存在著一個事物,它會耍金箍棒、是唐僧的徒弟、會七十二變……”進而這句話就是真的。
因此,羅素的摹狀詞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分析空指稱的句子是否為真提供了判斷依據。如他對“當今的法國國王不是禿子。”提供了兩種解釋:①存在唯一一個東西,他是法國國王且不是禿子;②并非存在唯一一個東西,他是法國國王且是禿子。顯然第二種解釋為真。那如何解釋肯定句呢?楊海波和黃雅婷[4]5-6認為“或許可以辯護:一個肯定語句可以依據雙重否定規律變成一個否定語句,進而可以按照羅素處理否定句的辦法來回避這一批評。”即把“當今的法國國王是禿子。”變成“當今的法國國王并非不是禿子。”但不管是從一個句子可真可假來說,還是從雙重否定的轉換來說,這樣的解釋不免有些牽強。
(三)邁農的基本理論觀點
邁農在哲學上以提出對象論而著名。他主要針對的是解決非存在對象問題,認為我們應該承認非存在對象“存在”。但非存在對象的合理性一直備受爭議,因此,邁農的理論曾備受批評。在《非存在對象:邁農與當代哲學》一書中提到,哲學家賴爾曾有過這樣的論斷:“讓我們坦率地承認,邁農的非存在對象理論從一開始就死掉了,被埋葬了,而且不可能被復活。”另外,羅素也認為“正如動物學不承認有獨角獸一樣,邏輯也不承認有獨角獸[10]”。羅素認為自己的摹狀詞理論可以解決非存在對象的問題,但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摹狀詞理論在解決非存在對象問題上有很多牽強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意識到非存在對象的問題并未被一勞永逸地解決。筆者認為邁農理論在解決這一問題上是有一定價值的。
邁農認為“對象”不只是指存在著的具體事物,也包括非存在的東西,它們是并不存在但具有客觀特性的對象,也就是說邁農認為不應該把對象限制為存在的對象,應遠遠超出現實存在對象的范圍。非存在對象指的是某些在現實世界不存在的事物,即非現實的、虛構的事物,比如:宙斯、獨角獸、福爾摩斯、金山、圓的方等等。
朱建平(2014)在《非存在對象語義學》中論述說,邁農贊同這樣一種解釋:為了斷定“有非存在的對象”而不蘊含“非存在對象存在”,其假設條件應為形式為“有F”和“F存在”的句子含義存在差異[11]。
舉例來看這一理論是如何簡單解決非存在對象問題的。“伯加索斯是飛馬。”按照邁農理論解釋為如下三小句:伯加索斯是飛馬;有飛馬;飛馬不存在。這里的關鍵是“有”和“不存在”并不矛盾。包括邁農的經典例子“金山”和“圓的方”,邁農接受這種說法,因為在邁農看來,雖然這樣的事物不“存在”于我們的現實世界,但這并不意味著就沒“有”這樣的事物。
普利斯特(2005)支持邁農的理論,并提出了其他世界的策略,稱為“noneism”。他假設了可能世界和不可能世界,且兩者論域相同,但并非任意對象都存在于所有世界中[12]。比如,伯加索斯就不存在于現實的世界里,而僅存在于可能的世界即希臘神話世界中。也可以說,非存在對象只是不存在于現實世界,但存在于其他世界。
在上述解讀下,筆者認為邁農理論具有一定合理性,而且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認為認識是重復的、無限的,正確認識事物不僅是通過反復的認識實踐,而且認識是無限發展的,對真理的探索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所以我們必須從發展的角度看待問題、看待事物,正如邁農理論討論了在我們的認知里不存在于現實世界的一些對象,但這并不代表這類對象不存在于其他可能世界,且不代表不存在于未來世界。
雖然邁農理論曾備受批評,但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不可否認邁農對象論的價值,至少在解決非存在對象的問題上,邁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四)斯特勞森的基本理論觀點
斯特勞森在其著作中對羅素摹狀詞理論進行了批駁。1956年,斯特勞森發表《論指稱》一文,提出了與羅素截然不同的觀點。作為日常語言學派的代表,斯特勞森認為羅素對句子及其邏輯屬性的看法過于抽象,忽視了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句子的日常會話用法。他認為,邏輯不是先驗的,它與語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日常語言中包含并體現著人類的思維結構,對思維結構的特征進行反省便抽象出來了形式邏輯。
斯特勞森強調的是人們在具體的會話語境中是如何使用句子的。因此,斯特勞森對名稱的意義和指稱進行了區分,意義是名稱的功能,指稱是名稱使用的功能。所以不能將意義和指稱等同,且意義和指稱與語境密切相關,日常生活中的名稱自身可以蘊涵多種意思,只有在結合語境時才能具體指稱某物。斯特勞森在《論指稱》中舉了一個例子:“法國國王是睿智的。”斯特勞森認為在不同的語境下這句話的意義是不同的。如果語境背景是在路易十四執政期間,則論斷是針對路易十四而言;語境背景是在路易十五執政期間,則論斷對象就是路易十五。這顯然屬于不同的使用,具有不同的指稱和意義。
在真值的問題上,斯特勞森同樣強調語境的作用。他不同意羅素關于語句自身的真值的觀點,相反,他認為語句自身并無真值一說,而是使用者用這一語句表達了真或假的命題。
雖然斯特勞森一直在批駁羅素理論,但事實上,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矛盾,因為他們分別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研究方法和角度。羅素追求語言邏輯的理想化和精確化,研究的是限定的、靜態的對象。通過研究范疇內的對象追求本質。但斯特勞森研究的是動態的自然語言,試圖揭示自然語言的語用性等問題。雖然斯特勞森的理論并沒有形成系統的框架,但他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人的因素,把語言哲學研究引入到了語用學的層面,為語言哲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
三、結語
綜上,弗雷格將專名看作一個廣義的范疇,未對真正的專名和摹狀詞作出區分,且對于空類名稱基本不予研究;羅素的摹狀詞理論在弗雷格的基礎上區分了專名和摹狀詞,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一部分非存在對象的問題,即把非存在對象改寫為不包含此對象的命題或句子,主要針對空類的摹狀詞句子,但這一解決辦法有限且有些牽強;而邁農直接主張接受非存在對象的“存在”,雖然這一理論備受批評,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僅解決了空類摹狀詞的問題還解決了非存在專名的問題;斯特勞森的語境論則發展為更接近真實生活的一種理論,主張用日常語言的使用作為研究對象,將人的因素考慮了進來。
從弗雷格、羅素、邁農和斯特勞森的對象理論來看,哲學理論逐漸從注重科學語言的形式邏輯分析慢慢轉向對于日常語言的實際應用分析。且繼斯特勞森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考慮語用因素。唐奈蘭重點強調了語詞的功能性劃分,使交流語境的內涵更加豐富,最初將說話者的意向性因素納入考量內容,進一步深化了斯特勞森的理論。維特根斯坦提出意義使用論,反對將意義看作抽象的東西,而是用語詞或語句在社會規約下去做事。在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影響下,奧斯汀和他的學生塞爾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認為憑借語言可以達到表意、行事和取效的行為功能,應該以實際的行為去解讀語言,語言所對應的是一種行為結果。格萊斯提出了會話含義理論,聽話者要聽懂說話者句子表面意思下的深層意思,即說話者想要傳達的隱含意思,這一理論把心理因素等更多復雜的因素引入到話語研究中。由此可見,將人的因素考慮進去是一大轉向,對后來很多學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事實上,弗雷格和羅素還有邁農也注意到了語用因素,但受限于時代背景,他們的研究重點還是在形式邏輯上。當然,每個理論的發展都是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不斷繼承與創新,他們都在不斷完善對象理論的體系,繼往開來,這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目前總體來看,這一趨勢說明學者越來越關注實際生活中的日常語言,越來越看重人的因素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這是一種符合人們認知發展的,且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