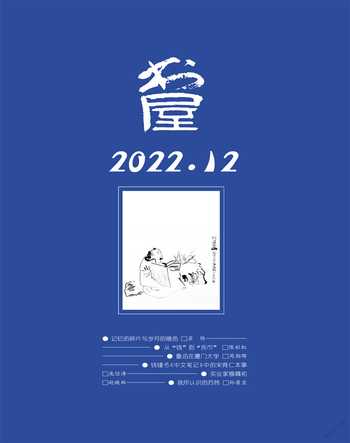新發現歐陽予倩紀念魯迅佚文輯考
康建兵
筆者在查閱民國資料時,發現歐陽予倩寫的一篇紀念魯迅先生逝世的重要文章——《不要以悲哀來紀念魯迅之死》。歐陽予倩在1936年10月26日寫成此文,發表于1936年11月10日上海出版的《電影·戲劇》第一卷第二期。此文既未被《歐陽予倩文集》《歐陽予倩研究資料》《歐陽予倩全集》《歐陽予倩佚文輯校與研究》等收錄,也未被《魯迅先生紀念集(評論與記載)》《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中國魯迅學通史》等輯錄,當是佚文。現照錄如下:
不要以悲哀來紀念魯迅之死
歐陽予倩
十月十九日到公司甚早,步高兄說劍云兄來電話說魯迅先生去世了,叫我們打聽一下如果確實便去拍點新聞片以為紀念。當時大家都像受了一種刺激,我立刻打電〔話〕問內山書店,據說真的:是清晨五點鐘的事。
五四運動以來,魯迅,誰不認為劃時代的作家?他的讀者是那樣的多,而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感動,而且他的作品深深得到國際的同情,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史上光明的一頁。
固然,他的奮勉和修養足以使他的才能發展到最高度,可是最當敬佩的是他能始終一致不屈不撓地站在民族復興運動的最前線為被壓迫者吶喊。人家說他老當益壯,其實五十六歲的年紀何嘗算老?盡管他為大眾嘔心肝,以致體力衰減,可是他一絲一毫沒有離開他的陣線,而他竟死了!盡管說誰都有這么一回事,盡管說精神不死,一個活生生的人一閉眼睡到墳墓里去,從此以后無從讀到他更新的作品,從此以后聽不見他的說話,站在帝國主義方面反對他的人們未嘗不引以為快,在仰慕他愛惜他的人們,又豈能不悲!
中國是不是只有一個魯迅?從五四運動以來,這許多年,他負起前驅的使命,盡了他的職責;目下的局面尖銳到最后的階段了,在〔這〕樣嚴重的形勢中是不是須〔需〕要更多的魯迅,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努力?我想今日的文壇斗士雖然才力有秉〔稟〕賦之不同,決沒有一個甘于自暴自棄的。
我們帶了攝影機,到了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這就是魯迅的住家,一所單開間三層樓房,擺著些破舊的家具,經周夫人的同意從樓上到樓下一一攝影,我們很希望這辛苦的斗士有比較舒服的床,比較舒服的椅子給他休養一下,可是他的臥室,在書籍堆積的一間小小樓房中一張小鐵床,一張舊椅子,一張舊藤榻上面鋪著一條薄棉墊,就這樣支持著他的峻崢瘦骨與群魔搏斗,到他最后的一息。
他還有一間秘密讀書室在狄思威路。四面都是書,中間靠窗一張書桌對面放著兩張舊藤椅,據說這里專為讀書,誰也不讓去談話的。我們因為內山先生的介紹,在那里拍了二百來尺片子。當時步高和我對面坐在窗口,談起一個偉大的作家要很戲劇的攝上銀幕,編劇導演兩方面都是異常困難的,隨著又談起《阿Q正傳》是不是可以拍成影片,當然是可能的,不過要很慎重研究。譬如高爾基的《布爾巢夫》,許多人都說無從上演,經過窐夫潭果夫(注:現通譯為“瓦赫坦戈夫”)的導演得到絕大的成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當我們拍攝臥室的時候,室中的空氣,不知不覺感到十分嚴肅。周夫人親自將桌上的筆墨書籍和煙灰缸茶杯等布置得和先生生前一樣,這個時候旁邊站著到幾位作家,他們的眼淚流了下來,這是何等凄慘的景象!
瞻仰遺容的那兩天,每日步行到殯儀館去的人何止五六千。可以說每個人的情緒是一致的。
魯迅不過是一個窮書生,他沒有勢力足以禍福人;他沒有養著爪牙去威逼弱者以不得不景從之勢;他沒有索隱行怪以鼓動青年們的好奇;他只有純潔的人格,精湛的修養,不畏強御的態度,苦斗不倦的精神,使大眾想忘掉他也忘不了!
當下葬的時候有孫夫人和蔡先生沈先生等的演說,尤其是內山完造氏講魯迅的為人和他的作品所與日本青年的影響,聽者感動到流淚。內山不是日本人嗎?他和中國許多青年辦理魯迅的喪事,其他也還有好幾個日本人在終日幫忙,那〔哪〕一個對他們有絲毫歧視?我們和他們在一處談話,一處吃飯,又何嘗不親同手足?就是我個人在日本,也有許多青年朋友,無論何時都很要好。國際的仇恨是什么?我真不懂。倘若沒有帝國主義在作祟,倘若強盜和流氓式的所謂英雄不存在,倘若沒有野心家在希圖利權獨占歪曲運用,全世界的人類何嘗不可以共同開發資源,平均享受幸福!
今后我們要和全世界的青年們握手努力鏟除阻止人類幸福的種種魔障,奠定大同的基礎,一兩個人的生死,并用不著過分的悲哀,尤其不應當只用悲哀去紀念魯迅之死。
十月廿六日
1936年時歐陽予倩在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任職,職務是編劇兼導演。10月19日一早,歐陽予倩剛到公司,程步高告知魯迅逝世的消息。歐陽予倩隨即打電話到內山書店確認,隨后與程步高、姚莘農(筆名姚克)、王士珍、程默等在當天下午兩點左右到達魯迅寓所吊唁,并拍攝紀錄影片。他們在征得許廣平的同意后,“從樓上到樓下一一攝影”。一周以后,即10月26日,歐陽予倩寫成紀念文章《不要以悲哀來紀念魯迅之死》,并交由《電影·戲劇》發表。
歐陽予倩一行在魯迅逝世當天到魯迅寓所拍攝紀錄影片,以及拍攝萬國殯儀館吊唁和萬國公墓的安葬情況,為后人留下珍貴的影像資料,但細節鮮為人知。歐陽予倩極少談論此事,僅在1961年寫的《電影半路出家記》中提及:“也不知是怎么樣一個機會,認識了姚莘農……那時候他表示著傾向進步。他告訴我說,他欽佩魯迅先生,并常到他家里去。魯迅逝世,出殯的那一天,他搶上去抬棺材,可是當時文藝界對他的看法卻還有一定的保留。”關于這一點,胡風在《關于魯迅喪事情況——我所經歷的》中的說法可供參考:“至于抬棺材這件事,當時簡單決定了,但臨時也有人自動加了進來,如姚克,他和這些人并無友誼關系的。魯迅和他,也完全是一般的社交關系,只是因為他和斯諾的關系。”
魯迅逝世當天,趕赴魯迅寓所拍照、攝像的并非只有明星影片公司的歐陽予倩一行。此外,還有當時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就讀的攝影師沙飛(原名司徒傳),他在魯迅寓所拍下了魯迅的遺容,后交由上海、廣州各大報刊發表。但被準許拍攝魯迅的“秘密讀書室”的,只有歐陽予倩一行。在明星影片公司去的人中,負責掌機攝像的主要是攝影師程默、王士珍。魯迅逝世的消息傳出后,國民黨市黨部派了一些特務監視魯迅的喪事,歐陽予倩等人的拍攝工作也遭到不斷阻擾。程默對此有回憶:“歐陽予倩和柯靈兩人帶我們去。去的時候,大家心情都很悲痛。魯迅已經躺在床上了,他的孩子、愛人都很悲痛。我們把機器拿出來,架上三腳架,拍攝了魯迅先生的遺容。我們參加追悼會是通過宋慶齡的關系,國民黨不讓我們去,派了很多特務阻礙我們的拍攝活動。拍攝這些材料很困難。”
《不要以悲哀來紀念魯迅之死》不僅未被《歐陽予倩全集》等收錄,同樣未被魯迅研究資料匯編等輯錄。
歐陽予倩與魯迅的交集,可追溯至五四時期,當時歐陽予倩創作過一部小說《斷手》,發表于1919年《新潮》第一卷第二期,這部小說引起過魯迅的注意,并得到他的評點。